《上海文化》| 学术专题:神话学研究
谁是聂赤赞普
张学海 | 西藏民族大学副教授
原文刊载于《上海文化》2019年第2期
内容摘要
聂赤赞普被认为是吐蕃王朝的前身西藏山南雅隆部落悉补野第一代赞普。本文从西藏史书上关于聂赤赞普记载分析入手,揭示了聂赤赞普叙述的神话传说特点;运用神话原型批评的方法,解读了西藏史前时期丰富的太阳崇拜文化现象,指出了西藏先民集体无意识的特征;分析了聂赤赞普史书记载的细节,提出了聂赤赞普是西藏先民以太阳为原型的藏族传说始祖的观点。
关 键 词 聂赤赞普 神话 原型批评 太阳崇拜
一、关于聂赤赞普的历史记载
聂赤赞普被认为是吐蕃王朝的前身西藏山南雅隆部落悉补野第一代赞普。关于聂赤赞普,在西藏的史书上有许多记载。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中记载:“天神自天空降世。在天空降神处上面,有天父六君之子,三兄三弟,连同墀顿祉共为七人。墀顿祉之子,即为墀聂墀赞普也。来作大地之主,降临来到人间……遂来做吐蕃六牦牛部之主宰也。”“降临雅砻地方,天神之子作人间之王,后又为人们目睹直接返回天界。”[2] 这两段文字说明了聂赤赞普的出身和来历。《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是敦煌出土的公元8-10世纪藏文历史文献。据此说,聂赤赞普是“天神降世”,来到雅隆,作人间之主,死后返回天界。所以,聂赤赞普具有亦神亦人的身份特点。
写作于1346年,成书于1363年的《红史》是藏族史学第一部综合性的通史著作。关于聂赤赞普的记载更加详细:“此后,乃有天神降世来为人主。喜饶郭恰大师所著的《殊胜天神礼赞》的注释和拉萨大昭寺发现的《柱间史》中说,释迦种族的释迦钦波、释迦黎扎比、黎迦日扎巴三支传到最后有名叫杰桑的国王;他的小儿子领着军队穿女人服装逃往雪山之中,后代世代为西藏的国王。《霞鲁教法史》中说,印度国王白沙拉恰切的儿子为聂赤赞普。本波教徒们则认为天神之主是由十三层天的上面沿着天神绳梯下降的,从雅隆的若波神山顶上沿天梯下降到赞塘郭细的地方,看见的人说,从天上降下一位赞普,应请他当我们众人之主。于是在脖颈上设置座位将其抬回,奉为国王,称为聂赤赞普,这是吐蕃最早的国王……天赤七王的陵墓建于天上,神体不留尸骸如虹逝去。”[3] 《红史》在“天神降世来为人主”的说法下,列举了聂赤赞普身份的两种观点:一是外来说,来自佛教的神圣家族或印度国王;二是本地说,以为“天神降世来为人主”是西藏本土宗教即本教的说法。《红史》著述于公元14世纪中叶,经过佛本之争和佛教在西藏7个世纪的传播,逐渐形成了结合西藏本教特征的藏传佛教。佛教成为西藏传统社会意识形态的主体,对西藏历史的叙述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1434年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所著的《汉藏史集》对聂赤赞普的叙述更加详细:“此后,有天神下降而为人主,其故事如下。前述印度护狮王有五个儿子,中间的第三子眼睛像鸟一样从下往上,长着碧玉的眉毛,手指联在一起,牙齿像海螺。此子出生后,护狮王说:‘这是凶兆,把他杀掉!’大臣们不愿用武器把他杀死,就把他放到一个有盖的铜箱子里,钉上钉子,抛入恒河之中。这个箱子被广严城地方的一对老夫妻得到,他们把王子养在森林中的僻静处,有飞禽、野兽来给王子送食物和饮水,并与王子一起玩耍,树木和花草也向王子弯腰致敬。这样过了一段时期,王子问:‘我的命运为何这样悲惨,我的父母是谁?’老夫妻说:‘你的父亲因为你长相凶恶,将你抛入水中,被我们拾得。’王子知道自己的来历,就逃入雪山之中。先到了拉日江脱神山,在这里渐渐迷失了道路,看见了吐蕃中部的雅尔莫那细地方的神雅拉香波,就前往此处。在释迦牟尼出生后的一千三百五十六年的阳水狗年(壬戌),王子到了贡布神山的山顶上,沿着穆梯下降,到了赞塘果细地方。此时有雅千拉色、托拉温布等十二名聪明少年在此处放牧牲畜,与王子相见。他们问王子:‘你是谁?’答曰:‘赞普’。又问:‘你从什么地方来?’王子用手指头朝天上一指,少年听不懂王子的话,感到十分惊奇,说:‘这人是从天上来的赞普,可当我们的王。’将他放在一个木头座位上,用脖颈将他抬回家中,因此得名涅赤赞普(意为颈座之王)。接着,众牧人在他们放牧的地方修建了云布拉宫献给赞普,这是吐蕃最早的宫殿。关于这位国王如何从印度来到吐蕃的情况,有几种不同的说法,本教徒说,他是用穆绳、江绳来到吐蕃的,不管怎样,大家说的都是涅赤赞普,他是吐蕃最早的王。”[4] 《汉藏史集》延续了《红史》中关于聂赤赞普的说法,突出了聂赤赞普外来说,认为来自印度,并融汇了本教的说法,以为不过是沿木梯下降的印度王子。在这个叙述版本中,除了看到藏传佛教意识形态观念的强化之外,为聂赤赞普增添了奇异的身体特征和神异化的人生经历,显示了处于传说的历史时代中“弃儿型”初祖的共有特征,颇具文学性。
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在西藏政教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他在1643年写成《西藏王臣记》一书,其中关于吐蕃王朝的第一代赞普的历史叙述颇有特点:“圣观世音又复思维,此时藏地虽有若干小邦之主,然无一大王出世,则佛教之兴,颇有困难,故未作加持。适有众敬王之裔与甲巴者,生有一子,圣者乃为之作加持焉。此子相貌,异乎常人,眼皮下陷,眉如翠黛,齿如列贝,手臂如轮辐之支分,具足各种德相。父疑为神怪所变,远逐边地。持白莲者放射殊胜智慧之光,照之使其改变心境,彼乃行至拉日江托山巅望见雅砻土地,如天堂胜景,下移地上,亚拉香布之雪山明洁秀美,致璧月生爱而施以拥抱。旋来拉日若布山顶,沿天梯下降,步行至于赞塘阁西。时苯教中有才德卜士十二人放牧于此,为其所见,乃趋前问从何而来,彼以手指天,知乃自天下谪之神子。众言此人堪为藏地之王,遂以肩为座,迎之以归,因此遂称为‘聂赤赞普’。”[5] 在这里,聂赤赞普来自印度,是众敬王的后裔。而根据佛教世系,众敬王与释迦家族有着血缘关系,从而使西藏本地的统治者与释迦牟尼拉上了关系。以“天神降世而为人主”为本教的聂赤赞普出身说法,在《西藏王臣记》不再提及。回顾藏传佛教广泛传播以来的前述历史著作,关于聂赤赞普身世的外来说和本地说,在此变为一种,即佛教的神圣起源学说。
法国学者石泰安说:“对于公元6世纪之前的阶段,不可能确定吐蕃任何能推论年代的历史。但西藏人在这个问题上却有他们自己口头流传下来的历史:神话和传奇故事。”[6] 不只是西藏,综观人类历史叙述,神话和传说可以是一切民族在文字产生以前的史前文明时代的历史源头。在聂赤赞普的历史记载中,依然可以看到聂赤赞普身上鲜明的神话和传说的特点。综观藏族历史的叙述,除却藏传佛教赋予其佛教的因素外,聂赤赞普来作人间之主的历史叙述具有鲜明的非理性特点:第一,聂赤赞普是“天神降世来为人主”,具有亦神亦人的神话身份。其终也,则不留尸身,如虹逝去,返回天界。第二,神话与传说的神灵或英雄初祖都有奇异的身体特征。《汉藏史集》中说聂赤赞普“眼睛像鸟一样从下往上,长着碧玉的眉毛,手指联在一起,牙齿像海螺”。《西藏王臣记》中说他“此子相貌,异乎常人,眼皮下陷,眉如翠黛,齿如列贝,手臂如轮辐之支分,具足各种德相”。后者在其相貌描绘中,增加了“手臂如轮辐之支分”的内容,附会佛教德相的说法。其他如眼、眉和齿的描绘,两者如出一辙。这些独特的身体特征,虽不见于更早的《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的叙述中,应当是其在口头流传的过程中,结合了先民意识与经验的结果,符合神话与传说故事的一般特点。第三,聂赤赞普缘穆绳或天梯降临人间,是世界的神话与传说中典型的模式。第四,聂赤赞普建造了“第一所宫殿”即雍布拉康,开垦了“第一块农田”,兴盛了本教等,把人类发展过程中诸多事迹,汇聚于其身,表现祖先崇拜和英雄崇拜的一般特点。
神话从叙述的表层来看,与历史追求的客观真实显然不同,它的意象与情节常常是非理性,不合逻辑的。所以“‘神话’就是虚构,从科学和历史上讲,它是不真实的。但在维柯的《新科学》中这一观念已经发生变化。从德国的浪漫主义者、柯勒律治、爱默生和尼采以来,这一术语所包含的新的观念逐渐取得了正统的地位,即‘神话’像诗一样,是一种真理,或者是一种相对真理的东西,当然,这种真理并不与历史的真理或科学的真理相抗衡,而是对它们的补充”。[7] 荣格从集体无意识的理论出发,认为神话是原始人深层的集体无意识的表现形式,即原型。集体无意识作为一种亘古绵延、四处渗透的原始集体心理,必然自发地出现和支配着个体的心理,集中地体现在神话和宗教中。他说:“神话是前意识心理的最初的显现,是对无意识心理事件的不自觉的陈述。”[8] 也就是说神话作为“原始意象”或原型,它反映了原始人运用形象、类比推论的方法认识自然和人类自身的过程。这样说来,在史前时代,神话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比逻辑理念哲学更趋近真理。
二、西藏早期的太阳崇拜
西藏的史前文明包括以古象雄为代表的藏西、藏北的牧猎文明,和以卡若、曲贡遗址为代表的农业文明。从时间来看,公元6世纪时,象雄文明繁盛一时,至7世纪聂赤赞普的后代松赞干布统一西藏全境,象雄古文明衰落,来自山南雅隆地区的鹘提悉补野真正地成为了“六牦牛部落之主”。文明的中心从西部阿里转向了拉萨,游牧和狩猎的生产和经济方式转向了以粮食生产和饲养牲畜相结合的经济形态。由松赞干布建立的吐蕃王朝,开创了西藏的文字文明的历史,所以依靠定居农业和畜牧养殖建立起来的吐蕃文明成为西藏历史叙述的正统地位。这种后来历史发展状况决定了对此前传统的选择性叙述。“正是这种‘选择性’在源源不断地生产着文化记录和文化传统,其标志就是‘决定了往昔活文化中哪些内容可以被记录下来,哪些不可以’(《文化分析》)。在《文化与社会》一书中,威廉斯进一步阐明了上述观点:‘这一选择的过程与统治阶级的利益密切相关,甚至几乎就是由统治阶级的利益所支配的,这是一个永远不变的趋势。’”[9] 这种历史与文明转化是分析关于聂赤赞普的神话的前提。
19世纪的宗教学家麦克斯·缪勒认为,早期的神话和宗教中的神,都来自自然,是自然物的人格化。而人类最早的崇拜形式是太阳崇拜,太阳“从仅仅是个发光的天体变成了世界的创造者、保护者、统治者和奖赏者。实际上变成了一个神,一个至高无上的神”。[10] 在人类社会的初期,原始先民的生活和自然息息相关,太阳的周期性运行给人类牧猎和农业生产带来重大的影响。对于牧猎生活方式而言,夏季在阳光的照射下,牧草生长茂盛,牲畜长得膘肥体壮,冬季太阳光变弱,牧草枯萎,食物减少,大量的牲畜冻死。这些自然的变化,增加了原始先民们对自然的经验,形成了以自然崇拜为核心的原始宗教。西藏阿里日土县多玛区恰克桑岩画,生动地反映了藏族先民中的太阳崇拜形式。
1号岩面,位于恰克桑余脉一突出的断崖上。左上方绘有残日和太阳,太阳内有小圆圈,外边射出十道光芒。太阳右侧绘一大树,多层枝叶分布于枝干两侧,枝叶外侧有若干圆点,不知是否表示果实。其右侧绘一卍形符号。右下方又有两个射出光芒的太阳。岩画均为暗红色的粗线条,当是用矿物颜料绘制。这幅岩画显然属于原始宗教中的自然崇拜的产物。[11]
其中“卍”和“卐”是西藏岩画一种常见的符号。“一般而言,苯教雍仲符号‘卐’的旋转方向是顺时针方向而行的,而佛教的雍仲符号‘卍’则为逆时针方向旋转……但从西藏岩画来看,这个区别应当是很晚的事情。很可能是佛教进入高原后,为区别佛教、苯教才出现的。”[12] 《概述苯教的历史及教义》中亦说“在公元10世纪以前,‘雍仲’似乎没有作为苯教表示属性的定语使用”。[13] “卍”或“卐”是太阳周期性运行中时空特点的符号表现形式,在人类早期文明的古埃及、两河流域、印度和古希腊都出现过。岩画中“树木图像可能是连接天与地的梯子,树木可能有‘天梯’的功能或作用”。[14] 这幅由太阳、大树和“卍”字符号组成的岩画,显然是原始宗教自然崇拜的产物,表达了太阳崇拜的内涵。虽然日土岩画中,在反映原始牧猎生活场景的画面中多有太阳的形象,但由于太阳与牧猎生产的关系是间接的,阿里地区和藏北草原发现的大量岩画,其主体形象是动物和牧猎场景。这些以太阳崇拜为主题的岩画虽然较少,但依然反映了藏族先民对太阳产生的自然崇拜,是其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的一种。
农业生产和定居生活的方式,与太阳的关系更加直接。农作物的生长、成熟都依赖太阳的光和热。春种、夏耘、秋收、冬藏的农业生产形式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都是按照太阳的周期性运行规律进行的。太阳不仅是自然事物的创造者,生命的给予者,也是人生产和生活的最高法则。“太阳作为一种文化范式,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符号,正是在全面依赖太阳而发展起来的农耕定居生活方式中产生的,正如骑马民族的游动生活方式全面依赖于马匹一样。所不同的是,太阳的光和热不仅是农作物生长的保证条件,太阳的规则运行本身亦为定居的农夫们提供了最基本的行为方式,提供了最基础的空间和时间观念,成为人类认识宇宙秩序,给自然万物编码分类的坐标符号。”[15] 太阳在农业社会里具有比牧猎社会更加重要的核心地位,对太阳的崇拜成为自然崇拜的核心,在西藏农区太阳崇拜有直接表现的形式和置换变形的形式。“在旧石器晚期至新石器早期阶段,藏族先民的打制石器中出现了一种新型的似荷叶卷边的圆形盘状器,有研究表明这种非生产工具形制的器具很有可能与当时人们的太阳崇拜观念有关,表现了藏族先民对自然天体的思索与膜拜。先民们是在人类最简陋的原始劳作过程中,用双手和石块敲制出形制规律,有节奏动感的‘太阳石盘’,这种对太阳天体至诚至信的热情毫不亚于其后人用身体丈量土地、朝圣地叩头的情景。”[16] 太阳在藏族先民看来是世界万物的创造者。藏族的《世界形成歌》中叙述:
最初天地形成时,
阴阳混合在一起,
分开阴阳是太阳。[17]
藏族的《世界形成歌》常常在婚礼上演唱,作为婚礼仪式的一部分。[18] 在这里,男女婚媾与世界形成有着象征认同关系,反映了太阳崇拜的观念中太阳的创造世界的作用。珞巴族谚语说:“太阳照大地,万物有生机。”[19] 珞巴族把太阳作为女神来崇拜。在举行一些隆重仪式时,往往要大量杀牲,但必须选出一头大而强壮的牛,由主妇象征性地宰杀,以向太阳献祭。在博嘎尔部落,人们在内外搭一座叫“打落脚”的篷架,其上方中央画一个太阳,不时献祭,祈求太阳女神赐予人财两旺,庄稼丰收。[20] 太阳也是僜人最重要的崇拜对象。僜人生活在西藏东南部的河谷地带,当地气候潮湿多雨,阴雨天气常常给庄稼带来危害,也给狩猎造成困难,所以,每当阴雨连绵的时节,庄稼遭受灾害,便要请巫师举行巫术仪式,乞求日出。[21]
日出带来了光明和温暖,在日落之后不仅陷入无边的黑暗,而且在高寒的青藏高原,更落入了寒冷的世界中。而火在夜晚带来太阳一样的光明和温暖,在形象类比思维下,火与太阳认同,太阳崇拜就置换为对火的崇拜。“一切火崇拜都起源于太阳崇拜。”[22] “巫术仪式中最重要的一种是用火来作为象征,加强太阳的力量。特别是当一年最短的时候——冬至来临。太阳被想象为正在疲倦,要用巫术的火堆加以鼓舞。”[23] 藏族谚语说:“西方之王是火云。”[24] 西方是太阳落下,晚霞烧红天边的地方。藏族的四方物质观亦认为,西方的物质为铜,色红。红色是夕阳的色彩。“拜火是吐蕃时期重要的民间信仰之一,当时有一著名的谚语说‘火和水,没有是不行的’(mye-dan-g-chu-ai/myed-du-myi-rang-ngo),吐蕃人祭天时(ganm-mtshad),要堆放一大堆柴草(shing-spungs),谓之‘天火’。”“格萨尔有一妃即名‘火妃’(me-bzav),说她是火山之王(me-ri-rgyal-po)的女儿。”[25]
农业生产和定居生活的方式,产生了对太阳观测的需要,因为太阳的周期性运行是确定农业生产规律的依据,而定居的生活也给太阳观测提供了方便的条件。藏族很早发明了测量太阳运行的方法——长柱测影法。“这种木质测影仪器全长一尺余,是七块二寸见方的小木块连接而成,棱角互相错开,七个层次分明,每一层次代表30°,以便测出影子的长度。”“藏族人民根据长柱测影法进行观测,依照测影的长度,发现每年冬天太阳南移的端点,太阳的影子最长,藏族称之为dgun nyi ldog,意思是‘冬季太阳翻转’,也就是‘冬至’。每年夏天太阳北移的端点,太阳的影子最短。藏族称这个时节dbyar nya ldog,也就是‘夏至’。介乎最长的影子的二分之一的时候,在上半年称为dpyed mny ams,意为‘春分’mny ams为平分,即最长影子的一半。已认识这一天白昼与黑夜的时间是相同的,平分的。在下半年,测出影子恰为长影子的一半。藏语叫做ston mny ans,意思是‘秋分’。”[26] 根据长柱测影法,藏族人已经能够根据太阳影子的变化,测定当日的时间,一个月和周年的变化,测算出一个回归年的长度为365天15时32分又4/13。《五部遗教·国王录》亦说:“夏季地日距离近。大气不推徐徐行。冬季地日距离远,大气推而行速快。”[27] 除了长柱测影法,藏族从生活实践中,还发明了大拇指测影法和测水法等简单而实用的观测太阳的方法。在对太阳的观测中,根据太阳光与热的周期性变化,确立了白昼与黑夜以及春、夏、秋、冬的四季等时间。对太阳运行周期变化的精确观测是确定农时的生产要求,也是安排生活活动的依据。在时间观念确立的同时,太阳运行的空间特点相伴而生,太阳是人们建立时间和空间坐标的标尺。
在原始先民那里,太阳的光和热给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带来重要的影响,一方面太阳具有了一种人们从自己的生产和生活经验出发可以把握的特性,但是另一方面,“太阳总有某些人们不知道的东西”。[28] 即产生这种重要属性的原因,是人们通过自己的经验难以把握的。太阳是这两者特性统一的整体。而“对于这种不可见的东西,人的感官无能为力,他既不能抓住,也不能理解,他只有闭起双目对之确信不疑。俯身下跪对之崇拜”。[29] 这就产生了对太阳的自然崇拜。所以,太阳作为原始意象,它是“感官在给向我们提供有限事物的知识时,总是和那并不有限,至少不完全有限的东西相联系。其主要对象事实上是详细表现无限中产生的有限,不可见所产生的可见,超自然所产生的自然,以及不完全是现象的宇宙所产生的现象世界”。[30] 所谓那些“无限”“不可见”“超自然”和“不完全是现象的宇宙”就是灵,即超验的存在,而“有限”“可见”“自然”和“现象世界”就是太阳的光与热的形式,亦即经验的存在。在原始先民看来前者是后者的根源,太阳作为原型是光(热)与灵的统一体。因此“一个原型内容首要是采用隐喻方法来表达自己,如果内容指的是太阳,那么用以说明的则是狮子、帝王、一大堆由龙王守卫的金子,或授予人们以生命和健康的力量等等,此刻无论这一件或那一件,都不可能找到一个多少还算妥善的表达方法”。[31] 雅利安人“不得不用表达各种活动的名称命名太阳,太阳被称为发光者、温暖者、创造者或养育者”。[32] 所以,在表达时,太阳的无限的、不可见的超自然的特性常常通过其客观可见的形象,并以形象之间接触与相似的关系进行互渗而形成的形象体系暗示出来。于是,太阳的光与热的特性及其所附着的事物以及与太阳特性类似或与太阳相接触的事物,都成为太阳的无限、不可见和超自然的灵性的表现载体。
西藏远古时代丰富的太阳崇拜现象,反映了太阳在原始先民的生产、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这种与人的生存密切的关系,使太阳包含了早期人类集体的生活体验和心理经验,在远古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为人类深层的集体无意识,凝聚在以太阳的形式如光、热、圆形和周期性运行等特点为基础的,以类比推论为思维方式的象征形象体系中。作为雅隆部落第一代首领聂赤赞普的神话反映了西藏远古时代原始氏族的心理生活,而这种原始集体无意识心理凝聚在对那个时代人的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的宇宙形象——太阳中。太阳崇拜作为自然崇拜的最早形式,形成了以太阳为核心对象的人类最早的意识,这种集体无意识成为人类文明建构的文化范式和原型,深刻地影响了人类早期的神话与宗教,特别是那些关于宇宙起源和谱系的神话。
三、聂赤赞普的原型
聂赤赞普是天神降世,来作“六牦牛部落之主宰”的。他既是人间的统治者,又是光明神,具有亦神亦人的特点。“光和统治权是两个出自日常经验的观念,它们是构成神这个复合的原型意象——观念的组成要素。”[33] 在太阳崇拜的观念下,太阳与统治者具有认同性的关系,“由于光是一日之始,所以光是创造的开始,于是太阳就从光和生命的赋予者变成创造者,由此他很快变成世界的统治者”。[34] “光天的崇拜落实在现实社会中,自然又同人间统治者结下不解之缘,帝王的神性特征一般总是首先从太阳神那里移植过来的。”[35] 那些人类的最初统治者都自称是太阳或太阳神的后裔,以此显示自然种姓的高贵和统治的合法性。“现代人类学证实,这种既有神的血统又有人的身份的国王,在世界各族文明初始之际是非常普遍的现象……”[36] 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古帝王中有太昊、少昊、金天、葛天、祝融诸帝王,此光明崇拜之反映于最高统治之说明。至夏以后,则帝王多以日名”。[37] 古埃及法老自认为是太阳神,即“拉”儿子和在尘世的显现。在古巴比伦文明中,“吴尔第一王朝的第一个国王……便被称为‘日神的儿子,深入海中和升到山上的主人’”。[38] 在西藏历史上,作为吐蕃王朝前身的雅隆部落的第一代首领的聂赤赞普,也是天神降世来作人间之主的,具有和世界上其他民族祖先同样的特点,依照人类神话思维的普遍性的规律,可以说聂赤赞普的原型就是太阳。这可以从西藏有关聂赤赞普降世的细节中得到印证。
聂赤赞普的神话发生在西藏东、南地区,传说他建造了第一所房子——雍布拉康,修造了第一块农田,反映了以农业生产和定居生活为主导的地域特点,与藏西、北的牧猎文明有着显著的不同。“人类自新石器时代进化到定居阶段以后,原始宗教的重心便从狩猎巫术和图腾崇拜转向了自然崇拜。诸如日月星辰、风雨雷电等与农牧生产和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自然现象,只是到了这时才开始成为人们敬畏和崇拜的对象。而在各种自然现象中,最显然易见的一个,也是对人类生活和思想影响最大的便是太阳。”[39] 从这些文化特性看来,聂赤赞普的天神身份中的“天”无疑是太阳的形象化概括。“最初的赞普只在白天待在地上,一到晚上就返回天上。”[40] 这是对太阳昼夜运行描述,聂赤赞普即太阳。聂赤赞普和他的六位后继者,合称“天赤七王”,他们死后,不留尸身,陵墓建在天上,沿彩虹逝去。而彩虹是太阳光的一种形式。聂赤赞普来自天上,又复归天上,是对太阳循坏运行的写实。古埃及法老是太阳神的后裔,“当法老死去时,他复归于天上的父神,同父神一起用光辉统治世界”。[41] 聂赤赞普与其后六代赞普合称“天赤七王”或“上天七王”,而“上天七王的坟墓位于天上。他们后代世系的坟墓建造的越来越低,其基本图式如下:一、岩板和粘土地;二,岩板与牧场的分界处;三,江河;四,阙;五,平原;六,山谷低部”。[42] 这种由高到低的后代陵墓建造的方法,是依循太阳照射在山上由上到下的特点而进行的。高与上、低与下的认同关系是依照人对太阳运行的直观观察而建构的。西藏地势西高东低,古代西部阿里常常被称为上部,东部康地常常被称为下部。所以由止贡赞普的好战而斩断的登天的木绳,切断了太阳之间的直接联系,但死后追慕太阳祖先的光辉依然是西藏史前文明的必然选择。“以后几代赞普的王陵相继在沿着山麓而直通天堂的自然阶梯中,由上到下依次埋葬。根据18世纪一位作者的说法,古代赞普的墓葬和宫殿可能是‘以木神的方式’而建立……”[43]
聂赤赞普是沿着天梯或木绳下降到雅拉香波山顶的。《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说:“当初降临大地,来做天下之主。在天之中央,大地之中心,世界之心脏,雪山围绕一切河流之源头,山高土洁,地域美好,人聪睿而英勇,风俗纯良。”[44] 太阳带来光明,驱走黑暗,万物萌生,世界充满生机。太阳是生命的赋予者,万物的创造者和世界的统治者,太阳升上的雅拉香波神山自然成为世界的中心。“圣山的山峰也是天地的汇合点。天地之间的这一接触和这种联系是西藏人的信条,可以追溯到起源时代……第一批赞普的某些王后也享有暗示神山各种形状的名字。至今仍在山上举行季节性的仪礼形式和庆祝的特殊节日……”[45] 西藏群山环绕,人们生活在山的怀抱中,从直观上来看,太阳升起在山头,也落下在山上,大山成为太阳爬上或走下的阶梯,所以聂赤赞普天梯降临的神话是对太阳升上山头的形象类推的结果,并因此衍生出与太阳出现相关联的山的崇拜。“群山等同于最早的祖先下凡使用的梯子或者‘木’绳。而赞普的陵墓也被称为‘山’。”[46] 山的崇拜成为太阳崇拜的变形方式。“圣山……被看作是‘擎天之柱’或者是‘大地之钉’……被看作是联接天、地的木梯。”[47] 因此,“通过‘木神之梯’或‘木神之绳’即可攀天或下凡,而人们又认为梯子是一种具有彩虹颜色的光柱。人们有时也称之为‘风梯’,有时又认为它如同山一样,先祖和赞普就是从此山一阶一阶地下来的,此山实际为天柱。在高地(房顶或山顶)的供养神香的香气迫使天门开放”。[48] 在西藏的传统文化中衍生出山神、战神崇拜的风马旗和玛尼堆的仪式形式。“嘛呢堆代表山上的战神。”[49] “圣山也是战神,人们经常用一些意味著‘首领’或‘赞’(或者像古代赞普一样称为‘王’)的术语来称呼它。”[50] 而构成这些类比关系与象征体系的原型,是太阳的运行。也就是说,在太阳崇拜中,原始先民以太阳运行类推,把山、木神(绳)、天梯等认同为太阳。
聂赤赞普天神下凡的地方,叫“赞塘郭细”,其意为“赞普的四门平原”,迎请聂赤赞普为王的12人,按照藏族历史和传说的记述,“这12位土著头人被称为祭司、猎人、当地居民、12位国王或苯教祭司,圣人或氏族头人”,但“他们的数目与这一矩形地盘的方位是一致的”。[51] 在聂赤赞普所下降的地点上,神话都强调了地之方形的特点。而这个地之方形的特点与聂赤赞普的天神身份是紧密联系的,所以显然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客观描述。“那么,地方的观念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我以为是神话思维类比推论的结果。原始人根据从太阳运行所获得的四方方位观念,以为有限的大地在四个方向上均有尽头,因而大地也就被想象成四边形的实体了。”“再加细察,我们发现神话宇宙观中的所谓‘地方’并不是正方形,而是长方形的。”[52] 定居农业生产时代,太阳对人的生产和生活的重要地位,促发了原始人的太阳观测活动,依据太阳每天运行的轨迹,以“日出”为东,“日入”为西,日中的极处为南,于此相对的方向确认为北。“所以,原始人留下来象征太阳的符号往往是一些十字形,卍形或十形。”[53] 由此确定了东、南、西、北四个方位和地之方形的特点。因此,地之方形是由太阳运行的空间坐标类比推论出来的,地理的四方形象征了太阳运行的特点。同时,由于原始人的独特心理状况,“尚未建立自我意识的史前人把自己观测太阳定四方四时的主体能力反过来归奉成太阳的‘神圣赐予’,人的本质在幻想中异化为神的本质,太阳神崇拜便在农、牧社会中普遍发生了”。[54] 太阳在神话思维中被认为是地之方形形成的原因。因此,在聂赤赞普神话中,聂赤赞普下凡的地方,“赞唐郭细”意为“赞普的四门平原”,表面上看是因聂赤赞普而得名的,深层上显示了聂赤赞普在地之方形形成的法则作用,表明了聂赤赞普作为太阳原型的神话内涵。
根据藏文语义,聂赤赞普被称为“肩舆王”。直接的意思是,聂赤赞普下凡之后被众人用肩膀抬着拥立为王的。在这里,人的肩膀成为了王座,王座是统治权力的象征,人的身体成为政治文化赋形的载体。“所有的民族和文化都有一种随手可得的物体——它是无所不在的和可延伸的——可以承担象征负担,这就是身体。”[55] 文化的权力机制生成了身体的区分,右与左,上与下等,前者比后者更优越。这种区分的根本原因,在于太阳崇拜,换句话说,太阳原型的制约、规范形成了身体的文化表征。“崇拜者在他的祈祷和仪式庆典中,会自然地朝向太阳(万物之源)升起的地方。大多数神圣的建筑,尽管属于不同的宗教,但都朝向东方,以面对这个方位为基准点,身体的不同部位也指派为不同的方向,西方为后,南方为右,北方为左。结果天上的区域特征反映在人体当中。南方的充分的阳光照耀着我们的右边,而不吉利的阴影投射在我们的左边。自然的景观,白天和黑夜、热与冷的对比,都使人认识到左与右的区别,并将二者对立起来。”[56] 太阳崇拜仪式中的身体姿势,赋予身体的左与右不同的意义,并使右边有更为优越的地位。在西藏的原始信仰中,“居于右肩的战魂(dgra-bla)也称战神dgra-lha,是人的护身魂,如此魂离去,人也就死去了……除了战神外,还有居于右肩的男神”。《格萨尔王传》有关人体灵魂分布的描述,是把“位于人头部的灵魂”,称为“上魂”(rtshe-bla),“右肩为男神pho-lha,左肩为阴神mo-lha”。[57] 身体的右边和上部,或头部与右肩在藏族的萨满教信仰中居于更加重要的地位。藏族的传统礼俗禁忌中,不能拍打男孩的右肩,认为这样会把他的保护神赶走。“肩膀上停留着‘战神’和‘人神’。”[58] “藏文中的‘祖’[(g)tsug]有时也与神山和祖神有关,一般是意味着‘头顶’(前顶、颈背等)。”[59] “与石堆和圣山相联系的神分别叫作‘山顶上的神’‘地神’‘男神’或‘战神’,它们同样占据人的头顶、肩膀、坚强的头盔和屋顶上。”[60] 太阳的光芒照射在人的身体上,接近太阳的头顶和肩膀,具有了更为优越的地位,它是战神、男神、保护神,也是山神、祖神。战神、男神、保护神与山神、祖神因此产生了神话的认同关系,而这些同构性关系的建立是由太阳形象类比推论的结果。所以,聂赤赞普成为人间“肩舆王”的神话情节,也是太阳原型隐喻的表现形式。
在神话思维中,“不同的物体,只要它们的功能意蕴相同,也就是说,只要它们在人类的活动与目的的秩序中占据相同或至少相似的位置,它们就往往具有同一名称,归在同一概念之下”。[61] 从以上对聂赤赞普神话的分析可以看出,聂赤赞普的形象在神话中具有太阳在人类活动中一样的功能意蕴,可以说,聂赤赞普与太阳有着认同性关系。所以,聂赤赞普神话体现了太阳崇拜中积淀的原始先民的集体无意识。聂赤赞普神话在西藏的历史文化发展有着独特的意义:一方面,神话在原始时代具有实际的功能,在巫术仪式中,神话是原始巫术仪式的一部分,神话的引用是加强巫术效果,实现人类支配自然目的的方式。一旦神话从巫术仪式中游离出来,具有了独立性,也是规范人的行为和心理的原则、协调部落社会成员关系、强化集体身份认同的方式。“准确地讲述起源神话乃是‘维持世界秩序所必不可少的一种宗教行为’”,[62] 聂赤赞普的神话作为太阳原型的变形,使藏民族的起源具有着神圣性的特点,以其自然的高贵性,显示出区别于动物的人类特性。另一方面,太阳崇拜作为西藏早期宗教的形式,赋予太阳或光以本体论的地位。“居塞佩·图齐(Giuseppe Tucci)认为,西藏宗教体验的基本特征就是赋予光(不论它是一种创造性原则、一种至上存在的象征,还是一种看得见的、可感知的启示,或万物所从出、存在于我们心目中的光明)以极其重要的地位。对于所有喇嘛教派来说,精神(sems)就是光,这种等同构成了西藏灵魂解脱论的基础。”[63]
作为西藏关于祖先起源的神话,聂赤赞普神话反映了西藏原始先民以太阳为原型的集体无意识。对原始人来讲,只见到日出和日落是不够的,这种外界的观察必须同时也是一种心理活动,就是说太阳运行的过程应当代表一位神或英雄的命运,而且归根到底还必须存在于人的灵魂之中。至于所有的神话化了的自然过程,例如冬夏、月亮的圆缺、雨季等等绝不是客观现象的喻言,而是内在的无意识心理的戏剧的象征性表现,由投射的方式接近人的意识——即在自然现象中反映出来。”[64] 所以,在聂赤赞普的神话中,它以太阳的原始意象为基础,遵循类比推论的方式,以太阳在实践中相互接触、形式相似的事物为载体或表现形式,揭示了太阳在原始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在原始意识中的深层语法作用,对藏民族的起源做了象征性解释。
[1] 作者简介:
张学海,男,1968年生,陕西礼泉人。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学、美学。
[2]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王尧译,《王尧藏学文集》卷1,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年,第249-250页。
[3] 蔡巴·贡噶多吉:《红史》,陈庆英、周润年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9-30页。
[4] 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陈庆英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1-82页。
[5] 五世达赖喇嘛:《西藏王臣记》,刘立千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页。
[6] 石泰安:《西藏的文明》,耿昇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9年,第45页。
[7] 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论:《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84年,第206页。
[8] 叶舒宪:《神话——原型批评》,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2页。
[9] 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常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7页。
[10] 麦克斯·缪勒:《宗教的起源与发展》,金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70页。
[11]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中国藏地考古(一)》,成都:天地出版社,2014年,第250页。
[12] 张亚莎:《西藏的岩画》,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00页。
[13] 桑木旦·C. 噶尔梅:《概述苯教的历史及教义》,《喜马拉雅的人与神》,像茄红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年,第120页。
[14] 张亚莎:《西藏的岩画》,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15页。
[15] 叶舒宪:《英雄与太阳》,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4-65页。
[16] 李丽:《藏族宗教》,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第2页。
[17] 民族院校公共哲学课教材编写组编:《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和社会思想资料选编》,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154页。
[18] 洛桑·沙吉:《西藏阿里日土地区的婚姻习俗》,《喜马拉雅的人与神》,第213页。
[19] 蒋凤、王慈编:《中国少数民族谚语选》,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9页。
[20] 刘芳贤、李坚尚编:《珞巴族的原始宗教》,宋恩常:《中国少数民族宗教初编》,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22页。
[21] 张江华:《僜人的原始宗教及其社会影响》,《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
[22] 利普斯:《事物的起源》,汪宁生译,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2年,第328页。
[23] 利普斯:《事物的起源》,汪宁生译,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2年,第327页。
[24] 谢继胜:《藏族萨满教的三界宇宙结构与灵魂观念的发展》,《中国藏学》1988年第4期。
[25] 谢继胜:《藏族萨满教的三界宇宙结构与灵魂观念的发展》,《中国藏学》1988年第4期。
[26] 崔成群觉、却旺、陈宗祥:《古代藏族的测时仪器》,《西藏研究》1983年第3期。
[27] 民族院校公共哲学课教材编写组编:《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和社会思想资料选编》,第163页。
[28] 麦克斯·缪勒:《宗教的起源与发展》,第132页。
[29] 麦克斯·缪勒:《宗教的起源与发展》,第132页。
[30] 麦克斯·缪勒:《宗教的起源与发展》,第237页。
[31] 荣格:《集体无意识与原型》,马士沂译,庄锡昌、顾晓鸣等编:《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24页。
[32] 麦克斯·缪勒:《宗教的起源与发展》,第122页。
[33] P. E. 威尔赖特:《隐喻与现实》,叶舒宪:《神话——原型批评》,第227页。
[34] 麦克斯·缪勒:《宗教的起源与发展》,第170页。
[35] 叶舒宪:《英雄与太阳》,第248页。
[36] 叶舒宪:《英雄与太阳》,第106页。
[37] 姜亮夫:《楚辞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79页。
[38] 阿甫基耶夫:《古代东方史》,王以铸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56年,第120页。
[39] 叶舒宪:《中国神话哲学》,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26页。
[40] 米尔恰·伊利亚德: 《宗教思想史》第3卷,晏可佳、姚蓓琴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年,第1163页。
[41] 叶舒宪:《中国神话哲学》,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86页。
[42] 石泰安:《西藏的文明》,第43页。
[43] 石泰安:《西藏的文明》,第238页。
[44]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王尧藏学论文集》卷1,第238页。
[45] 图齐:《西藏宗教之旅》,耿升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第273页。
[46] 米尔恰·伊利亚德: 《宗教思想史》第3卷,晏可佳、姚蓓琴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年,第1164页。
[47] 米尔恰·伊利亚德: 《宗教思想史》第3卷,晏可佳、姚蓓琴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年,第1164页。
[48] 石泰安:《西藏的文明》,第249页。
[49] 石泰安:《西藏的文明》,第243页。
[50] 石泰安:《西藏的文明》,第240页。
[51] 石泰安:《西藏的文明》,第41-42页。
[52] 叶舒宪:《中国神话哲学》,第34页。
[53] 叶舒宪:《中国神话哲学》,第167页。
[54] 叶舒宪:《中国神话哲学》,第172页。
[55] 菲奥纳·鲍伊: 《宗教人类学导论》,金泽、何其敏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3页。
[56] 菲奥纳·鲍伊: 《宗教人类学导论》,金泽、何其敏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8页。
[57] 谢继胜:《藏族萨满教的三界宇宙结构与灵魂观念的发展》,《中国藏学》1988年第4期。
[58] 石泰安:《西藏的文明》,第263页。
[59] 石泰安:《西藏的文明》,第262页。
[60] 石泰安:《西藏的文明》,第242页。
[61] 恩斯特·卡西尔:《语言与神话》,于晓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第66页。
[62] 米尔恰·伊利亚德: 《宗教思想史》第3卷,第1163页。
[63] 米尔恰·伊利亚德: 《宗教思想史》第3卷,第1174页。
[64] 荣格:《集体无意识与原型》,马士沂译,庄锡昌、顾晓鸣等编:《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第31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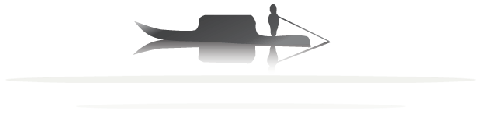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沈洁
The End
《上海文化》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 S S C I ) 扩展版来源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引文数据库来源刊
主办单位
上海市作家协会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