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化》| 名师学案
陈鸣树学案
符杰祥 |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黄乔飞 | 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
原文刊载于《上海文化》2017年第12期
内容摘要
陈鸣树先生为中国著名现代文学研究专家、鲁迅研究专家、文艺学研究专家。作为新中国学界的新生力量,其早期的鲁迅研究文章可谓一个时代曲折艰难的见证。新时期以来,他高屋建瓴,视野宽广,在继续推出众多鲁迅研究成果的同时,亦在文艺学方法论领域先后提出两极否定性原理、对应性原理等系列首创性概念,出色完成了一种跨学科、跨领域的开拓性探索。陈先生成就斐然,得益于他丰盛的文艺才情、深厚的理论修养与严谨的治学精神。无论何时,他的文章总能追随时代,也总能超越时代。
关 键 词 陈鸣树 鲁迅研究 文艺学 方法论
陈鸣树(1931—2014年),笔名澡雪,江苏苏州人。中国著名现代文学研究专家、鲁迅研究专家、文艺学研究专家。作为新中国学界的新生力量,其早期的鲁迅研究文章可谓一个时代曲折艰难的见证。新时期以来,陈鸣树高屋建瓴,视野宽广,在继续推出众多鲁迅研究成果的同时,亦在文艺学方法论领域先后提出两极否定性原理、对应性原理等系列首创性概念,出色完成了一种跨学科、跨领域的开拓性探索。陈鸣树在20世纪90年代主持编写了《20世纪中国文学大典》,该著是20世纪学术史料整理工程的典型展现。除此之外,陈鸣树在中国绘画创作及理论研究上也颇有造诣,洒脱自由的笔力与深厚沉潜的学识相辅相成,水墨丹青亦可自成一家。
一
陈鸣树先生于1931年10月,出生于江苏省苏州市一个破落商户家庭。早年丧父,因家贫中途被迫辍学。
1936年6岁,从报纸上剪下鲁迅先生出殡时的画像,以硬纸板粘贴放在床头,画像中“中国文坛巨子”的字样为其早熟的心灵开启了一扇启蒙的窗户,从而结下一生同鲁迅的缘分。
1949年前夕,任工厂学徒。从工厂老工人手中获得《鲁迅自选集》,开始了其自学历程。
1949年19岁,曾在苏州公安局等部门服务。其间因病在市府机关干部疗养所休养,广泛阅读文学书籍,并以《鲁迅全集》作为重点研读对象。
1954年24岁,结识江苏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朱彤先生,在其鼓励下在《人民日报》发表了第一篇文章。随后。于1955年在《文艺月报》上发表了长文《评许杰的反现实主义的“小说论”——关于〈鲁迅小说讲话〉的文艺理论部分》。
1955年25岁,因表现突出,被指定为新中国学术界的“新生力量”,受到中宣部领导垂访。之后被调入苏州文联,担任执行委员兼秘书,同时担任江苏省文联委员,华东作家协会会员(后改为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后调至江苏省《雨花》编辑部,负责理论组的工作。
同年,通过应试成为李何林教授的第一届副博士研究生,主攻鲁迅研究。李何林先生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重要的奠基人之一,对他的影响颇为深远。
1956年26岁,参加第一次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听取周恩来、胡耀邦的报告,并加入上海作协,与唐弢结识,并自许为其私淑弟子。
1959年29岁,在副博士研究生在读期间,陈鸣树出版了其第一本专著《保卫鲁迅的战斗传统》,该著是政治运动的典型产物。
同年,《论鲁迅小说的艺术方法及其演变》在《上海文学》连载3期,受到王元化先生的赞赏,并推荐给筹拍《鲁迅传》的主角赵丹阅读。上海文艺出版社文艺理论室周天写信鼓励其拓展成书,但最终并未落实。
1961年31岁,调入上海作协文学研究所。
“文革”期间,受到政治冲击的陈鸣树编写了一本《鲁迅的批儒反孔斗争》,同时因身体状况不佳被安排在上海市作家协会看守大门,免于下乡劳动改造。
1975年45岁,经李何林教授提名,调至北京鲁迅研究室参与《鲁迅年谱》的编写工作。
1976年46岁,完成《论鲁迅小说的典型化》一文,总计4万字,分两期发表于刚创刊的《社会科学战线》上。自此,其学术道路回到正轨。
1977年47岁,陈鸣树主动申请从北京调离,进入复旦大学任教。先在历史系中国思想史研究室担任蔡尚思先生的助手。在此期间发表文章《论鲁迅“五四”时期的思想》,从思想史脉络梳理鲁迅的精神气质。随后在校党委书记夏征农的建议下,在中文系成立鲁迅研究室,后改名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室,陈鸣树在此担任主任直至退休。
1981年51岁,出版鲁迅研究代表作《鲁迅小说论稿》(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2年52岁,出版普及性质的《鲁迅杂文札记》(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4年54岁,出版鲁迅研究论文集《鲁迅的思想和艺术》(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5年55岁,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4期发表《鲁迅研究史上的丰硕成果——三本鲁迅专著的学习札记》。
1986年56岁,在《学术月刊》第10期发表论文《鲁迅:中西文化冲突中的选择》,该文在上海市纪念鲁迅逝世50周年大会上宣读,并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学术成果奖。
80年代末期,陈鸣树在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进修素描。
90年代初期,与著名作家王小鹰拜国画名家王康乐为师。
1991年61岁,在鲁迅诞生110周年之际发表《论鲁迅的智慧》一文,在《文化报》《鲁迅研究月刊》《鲁迅研究年刊》等多处转载。
同年,《文艺学方法概论》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1994年64岁,主编完成《20世纪中国文学大典》3卷(上海教育出版社)。同年,《现象学美学方法述评》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学术成果奖。
1996年66岁,《浩气千秋民族之魂——纪念鲁迅逝世60周年论文集》收录其文章《20世纪初期鲁迅的人文精神》。
2004年74岁,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文艺学方法论》(第二版)。
2011年81岁,由上海鲁迅纪念馆和复旦大学出版社共同发起“《鲁迅论集》首发式暨陈鸣树教授80华诞庆祝会”,在上海鲁迅纪念馆召开。
2014年84岁,7月18日因病于上海逝世。
二
陈鸣树年少成名,24岁便于《人民日报》发表了其关于鲁迅研究的第一篇文章。此后,他相继编撰完成了14部学术著作,可谓成果丰硕。纵观其学术发展脉络,大体可以划分为两大领域和4个时期。两大领域集中于鲁迅研究和文艺学方法论研究;4个时期主要指50年代的成长期、60—70年代的沉寂期、80年代的高峰期、90年代以后的拓展期。
在1959年的特殊年月,尚在南开大学读书的陈鸣树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专著《保卫鲁迅的战斗传统》。该书无可避免地具有政治运动的时代印痕,对此,陈鸣树并不讳言,著文明确表示“悔其少作”,晚年也一直坚持自我批判。与巴金的《随感录》一样,不回避历史污秽的文字,反而能呈现出人格的高洁。但同时,书中亦不乏将鲁迅文学自觉放置于审美维度上进行观照的精美篇章,尤其是鲁迅与拜伦的比较研究、鲁迅与儿童文学的译介研究,无论是文风还是观念,对政治禁锢严峻的年代来说已是难能可贵的学术突破。在“文革”前后的极端年代,陷入沉寂期的陈鸣树也在革命文化自我消解的大潮裹挟之下,编写过两本《鲁迅批孔杂文选讲》(1975年)、《鲁迅批孔反儒的斗争》(1976年)小册子。
新时期以来,陈鸣树的鲁迅研究也在思想解放的大潮中回归正轨,完成了一系列鲁迅研究成果,成绩卓著。出版的著作包括《鲁迅小说论稿》(1981年)、《鲁迅杂文札记》(1982年)、《鲁迅的思想和艺术》(1984年)。同时,作为年谱组召集人参与了《鲁迅年谱》(1984年)的编撰工作。陈鸣树的学术研究一方面注重对史料的征引发掘,一方面又保持着阔达的知识理念。从鲁迅小说到鲁迅杂文,再到鲁迅思想和艺术价值,陈鸣树通过一系列论著,将个人对鲁迅的认知构建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这些论著,摆脱了5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庸俗社会学的桎梏,显示着新时代的思想深度与学术高度。在这其中,陈鸣树关于鲁迅小说典型化及艺术辩证法,鲁迅美学思想与思想史地位、鲁迅在中西文化冲突中的抉择与中国主体性问题的探讨,高瞻远瞩,思辨缜密,可谓巅峰之作。
在文艺学领域,陈鸣树的专著有《文艺学方法概论》(1991年)和《文艺学方法论》(2004年)。《文艺学方法论》在2004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是在修订1991年《文艺学方法概论》的基础上完成的。书中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文艺学方法论的原理与实践问题,共分为三部分。上篇为“方法论:原理”,具体阐述了研究方法的对应性和两极否定性原理、层次性原理、互补性原理;中篇为“方法论:中国与世界”,介绍并分析了社会学、心理学、新批评、原型批评、解构主义等10余种方法及其优劣;下篇为“方法论:实践功能”,重点关注的是文艺学方法中的发现机制、资料的实证性与思维的超越性、理论框架的构建原理等问题。三部分由原理而实践,并不满足于西方理论的译介,其中三大原理、三大功能,是陈鸣树独具创建的理论提升与学术归纳,显示出其深厚的文史哲修养与中国问题意识。
90年代以后,陈鸣树的学术思想基本成型,其主要的工作集中于学术思想的整合梳理。1994年,由陈鸣树主持编写的《20世纪中国文学大典》出版发行,这是20世纪学术史料整理工程的重要成果。2011年,《鲁迅论集》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该书收入了陈鸣树不同时期鲁迅研究的学术文章,既是一种个人研究成果的整理,也是一种鲁迅研究史的总结。
90年代末至21世纪,陈鸣树兴趣转移,重心移至书画艺术,在中国绘画创作和研究方面也颇有成绩。陈鸣树的生平事迹先后入选英国剑桥传记中心《世界知识分子名人录》《杰出的人》,美国传记学会《世界5000名人录》及国内《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等多种辞书。
三
从50年代以鲁迅研究年少成名,到新世纪结集出版《鲁迅论集》,陈鸣树毕生的鲁迅研究,或起或伏,或兴或止,贯穿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从历史意义上说,陈鸣树辗转于不同时代的鲁迅研究,可谓当代中国文化政治演变的缩影,也可谓当代中国学术发展曲折艰难的见证。
在陈鸣树最早的著作《保卫鲁迅的战斗传统》中,包含有许多大批判文章,这无疑是政治运动裹挟中的产物。个人终究无法跳出时代的限制。就此而论,本书的局限,也是时代的局限;个人的学术悲剧,也是时代的学术悲剧。但同时,在一种时代的扭曲生长中,陈鸣树的早期著作也显示出无法压抑的学术才华。在《论鲁迅初期美学思想》一文中,陈鸣树结合神话的溯源理论探索鲁迅创作的审美源头,对鲁迅文学中“涵养人之神思”的美学情怀给予了高度关注。同时,他对鲁迅笔下“温煦”与“刚健”美学特质的提炼,深入肌理,部分超越了阶级话语的刻板描述。新世纪以来,郜元宝的《鲁迅六讲》以对鲁迅早期文章中的“神思”“白心”等概念的精彩阐发而备受赞誉,堪称经典。对照陈鸣树在思想高度统制时代对鲁迅美学思想的艰难探索,其才华的敏锐与埋没,不能不让人心生感慨。
书中另一篇文章《鲁迅与拜伦》亦值得注意。世界性的比较眼光、影响研究的范式,在这部早期著作中已有所体现。陈鸣树探究的问题是:鲁迅如何吸收拜伦的积极抗争思想,并将其熔铸在自己的精神品质和文学创作之中。他发现了拜伦式英雄反抗强力的高傲精神与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心灵共鸣,指出拜伦与鲁迅共同的反叛热情不在于侵略弱小,而是“一方面摈斥侵略政策,一方面反对不抵抗主义”。[2]陈鸣树的研究初步揭示了跨文化语境下鲁迅的主体性特质。这是国内第一篇鲁迅与拜伦的研究文章,这样的发现无疑也是具有开创性的。在国外,较早研究鲁迅与拜伦关系的是日本学者北冈正子,其首篇《〈摩罗诗力说〉材源考笔记》直到1972年10月才刊载于《野草》第9号上。其后,日本学者藤井省三发现了安德烈耶夫对鲁迅和夏目漱石创作的影响,并认为鲁迅关于拜伦的材源除了木村鹰太郎的《拜伦——文艺界之大魔王》之外,还受到了诗剧《该隐》中恶魔的影响。不过,这一研究也是迟至1985年才在《俄罗斯之影》上发表出来。就此而言,陈鸣树的比较研究,即便在世界范围内,也具有首创意义。再如《鲁迅与儿童文学》一文,亦有先行性的价值。陈鸣树较早将文学译介引入研究范畴,发现鲁迅在儿童文学译介中并未坚持其一贯坚持的“硬译”主张,这种差异与矛盾,其实是体现了“救救孩子”的热爱与关怀的。
陈鸣树在鲁迅研究中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战斗情怀和“保卫鲁迅”的极大热忱,这其中有政治语境的印痕,也有导师李何林学术精神的引导。在近60年的学术生涯中,李何林始终坚持“五四”新文学的战斗传统,矢志不渝地发扬鲁迅精神。对李何林来说,鲁迅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巨大的精神符号,既是研究对象,也是学术信仰。在两部早期论著《中国文艺论战》(1929年)和《鲁迅论》(1930年)中,李何林即流露出鲜明的爱憎与是非,“保卫鲁迅”的立场同时也形成了其最为突出的两种学术特征:鲁迅视点和论战思维。在30年代,李何林曾公开发表两篇论战文章:《叶公超教授对鲁迅的谩骂》与《为〈悼念鲁迅先生〉——对大公报“短评”记者及其侪辈的愤言》,这在当时引起了极大轰动。在1939年出版的《近20年中国文艺思潮论》一书中,李何林更是言辞激烈地声讨了左翼阵营中的小团体作风,并将鲁迅作为革命阵营的“代言人”,突出其至高地位。同样,李何林在1959年发表的《十年来文艺理论和批评上的一个小问题》一文,也是因为坚持鲁迅传统而遭到批判。
《保卫鲁迅的战斗传统》一书中批判性的文风及充满战斗性的内容与李何林一脉相承。正如陈鸣树在《李何林教授对鲁迅研究的贡献——为祝贺先生八十寿辰作》一文中所言:“先生从青年时代开始,就不计个人利害,以精卫填海的精神,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着、战斗着、生活着。这也是先生的精神最令人感动、最值得后学师法的地方。”[3]不过,陈鸣树在早期的研究中仅仅关注到鲁迅战斗精神与政治语境中斗争意志同构的表象,而没有关注到其背后概念的替换以及政治掌控文学的问题所在。在这一点上,时为学生的他尚缺乏李何林更具前瞻性的问题意识与相对独立的怀疑精神。这一时期的学术文章,许多是盲从政治运动的跟风书写,理念化、口号化的意识形态色彩过于浓厚。在政治斗争的纠缠与裹挟中,青年陈鸣树并没有完全摆脱时代的政治束缚,甚至迷失其中。在恩宠有加的鼓励之中,他的文艺才华被弯曲与利用了。比如批判冯雪峰的那篇《一个个人主义心目中的鲁迅》,就是在周扬的授意和叶以群的指派之下写出来的。即便是在论述鲁迅与拜伦关系这样出色的文章中,陈鸣树也存在诸多缺陷。比如认为鲁迅笔下“孤独者”失败的原因是个人主义者的自我毁灭,而忽略了鲁迅对拜伦式英雄的同情与赞美,这是以意识形态的偏见,遮蔽了鲁迅文章自身的光华。
鲁迅研究被意识形态所主导,甚至沦为一种政治斗争的工具,是学人个体的迷失,也是时代集体的迷失。陈鸣树有着超越于时代的才华,敏锐的学术观察力使他能够突破时代,发现文学的“人学”特性。1961年完成的《论鲁迅小说的艺术方法及其演变》一文,是一篇代表性力作,因而得到王元化的赞赏和推崇。在高压环境中,没有人能够确保自身不被异化,在异化的时代里保有最后一点人性之光,都是难能可贵的。在那个狂热的年代,陈鸣树的学术道路艰难而扭曲。一方面,被政治运动消磨了才华与热情;另一方面,那难以扭曲或未曾消磨的一部分,也保留了政治风暴中最后一点学术才情与人格尊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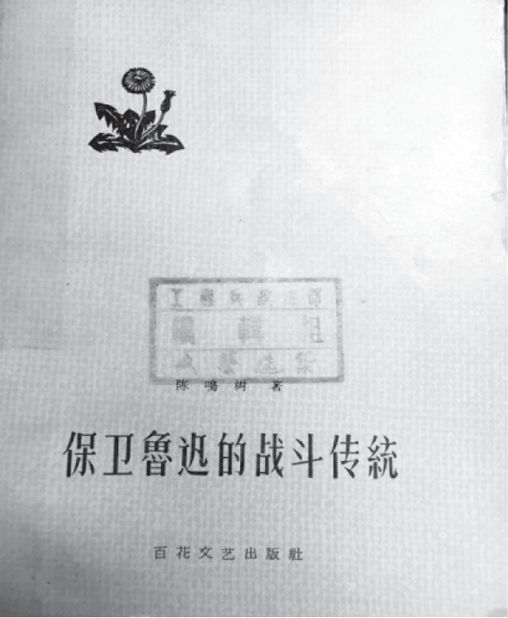
图1 《保卫鲁迅的战斗传统》
四
“文革”之后,陈鸣树的学术研究逐渐回到正轨。1981年,他的《鲁迅小说论稿》出版,有评价说:“它相当全面地触及了鲁迅小说的各个方面,自成系统,而且在体例上,兼得论文之深入与专著之系统两方面之长。”[4]该书在前人的基础上,以更为严密的论证逻辑、更为深入的文思,构建了具有个人气质的研究体系。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综合研究法的运用。
综合研究法最早的提出者是王元化。针对80年代译介西方思潮中急功近利的理论热与方法热,王元化明确指出应当坚持“古今结合、中西结合、文史哲结合”。陈鸣树吸收了其综合思想的精华,在《鲁迅小说论稿》中,他构建了两组嵌套结合的分析模式。
其一,历史视野。他将鲁迅小说创作放置于宏观的时代背景和历史进程中,探索文本间的内在联系。比如在探讨《呐喊》和《彷徨》这两本小说集时,他没有将文本中农民命运的凄苦、知识分子的彷徨、革命青年的无助作为单独的研究对象,而是将文本内容与时代特质相结合,创作风格与艺术方法相参照,从中得出的结论不是单面割裂的片段化呈现,而是具有史学视野的开放性总结。在《论鲁迅小说的艺术辩证法》一文中,他认为:“鲁迅小说的艺术方法的演变,正是标志着‘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向社会主义文学过渡的光辉范例;也就是带有新民主主义革命色彩的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以及这两者相结合的艺术方法,向社会主义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方法过渡的光辉范例。”[5]这样一种提法,让我们关注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发端问题,是审美感受和理性逻辑相结合的产物。
其二,世界眼光。陈鸣树关注的是鲁迅将民族主体性与外来“新主义”相结合的辩证思考。书中提到:“他一刻也不离开中国的现实去思考‘新主义’。他特别着眼于中国人怎样去接受‘新主义’。”[6]陈鸣树发现,鲁迅在吸收新文化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对本民族文化的自觉内省。鲁迅赞颂俄国人民迎来新世纪的曙光,出发点不是以“新主义”作为全盘吸收的对象,而是借此反思中国的国民性问题。在陈鸣树的论述中,鲁迅看到了未来的光明,但并没有脱离现实。再如解读《理水》时,陈鸣树发现,鲁迅所塑造的大禹不再是个人式的英雄,而是有一群同向同心的伙伴,这显示了鲁迅晚年回归本土、探求民族内部原生力量的一种新倾向。内外两套分析模式相互融合,使得《鲁迅小说论稿》突破传统的文本解读,走向更为圆融的综合性分析。

图2 《鲁迅小说论稿》
在80年代“解放思想”的启蒙思潮中,李何林的另一位弟子王富仁教授率先提出“回到鲁迅那里去”,可谓当时最响亮的启蒙号角。陈鸣树在1982年出版了新著《鲁迅杂文札记》,在某种意义上也正是对回归鲁迅本体的一种南北呼应。《鲁迅杂文札记》有意摆脱多年来将鲁迅作为注脚的意识形态化表述,对过去的固有概念和陈腐的思维模式亦有所反拨。在书中,陈鸣树概括了鲁迅杂文的四大重要特质:“一、总结了革命斗争的经验;二、映照出‘时代的眉目’的‘史诗’;三、描述社会风貌和心理特征;四、参与文化思想的斗争。”[7]同时,本书从文学史的意义揭示了鲁迅杂文的诸多创造性,诸如古典散文与史笔传统的发扬,史论、随想录、漫笔、日记、絮语等众多形式的文体创新,文白杂糅、庄谐兼具等语体风格的原创等。这些研究和总结,极大地丰富了鲁迅杂文研究的维度,从文体到笔法都进行了全面而自觉的历史回溯。但正如他本人所言,限于普及性质,“这些概括,还不免皮相”,部分论述点到为止,尚待展开。

图3 《鲁迅杂文札记》
90年代以来,陈鸣树的学术兴趣发生转移,但鲁迅研究仍是其重心所在。相比于80年代的系列论著,这一时期并不高产,但思想更为成熟,视野也更为开阔。计划中的《鲁迅智慧论》无暇完成,但相继发表了《论鲁迅的智慧》《论鲁迅初期的美学思想》《论鲁迅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论鲁迅的辩证法思想研究提纲》《鲁迅:中西文化冲突中的选择》等系列文章,皆立论高远,视野宏阔。其中所提出的种种创见,如鲁迅的智慧学、鲁迅的“神思”说、鲁迅的“中间物”等命题,高屋建瓴,洞幽烛微,眼光独到,思辨深刻,对推动鲁迅研究的深入发展,具有深远的启示意义。王吉鹏等在2004年出版《鲁迅的智慧》一书,便直言是在陈鸣树《论鲁迅的智慧》一文启发之下完成的。如前所论,青年学者郜元宝教授在新世纪出版的《鲁迅六讲》,其中关于心学与神思的大力阐发,亦有陈鸣树早年《论鲁迅初期的美学思想》一文的观点闪烁与思想呼应。
2011年,复旦大学出版社为陈鸣树出版了72万字的《鲁迅论集》,陈鸣树自视为“告别人生,谢奠学术”的“封笔之作”。[8]这本书是陈鸣树鲁迅研究成果的完整结集,也是毕生心血的最后凝结。在评述鲁迅的文化思想时,陈鸣树曾指出:“如果说,鲁迅在文化选择上,早期有一种‘返顾旧乡’的寻根意识,中期还有一种由返激力所引动的急遽心态,那么,在后期,就显得从容周详,应付裕如,完满地体现了理性认知的主体意识。”[9]以此来反顾陈鸣树贯穿一生的鲁迅研究,其文章境界由早年一种锋芒毕露的批判论战与自我迷失,最终实现一种理性升华与主体意识的完成,其文其人,也何尝不是如此。
五
陈鸣树在新时期以来另一重要领域是文艺学方法论。80年代的理论热与方法热,基本是西方文论的介绍与译述。中国学者所面临的一个最为迫切的问题,就是如何不再亦步亦趋,转而能够从本土丰富的文艺史中攫取养分,在参透西方理论的同时建构符合当代中国实际的文艺学方法论。陈鸣树是现代文学专业的学者,却别具只眼,最早自觉意识到了文艺学领域的这一问题,跨界钻研,孜孜以求。陈鸣树最为重要的理论著作——《文艺学方法概论》是探索这一问题的最终成果,虽未完全解决问题,但却率先从哲学高度探讨了文艺学方法的内在逻辑与思维原理,其价值不可轻忽。
《文艺学方法概论》在1991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在这部著作中,陈鸣树纵横挥洒,介绍了中西14种文艺学方法。这些理论在被中国学界接受几十年后,现在看起来已不再陌生与新鲜,但陈鸣树的超越之处就在于,他以自身深厚的文史哲修养,将文艺学方法论问题的讨论,自觉提升到一种哲学层次。在从哲学层次探究文艺学方法背后的思维与机制问题过程中,陈鸣树创造性地提出了自己的系列原创性命题,比如“两极否定性原理”“层次性原理”“发现机制的逻辑行程”等,这在“方法论热”盛行的80年代,无疑是一股清流。
在该著中,陈鸣树首先关注到的是方法背后的思维原理与机制问题,这对于以往习惯以经验论的方式理解西方文论的中国学界来说,无疑是极大的突破。陈鸣树在书中提出:“所谓文学本性,即是文学的客观构成性。它的客观构成性是一种事实而不是一种猜想。”[10]因此,文学要回归到生活之中,要从文本结构本身出发去设定其理论结构。从文学本体论出发,该著引出了3种范式:文学本体的本质分析演衍了文艺理论方法,文学的历史发展演衍了文学史方法,文学的社会影响的判断行为演衍成文艺批评方法。[11]这就使文艺学方法论的思考,重新回到理论衍生的内在层次,即是什么促成了不同方法的出现,方法出现过程中的思维模式是怎样的,呈现出怎样的特质等问题。该书中的上篇《方法论:原理》和下篇《方法论:实践功能》,都对这些问题提供了建设性的论证。从该书的结构也不难看出,陈鸣树并不满足于14种文艺学方法的评述,而试图要提供一种新的思想维度,探究原则性或原理性问题。
在陈鸣树看来,唯有界定方法的属性,才能够判定和选择一种恰当的方法。因此,他首先确立了“方法对应性两极否定性原理”。在谈到方法对应性时,他认为应当遵循对象第一义、方法第二义的准则。正如别林斯基所说:“批评总是跟它所判断的现象相适应的,因此,它是对现实的认识。”[12]因此,文艺学方法的运用,需要回归到主体,从唯物主义的基点做出合理、恰当的判断。但对象和方法的地位又不是绝对的先后顺序,陈鸣树在方法的否定性原则中补充说明了这一点。在他看来,文学的发现机制有其特殊性。新的逻辑起点很大程度上也受到前人观点的启发,学术研究的目的一在整理前人成果,二在突破前人经验,因此理论和方法是一种触发的机制,不应当回避理论创造的可能性建构。在倡导思想解放的新时期,社会变革引发对庸俗社会学与教条主义的巨大冲击,人们对大量涌现的新鲜理论成果如饥似渴,却忽略了理论热潮背后更为重要的理论建设及其机制原理问题。陈鸣树的学理态度与学术观念,对于80年代中国而言是难得一见的清醒与突破。
在陈鸣树看来,经验研究只能把握住规律的冰山一角,借用黑格尔的话来说:“经验主义力求从经验中,从外在和内心的当前经验中去把握真理,以代替纯思想本身去寻求真理……如果老是把知觉当作真理的基础,普遍性和必然性便会成为不合法的,一种主观的偶然性,一种单纯的习惯,其内容可以如此,也可以不如此的。”[13]因此,在进行理论运用及创造的过程中,逻辑的思维进程可以促成作品真谛的发掘,而思维需要3个层次——“感性、知性、理性”来完成一次旅行。感性,是针对个别对象,以最为深情的方式进行意义的丰富性拓展;知性则处在方法的中介位置,这是一种形成概念的能力;而理性则可以达到对对象最为深层的认识,它能够增进思想的增值和扩容,同时促进思想群落的产生。对于这一问题的认知,陈鸣树无疑走在时代的前列。他不仅看到了理论背后的思维层次问题,更提出了“理论热”应该向何处去的思考。正如许明先生所言:“80年代文艺学方法论的讨论匆匆略过,除了介绍几种新方法外,似乎对方法问题的基本理论问题没有什么触及,在80年代末极少数有哲学素养的学者意识到了方法热热不下去的问题。陈鸣树先生就是其中一位。”[14]
作为一位跨界学者,陈鸣树的文艺学理论也融入了鲁迅关于“中间物”的思考。他将文艺学方法视为主体与客体间的“桥梁”,并指出:“由文学本性推演出的理论框架,是文艺学方法论确立的前提,是寻求文艺学方法论本体内涵的可靠方法。”[15]文艺学方法不再作为架空的理论,而是参与到完整思维过程的建构,它没有凌驾于文本或读者之上,而是作为贯通主客的“当下”存在,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陈鸣树回顾了中西文艺学方法论的历史,归纳出中国文艺理论的特质是内省、直觉、主情、鉴赏;而西方则是外察、体验、主智、分析。这样的总结是一种思维方法,也是一种历史意识。
《文艺学方法概论》的出现,改变了以往文艺学专著对某一种外来方法的述评与译介模式,转而开始关注哲学思维方法的探索。陈鸣树在书中提到文艺学研究的3个阶梯:“即一般方法、特殊方法和具体(个别)方法。一般方法是最高层的方法,即思维方法或称哲学方法,特殊方法即运用到文学这个领域的各种方法,具体(个别)方法即适用于各别具体研究对象的方法,也可称之为实用方法。”[16]3个阶梯的研究方法如果缺失了第一层次的铺垫,则无法建设更为牢固的理论主体,一部文艺学著作如果忽略了思维方法的指导,而单纯停留在各种特殊理论的普及之上,无异于背离了理论研究的初衷。因此,陈鸣树从黑格尔出发,以理性思维作为逻辑主线,延展至马克思主义的理性思维模式,从哲学高度对文艺学方法论进行深入探讨。陈鸣树认为,文艺学方法论的展开必须以文学本体为据,因为文学来源于生活,所以无可避免地会同外部社会发生一系列联系,从而产生历史方法、传记方法、社会学方法等研究模式。与此同时,文学具有相应的意识形态与语言结构、审美意蕴层,为结构主义、符号学、美学、心理学、语义学研究模式提供了活动园地。陈鸣树打破方法之间新旧割裂的绝对化与简单化,“主张从文学本性出发引申出方法论的多元化,并且认为,方法只要切合对象,就没有新旧之别”。[17]这样,陈鸣树在《文艺学方法概论》中不但明确了文学研究方法的来源是文学本性的自由延展这一主张,同时让传统与现代理论找到一个平衡共处的开放空间,既大胆吸收新的研究方法,同时又容纳传统理论的合理表达。该书出版之后,引发了学界热烈的反响。石韫玉赞其“高屋建瓴,体大思精”,金学智誉其为是“一部‘智慧学’的书”。许明对该书的理论价值,则作出了更为系统的归纳与概括:
1. 在总体构思上,起点高。在研究意图上,该书展开的是元方法(方法的出发点)探讨,而不是某种方法的架构或运用。
2. 创造性地对文艺学方法的原理进行了设定,这是在文艺学研究中具有首创精神的。
3. 将知识增值和发现逻辑的问题引进了文艺学研究,并形成自己颇具吸引力的解释。[18]
2004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文艺学方法论》第二版,足见该书的学理价值与学术重量。过去主攻现代文学的陈鸣树能够在新的文艺学领域开花结果,这也再次说明:“一个人文学者必然要打破单一的学科分界,以广泛的兴趣贯通相关学科才会有所收获。”[19]只有打通学科之间的壁垒和屏障,拓宽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在交叉思维的互补中,才能更好实现学术研究的综合提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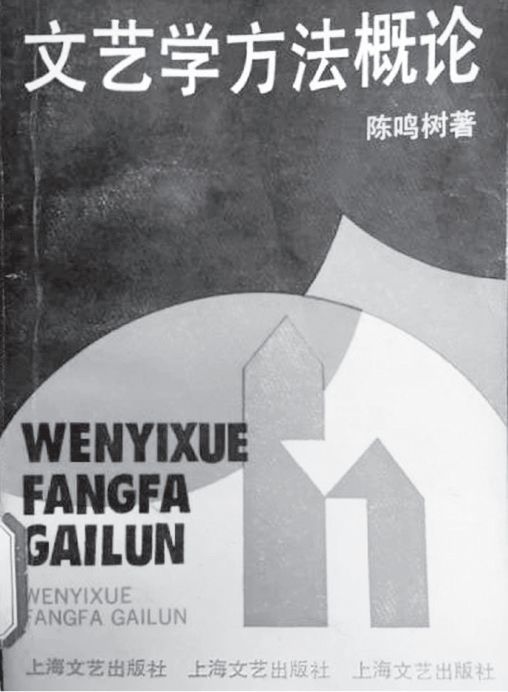
图4 《文艺学方法概论》

图5 《文艺学方法论》
六
陈鸣树成就斐然,得益于他丰盛的文艺才情、深厚的理论修养与严谨的治学精神。
陈鸣树在著作中有一句评点鲁迅的著名的话:“千古文章未尽才”,曾被钱理群先生大加欣赏而实行“拿来主义”,在致陈鸣树70寿诞的贺信中加以引用。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作为陈鸣树一生的写照。从年少成名,到中年颠簸,再到晚年跨界,陈鸣树的一生有众多未尽之才,但也留下了许多妙笔佳作。在笔者的感觉中,陈鸣树骨子里是一种浸染着江南文化的风流才子。只有风流才子,才会在不同时期展露文章才华,尽得时代风流。无论何时,陈鸣树的文章总能追随时代,也总能超越时代。即便在政治化的时代,先生的才情并未被完全束缚,他论鲁迅的文章,如抒情篇章,现在看来仍有启发。抒情论题近年被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大力发挥,认为是开辟了现代文学在启蒙、革命之外的一条新路。看看陈鸣树在那个革命化的时代,即有对鲁迅文章抒情才华别有会心的发现与洞见,再看看王德威教授在后现代主义时代的异域研究,不能不佩服陈鸣树的先见之明。先生无法挣脱时代的裹挟,但时代却也无法完全裹挟先生。即使在现代学术普遍凋败的年代,他仍然可以凭借个人一己的感悟写出成功的文章。[20]陈鸣树后期由鲁迅研究而文艺学、由方法论而书画艺术,跨多种学科而各有成就,看似偶然,实乃必然。
[1]作者简介:符杰祥,男,1972年生,山西临猗人。文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黄乔飞,男,1994年生,湖北赤壁市人。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研究生。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鲁迅手稿全集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号:12ZD167)的研究成果。
[2]陈鸣树:《保卫鲁迅的战斗传统》,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59年,第283页。
[3]陈鸣树:《李何林教授对鲁迅研究的贡献》 ,《南开学报》1984年第5期。
[4]滕云:《对鲁迅小说进行综合研究的一本新著——评陈先生〈鲁迅小说论稿〉》,《文学评论》1982年第4期。
[5]陈鸣树:《鲁迅小说论稿》,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第137-138页。
[6]陈鸣树:《鲁迅小说论稿》,第7页。
[7]陈鸣树:《鲁迅杂文札记》,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12页。
[8]杨剑龙:《思想史、文学史视域中的独特建树——读陈鸣树先生的〈鲁迅论集〉》,《上海鲁迅研究》2012年第3期。
[9]陈鸣树:《鲁迅:中西文化冲突中的选择——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五十周年》,《学术月刊》1986年第10期。
[10]陈鸣树:《文艺学方法论概论》,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1页。
[11]黄昌勇编:《陈鸣树先生纪念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80页。
[12]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3卷,满涛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第575页。
[13]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16页。
[14]许明:《渴望突破的契机》,黄昌勇编:《陈鸣树先生纪念集》,第186页。
[15]陈鸣树:《文艺学方法概论》,第33页。
[16]陈鸣树:《文艺学方法概论》,第75页。
[17]陈鸣树:《文艺学方法概论》,第53页。
[18]许明:《渴望突破的契机》,黄昌勇编:《陈鸣树先生纪念集》,第185页。
[19]许明:《渴望突破的契机》,黄昌勇编:《陈鸣树先生纪念集》,第187页。
[20]参见符杰祥:《病中的先生》,黄昌勇编:《陈鸣树先生纪念集》,第155页。
责任编辑:沈洁
The End
《上海文化》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 S S C I ) 扩展版来源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引文数据库来源刊
主办单位
上海市作家协会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