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江服务导报》曾经是飘荡在上海街头的一道风景线。它的“发现上海”专栏,一度打开城市的“褶皱”,在现实和想象的都市空间中,寻找上海的“魂灵头”,数次引发沪上百姓的热议,是上海城市精神和城市文化的有机构成。如今的媒介生态已经发生重大的变化,自媒体势不可挡,“媒介占有”似乎已然倒向“大众的占有”,但回望《申江服务导报》“发现上海”的点滴历程,依然可以在当下的媒介话语中找到诸多“未完待续”。本期“斯文在线”推送孙玮教授文章,按图索骥,开启一次“上海漫游”。
引言
《申江服务导报》(以下简称《申》报)是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报业集团中以都市消费为主要内容的周报。在2007年《申》报创刊十周年的特刊中,主编在卷首语中声称,“‘发现上海’是《申》报的一向担当,……作为一份上海报纸,应该成为这座所生所居城市的精神守望者”。“发现上海”是《申》报众多栏目中的一个栏目,这个栏目在《申》报中的特殊性在于,它背负了一份地方报纸与本地文化连接的责任。在《申》报上海开埠160年的特刊中,主编在简短的开篇文章中特别提及的栏目只有“发现上海”,“关注上海,是《申》报从创刊就开始的一个传统,从‘珍藏上海’专版到‘发现上海’栏目,……《申》报一直试图不负‘申’名,成为名副其实的上海价值发现者”。“发现上海”,在《申》报发展中后期逐渐成为整个报纸定位的关键理念。
“发现上海”栏目“发现”上海的视角是多样化的,包括方言、人物、历史、文学、艺术、新闻,等等。其中,都市“空间”元素被突出强调,成为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线索。都市空间中的主要元素如公园、广场、街道、建筑、河流、博物馆等等,成为栏目表现上海最重要的主题频繁出现。这个以都市空间“发现上海”的思路逐渐演变成整个报纸的一种取向。在《申》报十年的发展历程中,空间元素逐渐成为最重要的视角之一,在报纸历次重大事件特刊中被突出强调。2001年新世纪特刊以地理学意义上的重要元素河流为主题,将“苏州河”作为串联上海的历史、社会、现状的中心线索;2003年上海开埠160年特刊主题为“从老外滩到新天地”,直接以具有特殊意义的地方名称反映上海的空间变化,以统合上海160年以来的历史变迁。2007年《申》报十周年纪念特刊中,以“十年大空间”作为特刊第一板块,梳理上海十年间在城市空间方面发生的变化:空间设计是形而上的,但却是以形而下的生活为目的。“发现上海”栏目的责任编辑吴驷称,在此栏目的十年发展史中,经历过一个“空间转向”的过程;作为栏目的策划人,他逐渐自觉地将“空间”元素作为“发现”的最重要手段。而之所以出现这个转向,出自一个非常偶然的原因,一位建筑师建议他可以从空间的角度发掘上海作为一个都市的特质。后来这个建议逐渐演变成这个栏目的众多关于上海空间的系列内容,都市“空间”也成为“发现上海”最重要的操作理念。

本文以《申》报“发现上海”栏目及《申》报发展十年中的重要特刊为研究对象,集中于其中的“空间”主题,依据上述相关空间理论为框架,以“空间生产”为核心概念,描述并阐释《申》报作为一家地方性媒介如何进行都市空间的生产,这种生产怎样建构了一种“上海人”的集体想象。本文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地方媒介怎样通过都市空间的生产在地方文化的发展中扮演一个特别的角色。本文认为,在“发现上海”名义下进行的媒介都市空间生产,在建构都市公共空间、塑造上海人文化认同方面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建构都市公共空间:从“人民广场”到“市民广场”
广场。上海最著名的人民广场,在吴驷看来,早已失去它原初的意义。因为,人民广场作为政治公共空间的功能在1980年代结束之后湮灭了。取而代之的是适应都市生活的市民广场,这个所谓的“市民广场”不再局限于固定的广场概念,而是延伸到了街道、公园、河流(两岸)、商业购物中心等等都市公共空间。《申》报及发现上海的相关报道,将这些主题统合在一个主题之下——“都市空间”,这是与现代性都市的公共生活、公共文化相勾连的空间概念。在中国传统观念中,这个意义上的空间概念是非常缺乏的。《申》报关于都市空间的生产,正是出于这样一个特殊的视角,从政治意识形态意义的“人民广场”转向市民日常生活交往的“市民广场”,都市空间的“公共性”跳脱了狭义政治的框架,被赋予了都市现代性的新含义。
街道。“发现上海”空间主题的开山之作是《申》报创刊第一年的“情侣路”专题。这个主题在《申》报创刊一周年纪念特刊中以“本报情侣路评选大揭晓”告终,获得读者巨大反响,报纸“卖疯脱了”。这个主题以都市生活的一个典型场景——年轻人在街头谈恋爱为基本内容,将城市格局、市井风情、历史文化落实于“街道”这个都市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空间”元素整合历史、社会、文化、日常生活,这种视角在当时的媒介中算得别开生面,颇为新鲜。尽管“情侣路”专题只是利用了“街道”这个空间元素大做文章,并未在都市空间概念上有纵深的开掘,但这个主题对于“发现上海”而言意义重大,因为它开启了“发现上海”以及《申》报后续空间主题的系列内容,使得都市空间成为报纸“发现”上海的最重要方式。
“街道”从此在“发现上海”中反复出现。那些著名马路自然是被一做再做。如“大马路——南京路的文脉”、“四马路——福州路的文脉”专题,称“城市是一部具体的真实的人类文化的记录簿”,而“马路”则是一个城市的文脉。这两条马路周围的著名场所以此种方式被集合到了一起。“大马路”周边的是“远东第一跑马厅”、“独领世界时尚风潮的四大百货公司”、“卓别林定制过衬衫的老介福商店”、“展示过刘海粟裸体素描的张园”、胡蝶、阮玲玉电影中的南京路街景,等等。而福州路周边涉及的是剧院(天蟾舞台)、海派文化发源地(麦家圈)、风月场所红灯区(会乐里)等。这些都市空间元素的呈现,被赋予了历史的连贯性,特别是与当前社会公共生活的关联,如借“四大公司”讲述百货公司在上海的历史,一定延续到“永安公司”原址上现今的“华联商厦”;比如福州路强调历史上的商业辉煌“盖过大马路”,也提及现在变成了“文化街”。同年关于“淮海路”专题的标题是“‘围城’下的淮海路”,处理方式如出一辙,以文人笔下的“淮海路”串起和淮海路有关的历史、文化、人物、事件。这些上海著名马路的描写,被归结为行使城市的功能,而“城市的主要功能是化能量为文化,化生物繁衍为社会创新”,而街道则是都市公共空间。这和空间理论关于“街道”的观点不谋而合——街道最重要的用途之一是社会交往,“人行道上的社会生活的核心之处正在于它们是一种公共活动。……如果城市人之间有意义的、有用的和重要的接触都只能限制在私下的相识过程中,那么城市就会失去它的效用”。
公园。都市空间中又一个重要元素,也是“发现上海”大书特书的内容。
03年上海开埠160年特刊中,“公园”主题有一个专版,标题是“新世纪——我们有了呼吸权”,描述了中国从完全缺乏“公共花园的传统”到21世纪市民免费进入公园的公园发展史,这次报道将“公园”的功能定位在市民“呼吸权”的说法在当时是颇有些冲击力的。但很快就被《申》报后继有关公园的报道新理念所替代了。
05年“发现上海”栏目以“上海寻梦园——公园再发现”为题,展开上海公园的历史回顾与未来展望。在这个板块的开篇文章中,公园被称为“西方说法中城市的肺”,是承载上海梦的不可或缺的物质性空间场所。报纸采用上海史专家李天纲的专访,梳理了“从私家花园到公共绿地”的公园变迁史,特别点出,上海最早是没有“公园”这个概念的,洋人来了以后才出现所谓的“公园”。关于公园功能的传统概念是绿化,而现代观念则是多元化了,包括提升周边房地产价值,等等,而最重要是,提供了普通市民“日常休闲娱乐社交”的场所。这个“市民日常社交”的理念将公园的功能从“绿化”向都市空间的公共性推进了一步。

因为种种特殊、复杂的原因,外滩公园是上海100多家公园中最引人关注的,一方面因为外滩公园门口悬挂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示,成为一个历史事件(此问题学界尚有争论,但大众普遍知晓);另一方面则是它占据外滩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上海标志性景观。“发现上海”关于公园的主题多次拿外滩公园大做文章。
06年“发现上海”栏目以上海史专家熊月之“重说外滩公园的百年记忆”的专访,提出都市公共空间的概念。这篇专访的主要内容出自熊的一篇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论文奖的上海史专业研究论文,该论文的重点是外滩公园歧视华人社会反应的历史解读,指出“外争权益”只是当时社会反应的一个方面,在后来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历史情境中得到不断彰显、放大;而社会反应的另一方面“内省公德”,却受到长期的遮蔽与忽略。报纸专访则突出了外滩公园作为近代上海第一个公园,对于中国人“公共空间”观念形成的冲击。报道借熊之口指出,外滩公园开启了都市公共空间,使得缺乏公共意识的中国人明白了两点,一是都市休闲概念,让市民知道去公园是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突出公德概念,促使市民开始注意公共空间内的公共秩序和公共卫生问题。报纸在专访中提出“上海人都市公德的自省”命题,专门配发评论,号召上海人借由外滩公园事件的历史回顾,培养公共空间中的公德意识。
外滩早在1998年就被《申》报冠以一个意味深长的名称——“上海的公共客厅”,称“我们发现那种无名特质生气勃发,足以振拔拥有它的这座城市市民的精神。”在03上海开埠160年特刊中,“开埠为什么是外滩”的文章被放置在特刊第一板块“时空篇日常上海”的开篇处,文章将外滩的特质归结为“开放”,称“开放不仅是历史趋势,而且是人的生存本能”。这个版面的另一篇文章则称外滩的建筑和地理环境让人感到“亲切”和“自尊”,因此是上海吸引外地人和上海人的“客厅”。
《申》报的这些策划和报道,从外滩公园到外滩到上海“客厅”,始终围绕着都市公共空间的线索展开。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申》报将外滩称为“上海的客厅”的说法以及包含的理念,获得很大范围的认同。08年外滩改造方案公布之后,媒介进行了大量报道。其中,北京《三联生活周刊》的专题报道即釆用了“外滩是上海客厅”的框架,报道题为“外滩:回归‘公共客厅’”。这篇报道以外滩是公共空间的基本理念展开,报道援引上海市规划局副局长的话,反省外滩空间布局的不合理性,从“人的外滩变成车的外滩”,使得“这里公共空间性质衰落了”。文章还报道了陈丹燕(上海作家)、熊月之(上海史学者)、李天纲(上海城市文化研究学者)、钱宗灏(同济大学建筑学学者)对于外滩“不完整的公共性”的批评。
在关于外滩的《申》报报道中,“情人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主题。关于“情人墙”,上世纪70年代的《纽约时报》有过这样的记载,“沿着黄浦江西岸的千里长堤,集中了一万对上海情侣。他们优雅地依堤而语,一对一对之间只有几厘米的距髙,但绝对不会串调。这是我所见过的世界上最壮观的情人墙”。“发现上海”对于“情人墙”也有过多次报道。在上海开埠160年特刊中,“情人墙”主题占有整整一版。版面上方是1976年7月28日中共上海团市委一份调査报吿的节选,“从北京东路外滩到南京路外滩,在这200米的距离中就有600对青年男女谈恋爱,平均一米内就有三对,当然,在其中大多数是正常的,但早恋的也不少。其中将近200对青年男女在谈恋爱时,动作不正常”。版面中的重头文章是对“情人墙”具体情形的描述。其中特别提及“情人墙”形成的原因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海情侣们缺乏“一个既隐蔽又安全的地方”谈恋爱。家里地方既小,也碍于熟人的众目睽睽;“无奈去户外,公园早早关门,黑灯瞎火的地方经常有纠察、联防队员巡逻,以保证公共场所不受污染,那时又没有咖啡馆、酒吧、舞厅。”一言以蔽之,彼时上海缺乏市民日常生活必需的公共空间,“情人墙”是上海人在特殊时代创造出来的特殊都市公共空间。版面上的这两段文字形成极有回味的参照,“都市公共空间”的线索隐含其中,它的湮灭、扭曲与复兴,反映出上海社会曲折发展的历史变迁。

河流。文化地理学意义上一个现代城市的重要标志,以“苏州河”、“黄浦江”为主题在《申》报及“发现上海”中大量出现,次数极其频繁。在为数有限的《申》报特刊中有两次是以“河流”为主题的。分别是“苏州河”与“黄浦江”。
“苏州河主题早在《申》报创办初期就出现了。如1999年“发现上海”即以“苏州河明朝水清”为题做了一个专题。提出的主要概念是河流与城市的关系,在都市整体规划中考察河流的功能问题。在这次的报道中,提出了“苏州河是上海母亲河”的观点,动用上海文化专家唐振常,阐释苏州河和上海城市文化发展的关系。但在提出苏州河规划展望时,尽管提及了一个新加坡人建议两岸开高档酒吧的“奇怪”点子,但还是将重点放在了水质污染的治理上,即“水清”。此时苏州河两岸作为“都市公共空间”的理念基本没有出现。
01年《申》报的新世纪特刊中“苏州河”成为最主要的主题。这次的视角非常多元,包括历史、艺术、建筑、文学、日常生活,等等。提出,苏州河是上海的“城市名片”,在“专家规划苏州河”专题中,直接以“市民的共享空间”为主要观点,明确指出,“苏州河两岸应该是全市人民共享的休闲领域”,并落实到具体的空间规划设计中,如,“房地产开发必须后退,留出两岸一定比例的空间”,“亲水是苏州河景观设计的原则。水泥防洪墙要拆掉,代之以漂亮的铁栏杆,营造人在岸边走,水在脚下流的环境。”“苏州河可以成为年轻人聚集、消费游乐的地方。……可以开设很多前卫、个性的酒吧、咖啡馆、画廊,每隔一公里建一个休闲广场,……引来巨大的人流。”河流对于城市的功能明确定位于提供都市的公共空间。
“发现上海”及申报的空间生产,以“空间”元素呈现了上海历史变迁引发的社会关系的变革。这正体现了列斐伏尔强调的都市空间与社会关系的关系,“社会关系的存在方式究竟是什么?它们是具体自然的呢,还只是抽象的形式?空间研究给予了回答,它认为生产的社会关系是一种社会存在,以至于是一种空间存在”。在报纸话语中“人民广场”向“市民广场”转变,正折射了社会关系的历史变化,都市公共空间的概念重新树立之时,此“公共”已非那“公共”,这个基本抽离了“文革时期”政治功能的都市公共空间,开始被填充现代性中城市公共交往、普通市民城市生活的新内涵。
塑造集体记忆:从“真实”到“想象”
“你怎样理解‘发现上海’中的‘发现’这个概念?是‘反映’还是‘建构’?”吴驷在回答本文作者这一提问时说,他本人是新闻学学科背景,但在做“发现上海”时觉得新闻的方式不够充分,“因为不能够对于上海空间未来发展做出想象,那建构从何谈起?”因此发展出了一个新的体裁,既有新闻式的“真实反映”,也有主观式的“想象”,是糅合在一起的。他自嘲地说是一个“四不像”的体裁,在一般的报纸上很少见。在处理都市空间的主题时,常常使用这一体裁。新闻方式用于呈现当前或者历史上上海真实存在过的物质性空间,而主观的方式则是“想象”存在于各色人“心目中的上海空间”,这是策划人、写作者一种有现实基础的“空间想象”,建筑师、城市文化学者、上海名人常常是这种想象的理念提供者。这个栏目常常会出现标注着“戏仿”的文字,有时是借助具象空间的展开故事;有时是对于上海都市空间未来发展的构想。“发现”既是对于现存世界的呈现,也包含对于未来的想象,除了客观“反映”,还有主动地“建构”,就这点来看,“发现上海”和“珍藏上海”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珍藏”侧重于保护已经存在过的东西,而“发现”还试图主动开掘新的可能性。媒介对于空间的“发现”赋予了具象“真实”空间以主观意义。
“发现上海”在进行都市空间的生产时采用的方式,正包含了Edward W.Soja所总结的两种空间的思考方式,即聚焦于“真实”物质世界的“第一空间”视野,和根据空间性的“想象”表征来阐释此一现实的“第二空间”视野。“第一空间”方式用自然主义、唯物机械论或经验主义强调世界的具体性,认为客观“事物”比“思维”更真实。第二空间则是全然观念性的,它从构想的或想象的地理获得观念,并将这些观念投射到经验世界中去。Soja说,因此,存在着两种地理,一种是“真实的地理”,另一种是“想象的地理”,比如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每人心目中都会有关于空间的形象,这便是“心目中的地图”,每个人“心目中的地图”之所以各不相同且与真实地图有很大差异,是因为都渗入了“想象”。而“想象的”地理总是试图成为“真实的”地理,“再现”试图界定和安排“现实”。Soja本人的创新理论则是所谓的“第三空间视野,“它源于对第一空间—第二空间二元论的肯定性解构和启发性重构,综合真实和想象,是真实—想象的混合体。Soja认为“第三空间”的视野可以为人类思考空间问题提供崭新模式和创新思维。
“发现上海”采用真实和想象并用的方式进行上海都市空间的生产,这种生产是以“真实”的上海为素材,建构了一个“想象”的上海。《申》报生产出来的上海都市空间因此既是真实的,又是想象的,它并非是对于上海“真实”地图的“客观”呈现,也不尽然是凭空建构出一个“虚幻”的上海,而是真实—想象融合的上海。
“发现上海”空间主题中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个案,就是莫干山路的相关报道。它的特殊性在于,报纸书写在纸面上的“想象的”地理,在几年后变成了“真实的”地理,尽管上海市规划局实施的莫干山路重建计划和“发现上海”的想象不完全相同,但却惊人相似。但这只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个案,在“发现上海”及《申》报众多的空间主题中简直如大海一粟。那么,那些停留在报纸上的文字和图片——无论是关于“真实”的反映还是主观的“想象”——又有什么意义呢?对此,吴驷的回答是,能将“想象”变成“真实”固然有特殊的成就感,但这并非“发现上海”的主要目标。作为一家地方报纸,又是以“发现”为主題的栏目,最重要的责任在于,保存并延续上海人的集体记忆,以构筑上海人的文化认同。而空间是集体记忆最重要的元素之一。他说他的这个想法来自一些建筑师、历史、文化学者,他将这个想法通过“发现上海”具体实施。
著名建筑师登琨艳的一本建筑社会学的专著《失忆的城市——一个建筑师对当代城市的痛与爱》,以缩写加照片的方式整版出现在“发现上海”中。栏目的文章以“失忆的城市”为主标题,版面中央有大大的“失忆”二字。文章的重点是用大段的文字阐释城市空间和集体文化记忆的关联性,“我们需要一些历史的记忆,这些记忆承载在那些历经几十年上百年岁月荡涤的老建筑里。它们就像城市的肌理,每一沟每一壑都记录着我们城市的历史”。“要尽可能留存住可以留存的一些物化的记忆。上海有很多老工厂,如今被轰轰烈烈地改造成创意园区。……我们这座城市,找不到什么特别的自然文化遗产,但是我们能够保存一些属于自己的生活记忆。这些关乎普通人的记忆,谁又能说这不是最宝贵的人间遗产呢?”为了说明“发现上海”的空间生产与上海人集体文化记忆的关系,吴驷反复提及一件事,某一知识分子批判上海一个著名的所谓“怀旧”酒吧“上海1931”时说,里面的东西都是假货,所谓“怀旧”,不过是赚钱的幌子罢了。吴驷评价说,这个人根本没有理解怀旧的意义。“怀旧”是使用集体历史记忆建构文化认同的一种方式,“真假”并不是问题的核心。“发现上海”做上海都市空间,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都是在建构一种集体记忆以促成上海人的文化认同的建立,而上海丰富的空间性社会历史提供了这种可能性。

“发现上海”对于上海建筑“真实”和“想象”混合的生产,最典型地体现了以空间的集体记忆建构上海人文化认同的努力。
《申》报十年特刊中有两个对开版面以“寻找上海魂灵头”为题,题头下面的文字写到,“‘魂灵头’是上海方言里很有意思的一个词汇。……‘魂灵头’是身躯里面一个无形的东西,它跟心灵是有关的,自然非常重要,但与灵魂相比,它似乎轻灵许多,好像喜欢活动,是可以随时溜走的。我们知道,如果一个人灵魂丧失,那恐怕是再也找不回来了,而‘魂灵头’的丢失,确是可以找回来的。上海在这十年里和自己的‘魂灵头’捉迷藏。在最初的拓旧中,一声一声震耳的打桩声重重捶打着城市的心脏,我们有着难以言说的痴狂,眼睛里仿佛已经看见‘比过香港’、‘东京第二’、‘东方曼哈顿’的摩登新都。然而,那城市的‘魂灵头’,却在变迁中仓皇而固执地躲了起来。所幸的是,上海还未完全忘记自己。无论未来的上海变成什么模样,如果有一天,上海人对自己的‘魂灵头’完全忘却了,那么上海也令世界厌倦了。在那一天可能到来之前,让我们先到那些变迁过后的褶皱里,去寻找上海的‘魂灵头’。”在这个主题之下报纸提供了六个藏着“魂灵头”的褶皱,其中有五个是与空间有关的,这五个中又有三个与建筑有关。既有“真实的地理”中的建筑如老洋房,也有虚实融合的“想象地理”与“真实地理”并置构成了Soja的“第三空间”,如“平安里”是一个具象的物质空间,但文章中却是以上海著名作家王安忆写上海文化最出名的代表作《长恨歌》中的虚幻情形写出的;另一处著名老建筑张爱玲故居也使用同样笔法,将一个实存的空间与和张爱玲、上海有关的电影《红玫瑰白玫瑰》、《色戒》扯上了关系。所有的这些都是为了一个目标,在这些建筑空间中建构出一个上海的“魂灵头”,为失忆的上海招魂。
建筑主题在“发现上海”中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既涉及散落在西区街道中的私人老洋房;也有上海标志性建筑如国际饭店、大光明电影院、外滩万国建筑;浦东新区的新建筑金贸大厦、东方明珠电视塔、艺术创意园区也无一遗漏;上海老工业区大杨浦的老厂房在近年也成为关注焦点;苏州河、黄浦江主题更是串联了两岸在不同年代累积下来的形形色色的建筑。只要是空间中的建筑无论新旧,都以上海“魂灵头”的名义集合起来,这正如Zukin所言,城市的视觉再现“可以整合而不是离间社会与种族的群体,它也可以帮助新的集体认同”。因为“传统的机构——既包括政党,也包括社会阶层——在表达个人认同方面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而创造城市形象、定格城市画面的力量正变得越来越重要。那些创造形象的人也塑造了一种集体的认同”。
“发现上海”有一个多年以来自成系列的主题,名为“双城记”,后改名为“新双城记”,一直延续着上海与其它城市的比较。与上海相提并论的城市主要包括,北京、香港、巴黎、伦敦、纽约、东京,里昂,等等。亲手策划了“双城记”系列的吴驷说,是想借鉴他者经验,创造属于上海的“在地化美好生活”。通过上海和其它城市的比较,弄清楚上海都市的特质究竟是什么,这样才谈得上“在地化”。这种比较在早期以城市生活的多种元素展开,比如典型的“上海—北京”双城记,从饮食、运动、语言、人际交往、婚恋方式等等方面加以比较,空间元素也是其中重要一种,如以两个城市彼时的酒吧文化地标“衡山路”与“三里屯”,比较上海文化的“玩情调”与北京文化的“扎堆混”之不同。在后期的“新双城记”时期,空间元素被突现出来,成为双城比较的重点。如05年“新双城记”特刊中之“新北京老上海”专题,六个版面的内容几乎全部是以空间元素展开的,“新北京”集中于08奥运场馆建设、三里屯酒吧街变迁、胡同四合院改造、“789”艺术园区四个方面,而“老上海”则以茂名路酒吧街、泰康路原生石库门、SOHO现代城、东外滩景观展开,这些比较以都市空间为具体对象,落实于城市规划方案探讨,以都市空间承接历史、凝聚文化为理念,与早期的“双城记”相比,有着明显的文化意义上的对于都市空间的自觉意识。这个主题之下的开篇文章以“上海沉淀”应对“北京激变”,称,“曾经与北京暗自较劲的上海,在历经10年的飞速发展后,面对北京这一轮激变,显得处变不惊,一点脾气也没有。坐拥文化遗产的北京在那里一个劲激变;上海现在忙活的倒是寻找自己的传统了。……上海不再一味追求更快更高更强,……上海正在慢慢等待自身的积淀,好在若干年后再回首时,没有一丝遗憾。”在这段文字建构的想象中,上海的文化自信心正是来自都市的空间元素,“尽管上海未见得如北京一般有丰厚的文化遗产,这100多年来积淀下的世间遗产也同样精彩。……上海是历史文化遗产非常丰富的城市,这些历史文化风貌街区和优秀历史建筑,浓缩了上海特有的东西交融、海纳百川的历史文化底蕴,是城市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发展的历史见证,是城市精神的物质载体。”这些论述非常清晰地表达了以建筑、空间承载集体记忆、文化认同的意识。

“发现上海”运作中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方面是知识分子在其中的作用。以《申》报一个通俗消费类报纸的定位,知识分子在栏目中的作用不仅在同类媒介中非常罕见,即使是与严肃精英类型的同城报纸相比,也是独具特色的。这些知识分子以多样性角色介入“发现上海”。一种类型是以采访对象、意见表达者、学术著作的作者甚至“戏仿文字”的对象直接出现在版面中,如李欧梵及他关于上海都市文化研究的名作《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就被“发现上海”从各种角度使用过二十多次。另一种类型则是栏目的出谋划策者、理念、观点的幕后提供者。吴驷作为这个栏目的责任编辑与上海各大高校、研究所中有关建筑、历史、文学、艺术等文人圈有广泛联系,这些人成为“发现上海”的“专家后援团”。比如在《申》报上海开埠160年特刊中“目录”板块中的显著位置,开列了十四人组成的专家后援团名単,其中包括李欧梵、钱宗灏、郑祖安、薛理勇等等各个学科背景的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对于“发现上海”的作用主要有两个,一是提供了这个栏目的基本理念,比如栏目集中在空间、语言、城市与人的关系这三个维度,就是受到相关研究者的直接启发。二是以专家、权威、名人的角色出现在报纸上,成为这些理念的宣讲者,建立起这些学术观念、思想与普通市民的联系,而报纸就是沟通的桥梁。这些知识分子们都和上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关于上海城市的种种想法在建构上海集体记忆和文化认同方面,有着特别重要的影响,“上海人”想象共同体的形成,有赖于这些有自觉意识的文化人的努力,“发现上海”则是在上海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时期提供了这样的公共平台。
定义城市:蕴含历史与社会的空间
Sharon Zukin著名的发问“谁的城市?谁的文化”提出了“城市形象定义”的问题,“显示了文化符号、城市空间和社会力量之间的关联”。“发现上海”关于上海都市空间的生产,是以关于空间的“真实—想象”的文化符号定义城市的一种行动。这个行动中被突现出来的空间元素,并非与历史、社会隔绝,而是杂糅了历史、社会的因素,呈现了列斐伏尔“历史—社会—空间”辩证三元论的意蕴。
在“发现上海”中,上海的都市空间正是因为上海特殊的历史、社会因素才获得“上海之所以为上海”的意义。上海都市空间的形成是和晚清以来上海渐趋西化的殖民历史不可分割的。上海都市空间的主要元素马路、街道、公园、广场、河流两岸、老洋房石库门各色建筑,等等,无一没有这段殖民历史的深深烙印。上海人根深蒂固的关于上海城区的区隔概念,如“西区东区分成上只角(富人区)、下只角(穷人区)”等,都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和社会意味。因此,上海都市空间中有关历史、社会的“意识形态”问题是无法回避的。《申》报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且在一些关键时刻试图给予解释。如,《申》报上海开埠160年特刊主编卷首语中就开埠一事写到,“我们对开埠日曾经讳莫如深,因为它被视为上海半殖民地历史的开端,但如果敞开‘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宽阔胸襟,从开放的意义上去理解开埠的历史意义,则我们不能不看到,一个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离不开这个历史的起点,……我们城市的精神,就渗透在这160年的历史文脉中。”
“发现上海”运作中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方面是知识分子在其中的作用。以《申》报一个通俗消费类报纸的定位,知识分子在栏目中的作用不仅在同类媒介中非常罕见,即使是与严肃精英类型的同城报纸相比,也是独具特色的。这些知识分子以多样性角色介入“发现上海”。一种类型是以采访对象、意见表达者、学术著作的作者甚至“戏仿文字”的对象直接出现在版面中,如李欧梵及他关于上海都市文化研究的名作《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就被“发现上海”从各种角度使用过二十多次。另一种类型则是栏目的出谋划策者、理念、观点的幕后提供者。吴驷作为这个栏目的责任编辑与上海各大高校、研究所中有关建筑、历史、文学、艺术等文人圈有广泛联系,这些人成为“发现上海”的“专家后援团”。比如在《申》报上海开埠160年特刊中“目录”板块中的显著位置,开列了十四人组成的专家后援团名単,其中包括李欧梵、钱宗灏、郑祖安、薛理勇等等各个学科背景的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对于“发现上海”的作用主要有两个,一是提供了这个栏目的基本理念,比如栏目集中在空间、语言、城市与人的关系这三个维度,就是受到相关研究者的直接启发。二是以专家、权威、名人的角色出现在报纸上,成为这些理念的宣讲者,建立起这些学术观念、思想与普通市民的联系,而报纸就是沟通的桥梁。这些知识分子们都和上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关于上海城市的种种想法在建构上海集体记忆和文化认同方面,有着特别重要的影响,“上海人”想象共同体的形成,有赖于这些有自觉意识的文化人的努力,“发现上海”则是在上海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时期提供了这样的公共平台。
定义城市:蕴含历史与社会的空间
Sharon Zukin著名的发问“谁的城市?谁的文化”提出了“城市形象定义”的问题,“显示了文化符号、城市空间和社会力量之间的关联”。“发现上海”关于上海都市空间的生产,是以关于空间的“真实—想象”的文化符号定义城市的一种行动。这个行动中被突现出来的空间元素,并非与历史、社会隔绝,而是杂糅了历史、社会的因素,呈现了列斐伏尔“历史—社会—空间”辩证三元论的意蕴。
在“发现上海”中,上海的都市空间正是因为上海特殊的历史、社会因素才获得“上海之所以为上海”的意义。上海都市空间的形成是和晚清以来上海渐趋西化的殖民历史不可分割的。上海都市空间的主要元素马路、街道、公园、广场、河流两岸、老洋房石库门各色建筑,等等,无一没有这段殖民历史的深深烙印。上海人根深蒂固的关于上海城区的区隔概念,如“西区东区分成上只角(富人区)、下只角(穷人区)”等,都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和社会意味。因此,上海都市空间中有关历史、社会的“意识形态”问题是无法回避的。《申》报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且在一些关键时刻试图给予解释。如,《申》报上海开埠160年特刊主编卷首语中就开埠一事写到,“我们对开埠日曾经讳莫如深,因为它被视为上海半殖民地历史的开端,但如果敞开‘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宽阔胸襟,从开放的意义上去理解开埠的历史意义,则我们不能不看到,一个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离不开这个历史的起点,……我们城市的精神,就渗透在这160年的历史文脉中。”

“发现上海”在表现“空间”,总是试图挖掘背后隐藏着历史、社会因素,那些不会说话的具象物质的“空间”因此具有了鲜活的生命——承载着历史、社会的重负。这些“空间”是“活着”的历史、是“可视的社会。这正如Soja理解的列斐伏尔空间理论的精髓所在,“只有当社会关系在‘空间’上‘烙印’——亦即具体再现——于社会空间的社会生产时,它们才是具体的,才是我们实际社会存在的一部分•……不存在没有空间化的社会现实,也不存在非空间的社会过程”。
05年8月31日,《申》报以八个版面在“发现上海”、“影像上海”两个题头下,就重要历史事件“一·二八”、“八·一三”事件做专题报道,整个内容都是以“空间”元素为落脚点,但这个空间却是糅合了历史、社会元素的丰富内容。八个版共刊登20幅照片,再现历史场景,在这些历史场景中,建筑是最重要的角色。如被日军轰炸破坏的商务印书馆大楼、被日军掀翻了的“市府新厦”楼前的孙中山铜像、门口有日军站岗的复旦大学校门、被日军轰炸破损的上海北站候车大楼,等等。这些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的“空间”表现,因为背后蕴含的历史、社会因素,获得了丰富的意义。
这个版面的文字部分是以关于“空间”的“真实再现”和“主观想象”两种方式展开的。板块的主标题是“一・二八、八・一三:大上海・新华界・梦没了”。“真实再现”一方面集中反映日军侵略对上海城市空间造成的巨大破坏,“庞大的‘商务城’完全毀于战火”,“‘东方图书馆’的中西藏书被焚烧得数周不息”,“亚洲一流的北站大楼只存留下千疮百孔的躯壳”;另一方面,也披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骨子里有民族气节的上海人”曾经推出过一份“世界级水平的城市规划”,名为“大上海计划”,是试图在租界林立的上海都市空间中建设一个华人自主的“新华界”。这个板块文字的主要内容都是以这个被尘封已久的城市规划展开的,被突现的要素仍然是空间,比如“大上海计划”中上海都市中心是东北角的江湾五角场;计划的附带产物“飞机楼”成为那个时代的上海“标志性”建筑;“亚洲第一”的大型体育场上海市江湾体育场“惊艳登场”;市政府新厦落成,全市放假一天,10万人在市府广场集会,等等。报纸文章称,这个计划就是要“与洋人别苗头”,“为的就是总有一天‘将租界取而代之’。”这个主题怎样与“一·二八”、“八·一三”事件扯上关系?“发现上海”告诉读者,正是日军侵略,使得上海人的这个梦想破灭了,“一个繁华的新市中心诞生了。就在朝气蓬勃的江湾五角场渐渐展现出魅力时,日本人的侵略战争给年轻的市中心以毁灭性的打击,日本鬼子的坦克耀武扬威地驶过江湾,轰鸣的引擎声中依稀听见江湾无力的哀嚎,市政府大厦前,中山先生铜像倒地的一刹那,大上海计划也以一个悲剧结局,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这种将多个历史事件(“一·二八”、“八·一三”与“大上海计划”)事件并置、拼贴的做法,充分体现了报纸对于都市空间主题的“主观想象”,它使得那些关于“空间”的“真实”获得了更多的超乎“空间”的历史、社会意义。
在这种想象中,空间、历史、社会三元素水乳交融、交相辉映。一个历史事件以“空间”呈现于当下,这个“空间”元素旋即又被赋予了更大社会场景中的历史意义。在这个板块的八个版面中,“一·二八”、“八·一三”事件的具体内容只在首页的一小段文字具体涉及,后面则变成了一个线索和由头。前三版以“80年前海归派梦想——大上海八·一三之痛”为小标题,重点叙述“大上海计划”;中间两个版面的小标题是“闸北——‘一·二八’前上海文化核心地带”,描述华人“自治闸北”在城市建设方面的巨大成绩,如宝山路、东亚第一图书馆“东方图书馆”、上海火车站“北站”等等,这些内容与主题的连接和“大上海计划”相似,是“日军的两次入侵,给闸北带来毁灭性打击”。最后三个版面笔锋一转到了“江湾体育场”,冠之以“30年代大上海计划的遗产”,叙述了江湾体育场70多年来的历史变迁,甚至连带扯出了中国“乒乓球”运动(民间乒乓球队在江湾体育场训练)、姚明父母(作为篮球运动员经常出没江湾体育场)、乒乓外交(尼克松、美国乒乓球队访问江湾体育场),等等。这种呈现方式集中体现了Soja所谓“地理性历史”的思考方式,即将空间—历史—社会同等地结合在一起考察都市。作为都市形式,空间特性包括形式或形态、活动或动态两个方面。形式或形态,用物理的结构如建筑、纪念碑、街道、公园等来表现,这些又可以在经济财富、文化认同、阶级差异和都市居民的个体与集体属性、关系、思想和实践的全部范围内获得表达。作为活动,则涉及更多的动态性质,它产生于都市生活方式的社会结构,产生于最广义的社会生活不断发展,有目的计划和政治性控制的“语境化”和“空间性化”,但正如Soja所言,“每种空间性的东西同时是社会性的”这种观点更容易理解,但“理解相反的关系即社会性的同时内在地是空间性的就难多了”。如果以这个视角考察“发现上海”的“空间”主题,它的独特性也是一般大众媒介中罕见的。
06年“大上海计划”又以其主要实施者——水利工程专家、时任上海市工务局局长沈怡的相关著作为由头,重新出现在“发现上海”中。这次内容的主标题意味深长——“争夺上海都市话语权”。以更加翔实的历史资料重点阐发了这样一个观点,都市空间是都市话语权斗争的重要场域。比如提及“大上海计划”中沈怡“以修筑中山路包围整个洋人租界的睿智,使‘越界修路’的阴谋不攻自破。”“大上海计划”这个不同寻常的城市规划,被赋予了那个时代有民族气节的国人与帝国主义抗争的意义。这种以“空间”定义城市的方式正是“发现上海”及《申》报“发现”上海价值最重要的方式之一。这种“定义”行动施展于城市空间的各个角落。03年的“重新定义北京西路”,以各国著名设计师对“堪称上海皇冠”的北京西路、静安寺一带“想象中的设计”,“呈上他们眼中理想的上海人居家空间。”06年的“想不到的上海”,以“创意之旅为主题,呈现了一个“新上海”空间景观,以长久被忽视的“中国工业源头大杨浦”的老厂房演变为创意园区作为主要内容,力图打破上海的价值在于西区的刻板印象,拓展人们对于上海的认知。04年特刊“黄浦江——那是我们的海”,30余个版面的内容全部以黄浦江这个都市空间中的关键元素作为由头展开。特刊的开篇文章阐发了黄浦江所象征的上海精神,称黄浦江是上海城市精神的体现,“上海没有海,黄浦江是我们的大海”。上海的品质是自由开放,充满梦幻、机遇和挑战,“这里曾是不设防的港口,是全世界最自由的港口。100多年以来,不知道有多少人从世界各地,经由这条江,抵达上海;又不知道有多少人,经由这条江,抵达世界。”上海是有引以为豪的历史和辉煌未来的。“虽然我们的黄浦江曾经承载了过多的荣耀,虽然我们的黄浦江也曾经历过怀疑与失落,我们却始终看到了一条充满流动色彩的海。”上海的独特性在全球化背景下怎样呈现?“对于今天而言,我们只关注当下抵达我们城市的将是什么,从这里出发的又将是什么?我们将从世界获取什么,我们又将向世界输出什么?今天黄浦滩头的人来人往,谁又将是世界的翘楚?”在这里,黄浦江,这个上海城市最重要的两条河流之一,不仅仅是上海城市精神的空间表征,甚至就是上海都市本身,它是空间—历史—社会三位一体的上海。这种手法体现了“发现上海”及《申》报以空间定义城市的典型特征,即,不遗余力地挖掘这个城市空间的历史、社会内涵,并审时度势赋予它们在这个时代新的意义,以重新定义“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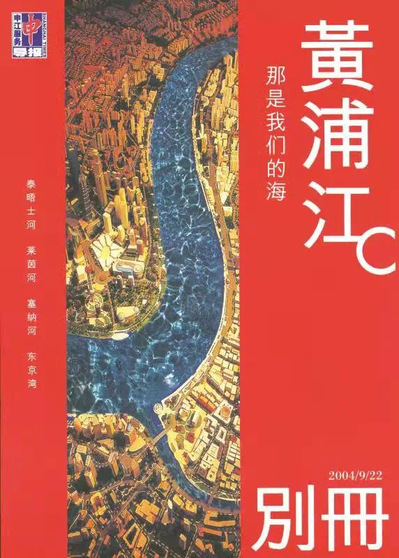
结语:都市空间生产——媒介何为
“发现上海”都市空间主题的表现方式,对于《申》报有很大的影响,凡《申》报关于重大事件的特刊中,“空间”主题几乎一直是最重要的板块,吴驷作为“发现上海”的责任编辑,常常出任这些特刊的总策划人。但从报纸整体来看,“发现上海”却是非常特别的,或者可以说与报纸的整体风格很不协调,尤其是以“空间”为主题的板块。比如03年《申》报以“伫立于‘两河’节点的外滩酝酿申报‘世界遗产’”的新闻点所作专题“黄浦江、苏州河——现代上海两河流域”,操作理念和方式与“发现上海”空间主题的一贯风格非常接近,这个专题的编辑并非吴驷。其中对于上海近年来以奢侈著名的建筑“外滩3号”的处理,是以“文化资产保护性开发案例”展开的,通篇都是以建筑师的设计理念以及这些理念与上海文化、历史关联的阐发为内容,完全没有浮华商业情境的描绘和渲染——而这正是《申》报其它栏目处理“外滩3号”的常规性做法。尽管“发现上海”在许多方面也沾染消费报纸的气息,如文字的煽情、浮夸、矫饰,思维断裂呈碎片化,刻意制造“噱头”以吸引读者,等等,但总体来说还是有着清晰的学术视野与人文韵味,与一般的都市消费类文字迥然不同。这也使得“发现上海”在读者越来越低龄化、商业消费气息日渐浓重的《申》报中显得不伦不类。
对于“发现上海”的这个境况,吴驷的回答是,“发现上海”能做到今天这个程度,有赖于《申》报这样新型报纸提供的平台,这对于同城历史悠久的老报纸来说,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申》报相对宽松自由、潜藏不确定发展可能性的环境,正是“发现上海”得以形成自己特殊风格的保障。吴驷说,“发现上海”没有直接受到市场压力对报纸的影响,但《申》报不可能回避这个问题。如果《申》报都采取“发现上海”这样相对人文、学术的方式操作,结果怎样是很难预料的,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成功的可能。关键在于,中国、上海都没有形成媒介创新的大气候。事实上,上海亦有其它媒介釆取类似的方式——即以都市空间为主要元素建构上海的集体认同,如《新民周刊》的“城市表情”专栏,上海电视台的“发现上海”节目。但按照吴驷的话来说,没有一个像《申》报“发现上海”栏目这样系统性、理论化、有自觉意识地展开。从这个角度来说,上海媒介建构集体认同的行动远远没有规模性的出现,无论是以怎样的方式。
一位网民在博客中写到,“每周雷打不动购买申报,虽然最喜欢的栏目并非《发现上海》这栏目,但恰恰是这样的栏目让我关注起了上海,我生活的地方。作为上海人,对上海有些事并不很清楚,这经典的栏目使我了解了上海很多细节,越发令我对上海产生遐想,有一天想照着报纸上的历史、人文、商业等等的地标寻找上海的最隐晦的曾经。”这个情形不由人想起安德森所描绘的、报纸在“想象共同体”建构中所产生的影响,“报纸的读者们在看到和他自己那份一模一样的报纸也同样在地铁、理发厅,或者邻居处被消费时,更是持续地确信那个想象的世界就植于日常生活中,清晰可见。……虚构静静而持续地渗透到现实之中,创造出人们对于一个匿名的共同体不寻常的信心”。当前没有更多的材料得以梳理清楚“发现上海”与《申》报读者的上海人自我认同之间的关联,我们能看到的只是媒介从业者有自觉意识的努力。这种媒介作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转化为一种地方文化构筑“想象共同体”的现实,受制于众多的不确定因素。值得注意的是,《申》报、“发现上海”的此种努力在当前的媒介行业中并不普遍,中国大部分的地方媒介没有表现出直接介入当地文化建构的自觉意识。
吴驷说,“发现上海”的目标一言以蔽之,是“占有”上海,这个“占有”的方式是,依靠媒介话语力量“再生产都市空间”。但还要追问的是,这个“空间再生产”的力量除了媒介还有谁?“媒介占有”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变成“大众的占有”?
本文为“‘传播与中国·复旦论坛’(2008):
传播媒介与社会空间”的会议论文,
注释参见原文。

【作者简介】
孙玮,1964年生,上海人,新闻传播学博士,现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媒介理论、城市传播、媒介文化研究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