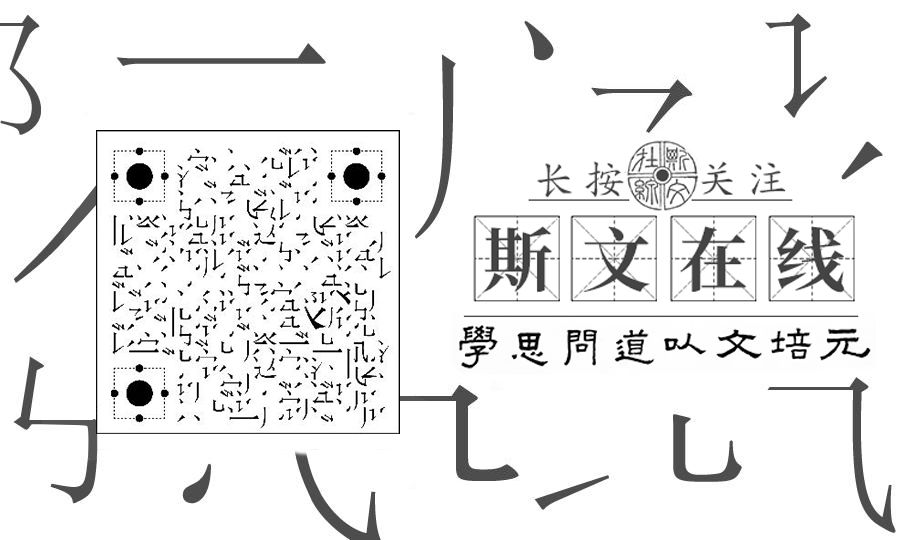面对浩如烟海的传统典籍,经过多种分类尝试,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脱颖而出,尽管此后偶有其他分类方法出现,直到清末民初,经、史、子、集四部之学始终是对本土典籍、学术和知识进行序列化的主流方法论。在近代西学东渐思潮的影响之下,西学的分科观念对传统学术和知识的分类方式提出了新的挑战。在体用分离的过程中,中国近代学术门类从四部之学逐渐演化为现代学科,传统典籍分类法也为杜威图书分类系统所取代,学界对此已有相当充分的讨论。从内容上看,旧有的“词章之学”大致对应后来的中国文学学科,清季民国是传统文章学经历解构与重建的时期,近代文章学理论的因创同时融合了传承出新的自省和应激干预的外求。词章之学因应西学知识分类体系的冲击而发生的异变,成为近代文章学理论转型的重要场域。壬寅学制中的《钦定大学堂章程》设有文学科,共分七目,其一即为词章学,所授内容划定为中国文章流别。其后,癸卯学制中的《奏定大学堂章程》改设中国文学门,课程设计中包含一项名为历代文章流别的课程。撰写首部本土中国文学史的近代学人林传甲,曾为优级师范生讲授《历代文章源流》,其所撰《中国文学史》通体架构也完全遵照清廷所颁学堂章程。可见,历代文章流别学科的设立与本土文学史的诞生息息相关。近代文章流别论的生成不仅形塑了早期文学史的书写范式,而且汲取了传统文章学体用兼论的要素,并在向现代文学学科转型的过程中,逐步实现了与西方文学史知识型的对接。
与此同时,经、史、子、集四部之学作为典籍文本的传统类目,成为近代文章流别论寻求话语转换的重要接入点。四部之学进入近代文章流别论的方式,不仅展现了前现代和现代文学观念所发生的碰撞,进而也影响了本土文学史的叙述模式和展开路径。首先,传统学术与文章关系密切,四部之学从学术流别转换为文章流别的分合升降,其历史脉络散见于历代学术史和文章学著述之中,清代官方意识形态对经、史、子、集地位的落定有直接影响。其次,爬梳经、史、子、集与文章之间的关系,并延展出文类优劣、文体考辨等一系列新的命题,几乎成为近代诸种文章学讲义或教科书的共性特征。第三,将四部之学尽皆纳入文章的范畴,是传统杂文学观仍在发挥效力的显著体现,对四部文章的分体认识与近代文章学理论的骈散之争也有着密切的联系。福柯指出,着眼于差异性符号的西方分类秩序科学催化了“知识型”的更迭。已有研究侧重作为本土“知识型”的四部之学因应西方分科治学冲击所发生的知识结构和学术观念的转型,而对四部之学进入近代文章流别论话语体系的研究着墨不多。本文拟从清末民初词章之学的界域内出发,考察经、史、子、集四部之学与近代文章流别论生成的理论渊源、具体表现和最终影响,以期对现代纯文学概念的反观自省以及古典文章进入文学史的标准问题讨论有所助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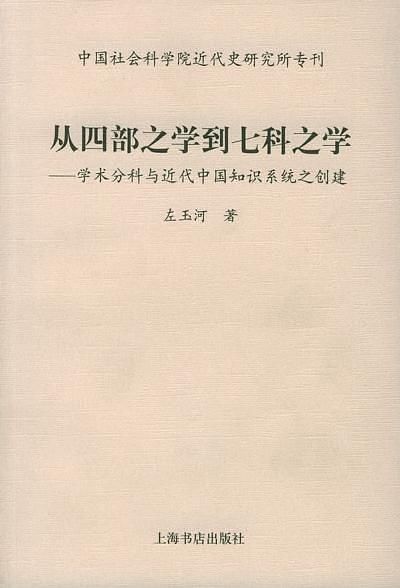
《奏定大学堂章程》中国文学门附中国文学研究法,建议文学研究须辨明“群经文体”、“周秦传记杂史文体”、“周秦诸子文体”、“史汉三国四史文体”、“诸史文体”、“汉魏文体”、“南北朝至隋文体”、“唐宋至今文体”等,并着重强调要明了“文章出于经传古子四史者能名家、文章出于文集者不能名家之区别”,意味着经传、古子、四史和文集作为文章本身和文章取法的对象,其位次存在高低,隐含经、史、子部文章优于集部文章的序列化倾向。可以说,也正是这一近代学制顶层设计的主导下,当时涌现出大量近代文章学讲义或教科书,从不同视角阐发经、史、子、集与历代文章流别的关系,成为早期中国文学史叙述的理论范式之一。追溯这一观点的理论起源的发展,需要首先考察经、史、子、集四部在目录学意义上独立分化的过程,及其与历代文章学理论的交互,尤其是清人对四部之学的态度。
汉魏六朝时期的论文之言,展现出了文体学的自觉意识,渐启有韵为文、无韵为笔之分。刘勰《文心雕龙·诸子》在经之作者为圣人、子之作者为贤人的认知基础上,得出“经子异流”的结论,进而辨析子与论的分别所在:“博明万事为子,适辨一理为论”。但其畅论诸子、史传,仍未脱离“论文叙笔”的基本框架,从全书的撰述宗旨来看,出于儒家传统要求的宗经意识也极为浓厚。经学对文学的影响源远流长,尊经意识在历代文论中都有所体现。同时期任昉的《文章缘起》从训诂学的角度,爬梳各体诗赋文章的名称、渊源和制式,也以文章源出六经之论为本。《颜氏家训》谓:“夫文章者,源出五经。”文本于经的思想深入人心,经部文字不仅能够统摄全部文章,文章的诸多体制也悉备于五经或六艺,往往成为后世论列文章之学的不刊之论。早在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成型以前,作为一切文章的导源,经传在传统文论中的导源性地位业已确立,且少有动摇。
史、子、集部与历代文章学理论交互的情况以及三者之间的升降排序则更为错综复杂。挚虞《文章流别集》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总集,惜已不存。“自挚虞创为《文章流别》,学者便之,于是别聚古人之作,标为别集;则文集之名,实仿于晋代。”刘歆作《七略》,中有《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子部始自树立,且其序位仅次于经部。王俭改录为《七志》。阮孝绪《七录》折衷众录,将《七志》之中的《经典志》、《诸子志》、《文翰志》分别更名为《经典录》、《子兵录》、《文集录》,新增《纪传录》,仅次于《经典录》,并对《纪传录》目录进一步细分,大致对应后世经、史、子、集的内容顺序也基本排定。相较于类目名称得以沿袭的经典、诸子二编而言,其改《文翰志》为《文集录》的理由是“窃以顷世文词,总谓之集”。至此,总集、文集始盛于六朝齐梁之时,作为文词之总名的集部也呼之欲出,成为四部中独立时间最晚的一部。《隋书·经籍志》最终成为经、史、子、集四部典籍目录分类确立的滥觞,其序次也沿用终始。
随着具有后世集部性质的文章篇帙日益浩繁,这些文本获得的学术评价和地位也不可避免地有所上升。南朝梁另一部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昭明文选》,在序文中提出了与过往不同的文章去取标准,以经文不得妄加裁剪为由不予收录,亦不取诸子“以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史传文字也以其繁博见弃,并将选文标准限定为“事出于深思,义归乎翰藻”的内容。《文选》的取法原则显示出“去笔化”的鲜明倾向,凸显了藻绘文章的纯粹价值,在尊经崇史的时代语境之中实属特出之论。此后,《文选》的理论脉络亦不时回响,为经、史、子部文本能否被视为文章的合理性质疑埋下了意义深远的伏笔。此外,钟嵘《诗品》对“羌无故实”、“讵出经史”的诗歌批评也颇有微词,对诗文未分阶段诗歌自是一家的独立地位有所回护。
但从历代文章分类的实践来看,集部一枝独秀的情况宛若昙花一现。南宋真德秀《文章正宗》虽出于尊经意图,赞成经文不当同录的观点:“《书》之诸篇,圣人笔之为经,不当与后世文辞同录”,客观上却摭拾包括了《春秋》、《史记》、《汉书》等在内的经史传记文字,“以为作文之式”,在诗赋类中,编者也“尝欲抄取经、史诸书所载韵语”,表达了取材于经史文字的编纂思想。《文章正宗》虽然首度将经史二部纳入到文章的范畴,但其以理为本、文辞虽工不取的选录原则,恰恰抹煞了集部文字独立的文学艺术价值,在推崇经、史的同时对集部有所贬损。另一方面,为集部张目者也往往不甘示弱,主动与经史文字划清界限。例如,杭世骏《袁才子文集序》云:“文莫古于经,而经之注疏家非古文也,不闻郑《笺》、孔《疏》与崔、蔡并称。文莫古于史,而史之考据家非古文也,不闻如淳、师古与韩、柳并称。明清之际此类文论风气尤盛,体现了对注疏考据侵蚀文域的反拨。
尽管经、史、子部与文章的交互属性长时间处于众说纷纭的状态,此三者作为文章体制取法的根柢之学始终有理论脉络可循,并在从学术流别转化为文章流别的过程中,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差序化格局。南宋陈绎曾《文章欧冶》持论和《文心雕龙》经子作者为圣贤分途的论述逻辑如出一辙,进而将史传文字也增补进入既有的等级序列之中:“六经之文,诸子不能及者,圣人也;诸子之文,史不能及者,贤人也。”经、子、史之文三者的位次更定可见一斑。但从维护学术正宗的立场来看,经、史、子的排序同样也不乏具说服力的阐释,且渐有后来居上的苗头。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类叙云:“夫学者研理于经,可以正天下之是非,征事于史,可以明古今之成败,余皆杂学也。”经、史可以正是非、明成败,子部虽属杂学,犹可“与经史旁参”,以资借鉴,而集部不仅内容羌杂、泥沙俱下,多半还充斥着文派纷争,又等而下之。邵长蘅《与魏叔子论文书》谓“读书先于治经”,随后“综贯诸史”,之后再“旁及子、集”,所倡导的读书顺序同样也是经、史、子、集。
作为文章的取法源头,经之地位最尊,史、子二者的位次互有先后,集则殿后,但经、史、子、集的排序在近世渐成为主流,成为四部之学在传统词章学论述中的基本差序格局。这一差序格局的形成,一方面可以归因于四部之学对应的学术位格本身的差异,经本位思想尤其源远流长:“《五经》、《四书》,五谷也;史籍艺林,脯醢盐蔬茶洒也。贯穿餍饫,可以养生,可以长世。若诸子、佛老,则海外奇品,适口滋毒者也。”因此,历来论者多以四部之学的正欹主辅叙定其作为文章素材或取法文本的价值。一方面,四部的差序地位也和历代文章学贵古贱今的历史思想传统有关。如清人叶元垲转引姜南《叩舷凭轼录》,沿用前代经、子、集之文层层递降的逻辑,用来解释文章代降而卑的现象:“盖周之文,六经、孔孟也;七国之文,诸子之文也;汉之文,文士之文也。道失而意,意失而辞,可以见诸子不如六经、孔孟,文士不如诸子也。”六经、诸子、文士之文其所从出,在时间上既有先后之别,则大道失真,卮言日出,其思想价值也每况愈下。
明人尚论集部之学,“凡典册不越经史子集,集亦学也。或以为为文尔,集固独文,其间用有与经史同焉,又乌可以不博”,但到清代却为之一变。清代乾隆时期官修《天禄琳琅书目》持论云:“係以集部之书,固不必如经、史、子篇目,各沿奉为圭臬也。”集部地位在清代发生骤降,与明清之际尚实学、重考据的学术风气有关。清代章学诚《文史通义》明确将经、史、子、集在词章之学中的序列问题推到时代的前台。《文史通义》在尊经的前提下抛出了“六经皆史”的论断,虽非首创显豁之论,却也为从历史角度辨析文章学的学术源流奠定了方法论范式。由于章氏的学术史观念具有崇古薄今的倾向,在梳理文章流别的过程中,他提出,战国之文源于六艺,后世文体皆备于战国,究其原因在于经、史、子三者专家衰歇,渐次分化为文集中的经义、传记和论辩,正发生在战国之际:
“子史衰而文集之体盛;著作衰而辞章之学兴。文集者,辞章不专家,而萃聚文墨,以为蛇龙之菹也。后贤承而不废者,江河导而其势不容复遏也。经学不专家,而文集有经义;史学不专家,而文集有传记;立言不专家,而文集有论辨。后世之文集,舍经义与传记论辨之三体,其余莫非辞章之属也。而辞章实备于战国,承其流而代变其体制焉。”
为了说明文章流别的大略情形,章学诚举出的两对概念分别是“子史”与“文集”、“著作”与“词章”,两者之间分别存在着因果关系。正因为道为天下所裂,子、史不以家名,文集方始兴盛,又由于子、史之职不得官守,只能借助于著述文字,但伴随着古学的分崩离析,连这著作形态也风流云散,终竟沦为词章。著述“衍为文辞”,而文辞又“生其好尚”:
“汉、魏、六朝著述,略有专门之意。至唐宋诗文之集,则浩如烟海矣。今即世俗所谓唐宋大家之集论之,如韩愈之儒家,柳宗元之名家,苏洵之兵家,苏轼之纵横家,王安石之法家,皆以生平所得,见于文字,旨无旁出,即古人之所以自成一子者也。其体既谓之集,自不得强列以诸子部次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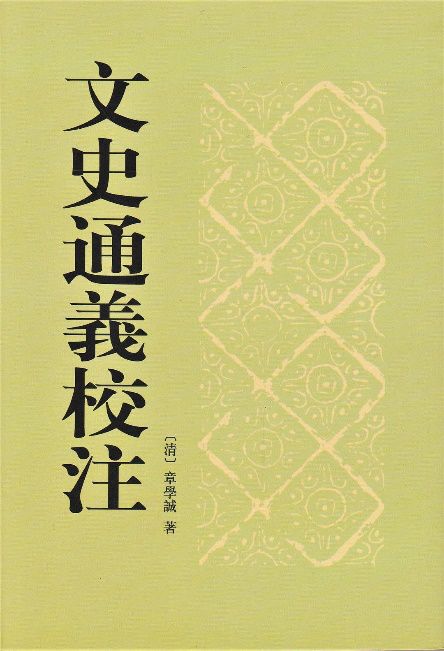
文集的前身即是诸子的一家之言。因此,就章学诚对文章流别的历史观照而言,经、史、子、集四部之学中,以史的观照作为方法论,文集之兴虽可溯源至诸子,但已然是诸子裂道、“礼失官废”之后的支裔了。因此,他主张文集迥异于经、史、子三者,不当称其为学:“古人以学著于书,后人即书以为学。于是专门经史子术之外,能文之士,则有文集,涉猎之家,则有说部,性理诸子,乃有语录,斯三家者,异于专门,经史子术,可以惟意所欲。”章学诚的集部劣等化思想反映了清代中叶颇具代表性的学术立场,对近代词章之学的发展也影响深远。
据张之洞《书目答问》集部别集类条下注,其于清朝文人别集“除诗文最著数家外”,仅取“其说理纪事考证经史者”,其所撰《輶轩语》也明确提出读集不能工文的观点:“近代文集,鄙者无论,即佳者少看数部亦无妨。多读经、子、史,乃能工文;但读集,不能工文也。”张之洞是晚清癸卯学制的制定者,推定这一表述与《奏定大学堂章程》中的“文章出于经传古子四史者能名家、文章出于文集者不能名家”之间存在直接联系,似也未为过分。而早在清末新式学堂大量兴起之前,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曾提出在各省设立面向二十五岁以下人士的学堂,规拟课程内容之一为“诵经史子及国朝掌故诸书”,亦将集部摒于所学之外。
无论是作为历代文章取范之源还是被视作文章本身,经、史、子、集四者在历代文章学理论中的位次和地位时有升降。又由于清代向慕实学的治学风气使然,章学诚《文史通义》从史本位出发爬梳历代文章流别,其“子史衰而文集盛”的观念成为近代文章流别论的重要理论渊源,而癸卯学制的纲领性意见也在清末民初词章之学的学科建制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成为经、史、子、集四部之学进入近代文章流别论并发挥作用的历史条件和理论传统。
清末《奏定大学堂章程》设有历代文章流别一科,明告此科教员可仿照日人文学史著述撰写讲义,为文章流别与文学史的合流开启了方便法门。但是,历代文章流别科的讲授仍然面临诸多实际问题,首当其冲者便是划定历代文章的范围。诸如“若六经之文,非可以文论者”。这般,将儒家经典看作文章是对经部典籍和尊经传统“轻渎”的传统观念不再壁垒森严,经、史、子、集四部文本开始尽皆被纳入到文章的范畴:“吾国文章范围颇广,举凡政治、哲理、历史、舆地,苟藉文字以见者,悉包括于文章之中,所谓经史诸子皆文是也。”中国传统学术与文章同源,经、史、子、集四部之学也天然具备从学术流别转向文章流别的条件。有学人指出,传统目录分类法存在“辨体”和“辨义”之分,如荀勗七略“以学术之流别为主,不以体裁为主”,即属辨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以体裁为主而不以学术为主,属“辨体而不辨义”。这一论断或许仍有可商榷处,但近代文章流别论无疑进一步淡化了四部之学的“辨义”成分,而将经、史、子、集的“辨体”要素发挥到了极致。章学诚的文章流别论及其对四部之文分化迁转的叙述逻辑,不仅为近代文章流别论的“辨义”提供了学术话语的基本土壤,而且也成为四部之文“辨体”的理论起点。
为近代文章流别科所撰的多种讲义或教科书以及大量近代文章学著述,明显受到章学诚以文集为后出、文集不如著述、集部劣等化等学术思想的影响。如马絅章《效学楼述文内篇》“论古来文章流别”一节所云:“经、史、子、集四部,质言之,经,载道者也,史,记事者也,子以谈理为宗,集以摛词制胜者也……子家各有宗门,而其典章制度之属,多与经史出入;惟文集之名,出现稍晚,其体最裂。”把后出的文集视为裂道之体,与章氏所论一脉相承。近代湖北罗田学人王葆心所撰《古文辞通义》为现存历代文话中篇幅之最巨者,该书前身为师范学堂讲义,后更此名即步趋章学诚《文史通义》,书中全篇引证了章学诚有关经、史、子、集四部文章的流别叙事,作为撰述的宗旨和取法对象。来裕恂《汉文典》把文章体裁分为“撰著之文”与“集录之文”,前者指“君师道判,政教权分”以后诸子百家的著述,后者则是道裂学散之后的产物:“自专门之学微,而撰著之作衰,亦自撰著之作衰,而文集之名起……自《七略》流为《四部》,而集录之体,日益发达不可遏,然古义荡然焉矣。”这一论述逻辑也和章学诚对经、子、集三者演化关系的看法完全一致。从述学体例来看,不少近代文章学撰述也都选择章学诚《文史通义》作为比附的对象,其原因或在于章氏治学风格和观念易与西学对接,利于在阐发传统和比附西学之间获得平衡:“章学诚的学问路数本来并不见重于世,但因为与西学有些形似,容易附会,所以成为近代趋新学人再发现的重点。”《文史通义》以类相从、追求横通的著述体例和追求本也出入子、史之间,既有自成一家、独树一帜的理论感召,也有贯通文史、纵论分合的学术立场。

在清末词章之学的学科范围内,外来的分科治学要求与本土固有的知识体系发生击撞,鲜明地体现在以经、史、子、集的文章之体来对接情、事、理的文章之用。历代文章学不乏关于文章体用关系的表述,伴随古代文体学的发展,世人对文章体用关系的认知也逐渐深化。王世贞曾以理、事、词三者隐括历朝文学,魏禧提出文章之用不外乎明理、适事。以清代两大古文派别为例。阳湖派恽敬是嘉道时期倡导子家之文的重要人物,欲以子部救文集之失,并用言事、言理、言情区分文词的效用:“言理之辞,如火之明,上下无不灼然,而迹不可求也;言情之辞,如水之曲行旁至,灌渠入穴,远来而不知所往也;言事之辞,如土之坟壤咸泄,而无不可用也。”桐城派刘大櫆《论文偶记》则谓:“理不可以直指也,故即物以明理;情不可以显言也,故即事以寓情。即物以明理,《庄子》之文也;即事以寓情,《史记》之文也。”也隐约将明理、寓情之文与子、史文章进行钩连。
尽管传统的文章体用论对文章表情、言事、明理的作用有所认识,近代文章学著述中首次且集中地出现了大量以经、史、子、集四部的分体学说来对应情、事、理三种文章作用的表述。例如,在辨析经、史、子学术渊源的基础上,前揭王葆心《古文辞通义》提出用情、事、理三者统摄四部之文的体用范畴:“绎章氏之意,盖可知三门之分自经史子。经义分自经类,在著述门,为说理;记载分自史类,在记载门,为记事;论辨分自子,其类亦统在著述之说理。告语一门亦言经,左史之遗,推合其类应并出自经史。三者之外统归词章,词章则抒情一类之汇。而情、事、理三者之流别明矣。”将经、史、子和词章分拆归入告语门、著述门、记载门,分别对应抒情、说理、记事三种行文的功能和目的。
又比如,桐城殿军姚永朴《国文学》云:“古今著作,不外经、史、子、集四类,约而言之,其体裁惟子与史而已。盖子有二派,老、庄、孟、荀、管、墨诸家,皆说理者也,屈、宋则述情者也,左邱明、司马迁、班固以下诸史,则叙事者也。经于理、情、事三者,无不备焉,盖子、史之源也。如子之说理者本于《易》,述情者本于《诗》;史之叙事者,本于《尚书》、《春秋》、三《礼》。此其大凡也。集于理、情、事三者,亦无不备焉,则子、史之委也。”这一观点在其之后所撰《文学研究法》中得到了悉数保留。在文皆源出于经的前提下,他主张经兼有理、情、事三者,子部多说理,史部多叙事,集部为子、史之流,亦兼理、情、事三者,用总分总的形式梳理四部之学与文章体性论,同时也凸显了文章流别在时间发展上的线性关系。
高步瀛《文章源流》仿挚虞《文章流别志论》而作,同样也以理、事、情三者分别对接子、史、集三部:“文章之类别,可括为三:一说理,二叙事,三言情。以经言之,《易》,说理者也;《诗》,言情者也;《尚书》、《春秋》、‘三礼’,皆叙事者也。然如《仪礼》之记传,及大小戴《礼记》,则又兼说理者也。以史、子、集言之,《史记》、《汉书》诸史,皆主叙事;《老》、《庄》、《管》、《墨》诸子,皆主说理;集如屈、宋、司马相如等,皆主言情。然三者,非有一定之界域,此不过就其毗重者言之。”作为吴汝纶的高弟,他和姚永朴的看法颇为接近,认为经兼三者而有之,子、史、集分主说理、叙事和言情。
刘咸炘《文学述林》将文章分为外形和内实,指出外形之体性由内实而定,可归为事、理、情三者,并将其与史、子、集部文字作大体对应,惟经部文字未涉其中:“事则叙述(描述在内),理则论辨(解释并入),情则抒写,方法异而性殊,是为定体。表之以名:叙事者谓之传或记等,史部所容也;论理者谓之论或辨等,子部所容也;抒情者谓之诗或赋等,古之集部所容也。”阐明事、理、情是文章撰写的目的所在,为文之用,叙述(描写)、论辩(解释)、抒写则是文章撰写的具体方法,为文之体,传记、论辩、诗赋等文类名称,为文之名。从“古之集部所容也”一句可以看出,刘咸炘在以四部之体对接文章之用的过程中,虽仍沿用四部之文的提法,却明显有了区别古今的概念,传递出对四部容受文体与文章写作方法之间的不合时宜之感。
经、史、子、集是传统学问和典籍的分类方法,文之用归于情、事、理三者也是古代文章学理论的组成部分,但是近代文章流别论将二者进行对接的做法以及对后者阐发的深入程度皆为过去所不及。四部之学与文章体性论之所以在清末民初的时间点上发生直接的联系,与域外文章学思想的传入有着一定的联系,显然受到了后者的启发和刺激。
20世纪初刊载于《新民丛报》上的马君武《法兰西文学说例》,提出散文分为五种,分别是记事、辩论、学说、戏剧和书牍。这一观点正为王葆心《古文辞通义》所化用,以记事、辩论和书牍分别对应记载门、著述门和告语门。又如,来裕恂《汉文典·文章典》,是在吸收日人大槻文彦《支那文典》、儿岛献吉郎《汉文典》和《汉文典续》等域外近代文章学思想的基础上进行的。该书将文体分为叙记篇、议论篇、辞令篇。其中,“古今称叙记之文,《左传》、《国语》、《史记》、《汉书》而已”,“议论之文,所以治世,经邦论道,莫重于斯,有诸子之遗风”,辞令篇则涵盖告语文和诗赋等。这一分类方法受到儿岛献吉郎《汉文典续》叙记体、议论体两种即可涵盖一切文章的影响,同时也保留了辞令篇的传统文体类目。近代文章学学人在平衡和融合域外及本土文章学思想方面所作出的种种努力,可见一斑。
上述清末民初的文章流别论中,集中出现以情、事、理三种统系统摄四部文章的现象,还隐约延伸到了日后经过东洋改造而间接传入国内的“知、情、意”三分法。“知、情、意”的三分式认知结构最初源于古希腊哲学,在西方语言学转向的发展趋势中成为西方文体分类的内在逻辑,又为日本近代文学、哲学、语言学学界所吸收,进而传入中国,并在哲学、教育学、文学领域内被不断引用和书写。在近代文章学领域,“知、情、意”普遍被阐释为知识、情感、意志,分别用来对应不同的文章体类。比如,黄人《中国文学史》(1904年)的文体观就是由心理学的“知、情、意”映射到文学领域并加以变通的典型例子:“人之心理上有知、情、意三方面,而发现于外部者,行为与言语也。广义之文学,由于言语,知、情、意皆可从此发现,而由上节观之,则文学可分二种类:(一)知的文学,(二)情的文学。而美之文学属于后者,以感情为最精之本质。”这样的阐述在清末民初的教育界流行一时,几为众口一词:“夫文章之体制,有知的文章、情的文章、美的文章”。特别是到20世纪20年代以后,“知、情、意”三分法在文学教科书中得到进一步普及,并与文章具体的表达方式相联结:“许多学者根据知、情、意把文学分成不同的类型,表现出现代杂文学观的鲜明倾向。这可以从梁启勋、谢无量、陈启文、胡怀琛、卢冀野、童行白等文者的论述中清晰地看到。”因此,近代文章流别论中的情、事、理三者,既上接经、史、子、集的传统文章分类逻辑,也下启知、情、意的现代文章体制。
可以说,用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对接情、事、理三种统系的文章流别论,正介于传统文章学向现代文章学的新知识型转化的过程之间,体现了近代文章学丰富多元的理论空间。如马絅章《效学楼述文内篇》所言:“吾辈今日欲辨流别,则经、史、子、集之合而分、分而合者,不可不从其朔,而悉以文观之。此固人事自然之则,而亦为研览文学史者所当知也。”四部文体与文章体性论的分合感应,揭示了传统学术和文章门类与外来文体分类观之间的拉锯,也为文章流别和日后文学史的书写提供了可供选择的叙述范式。
通观历代诗文总集的编选史可知,《文选》弃录经、史、子的做法并非主流。尽管历来尊经传统根深蒂固,在清代以前,经部文字亦鲜少被选入诗文总集,而史部和子部文本被纳入到文章选辑范围内却并不少见。章学诚通论文史之举,前亦有兆,通代诗文选本如姚铉《唐文粹》、吕祖谦《宋文鉴》、苏天爵《元文类》等,其编纂宗旨都是力求包括一代文章之有关天地国家者,与正史相辅而行。另一方面,历代著者对子部之文亦有分说,虽然“诸子之作皆为学术而作,皆非为文而作文也”,赵岐《孟子题辞》、郭象《庄子序》等也都对诸子之文的修辞特点不吝美辞,为从诸子之学转向诸子之文的视角转移打开了局面。清代诸子学的兴盛为子家文派的崛起创造了条件,嘉道时期恽敬、龚自珍、包世臣等明确提出“文集之衰当起之以百家”,主张用说理性强的子家文章纠偏纤弱不振的时代文风。这些都为清末民初西学东渐观念影响下重新审视经、史、子、集四者之间以及四者和文章之间的交互关系作了学理上的铺垫。
姚鼐《古文辞类纂》虽未将史、子文字选入集中,仅在考镜论辩类源流之际略微提及:“论辨类者,盖原于古之诸子,各以所学著书诏后世。”但据《经史百家杂钞序例》可知,曾国藩本于姚鼐选辑《古文辞类纂》进行增删,除简化和变更序目外,明确表示将姚氏不录的六经、史传也采入古文辞的选本之中,且冠以“经史百家杂钞”之名。对此,朱东润先生指出,曾国藩对古文辞内涵的界定最为宽泛:“曾氏之言古文,既包经史百家言之,而旁通之于骈文,故古文之领地,至是遂最为庞大。”实际上大大拓展了古文的范围。曾氏开列的读书清单亦与其编纂选本的观点相一致:“盖《史记》、《汉书》,史学之权舆也;《庄子》,诸子之英华也;《说文》,小学之津梁也;《文选》,辞章之渊薮也。”经、史、子不仅是文章取法的源头,其本身也可被视作文章之一部。这样的做法在清末民初引发了极大的反弹,支持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对经、史、子、集四部文本所具有的“文学合法性”产生分歧的理论出发点,既与外来文学观念的引介和渗透有关,也与骈散易趣的近代文章学派分理念有关。
清末西方文学进化论和纯文学观念的引入,带来了文学批评方法的更新和文学史书写范式的演进。长期以来,在经、史、子、集四部文章的升降差序之中,以经部地位最为尊崇,集部则始终屈于末流。与清代中叶诸子学和诸子文派的起复相比,集部之学和文集之名亦未有丝毫起色。但这一状况在清末民初文学标准的重新确立中遭到了极大的颠覆,纯杂文学观念的传入对经、史、子、集四部的再认识产生了偌大的影响。朱自清曾在《文学的标准与尺度》、《什么是文学》等一系列文章中指出,原先以诗文为正宗的传统文学基本以“儒雅风流”为标准,新兴的语体现代文学“大部分是受了外国的影响,就是依据着种种外国的标准”,但在文学传统里也能找到它的因子:“‘纯文学’、‘杂文学’是日本的名词,大约从De Quincey的‘力的文学’与‘知的文学’而来,前者的作用在‘感’,后者的作用在‘教’。”同时,在破除杂文学体系、建立纯文学观念的进程中,经、史、子、集部文本的“文学性”也迎来了新的验示。
刘咸炘曾梳理文学定义和范围的演变历程,指出本土传统文学概念经历了从册籍之学到集部专名,由文笔之分到归于质朴的古文,所指范围广狭不同,持论间有反复,至近世又引入纯杂文学的概念:“最近,人又不取章说(按:指章太炎),而专用西说,以抒情感人、有艺术者为主,诗歌、剧曲、小说为纯文学,史传、论文为杂文学。”根据他的观点,纯文学将文章格调设为阑入文本的标准,“正与《七略》以后齐梁以前之见相同”。可以见出,由于纯文学设立了以作品美学价值为转移的准入标准,集部反而成为优先同时也是最易被认定为具有纯文学性质的文本,而隶属于经、史、子部的文本却往往被划入杂文学的范畴。这样的处置既延续了清代中后期文笔之分的理论重提,也暗含了近代选学和古文两大阵营的文章学思想的对峙。
主张骈散合一的阮元溯源文章传统,以《文选》录文原则为准绳,主张辞章理应区别于经、子、史:“昭明所选,名之曰‘文’。盖必文而后选也,非文则不选也。经也,子也,史也,皆不可专名之为文也……然则今人所作之古文,当名之为何?曰:凡说经讲学皆经派也,传志记事皆史派也,立意为宗皆子派也,惟沈思翰藻乃可名之为文也。非文者尙不可名为文,况名之曰古文乎?”他强调,经、子、史与文章未可一视同仁:“近之为古文者,以彼所弃,为我所取,立意之外,惟有纪事,是乃子、史正流,终与文章有别。千年坠绪,无人敢言。”与此同时,阮元也指出,古文家的阵地却多集中在经、史、子三部,与《文选》的路数截然不同:“昭明选例以沈思翰藻为主,经、史、子三者皆所不选。唐宋古文以、经、史子三者为本,然则韩昌黎诸人之所取,乃昭明之所不选,其例已明著于《文选》序者也。”他将文选派和古文派发生分歧的原因归为奇偶成分的差异:“其不合之处,盖分于奇偶之间,经史子多奇而少偶,故唐宋八家不尚偶,文选多偶而少奇,故昭明不尙奇。”和他同时的梁章钜在《退庵随笔》中,先是驳斥了友人谢金銮关于《文选》道理、事理、文理皆有不足的看法,继而援引阮元《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全篇文字,力排众议,扬骈抑散:“为文章者,不务协音以成韵,修词以达远,使人易诵易记,而惟以单行之语纵横恣肆,动辄千言万字,不以为烦,不知此乃古人所谓直言之言、论难之语,非言之有文者也。”对真德秀《文章正宗》等历代诗文选本阑入经史文字也颇有微词,《文选》则是清代骈散合一论者引以为据的出发点。
另一方面,姑且不论韩柳自述为文旁搜远绍,于经史子无所不取,仅就清代桐城派而言,桐城派先驱之一方以智曾论取材次第云:“昔人谓胸中先有六经、《语》、《孟》,然后读前史。史既治,则读诸子,是古人治心积学之方,往往有叙有要。”明确将经史子三者视为文章薪火之要素。方苞奉敕选编《钦定四书文》,评价明代时文有云:“至正、嘉作者,始能以古文为时文,融液经史,使题之义蕴,隐显曲畅,为明文之极盛。”对采撷经史入文予以表彰。吴德旋《初月楼古文绪论》直接将史书看作文章之一部:“《史记》、两《汉》、《三国》、《五代史》皆事与文并美者;其余诸史,备稽考而已,文章不足观也。”湘乡派曾国藩也对熟读经史子有助于古文有过反复申说:“长于《易》者其言精深而奥洁,长于《诗》者其言温雅而飘荡,长于《书》者其言重硕而通达,长于《礼》者其言严慎而暇愉,长于《春秋》者其言浑朴而简峻,长于史者其言恢奇而溥博,长于子者其言纵厉而峭实。”考虑到《经史百家杂钞》的编纂,曾论看重经史词章的意味更为深厚。
因此,清代骈文和古文之间本就存在骈散异趣的分歧,但两者的矛盾在清末民初的文章学语境中显得愈加突出,并鲜明地体现在四部文章与纯杂文学观的呼应关系之中。有学者业已指出,刘师培的文章发展史观上承刘勰对文章流别的梳理以及章学诚在文史研究方面的路数,将文章的发展纳入学术史视野进行考察。同时,刘师培又是近代选学的坚定支持者,坚定主张古文即是经、史、子,骈文方对应于集部:“诚以古人不立文名,偶有撰著,皆出入六经、诸子之中,非六经、诸子而外,别有古文一体也。”经、史、子被归为古文的界域,集部的特殊地位得到凸显,骈文亦得以抬升。如郭象升《五朝古文类案叙例》也认为,经、史、子历代多有删订,而选辑一法则为集部所独有:“夫删订之业,圣人所以约义理而扶人纪也,其于经史诸子,宜皆可施;而昭明选例,但取文士之华辞,选辑一途,亦随为集部所独擅。”在承认集部特性的基础上,他进而提出骈文方是集部独立价值的唯一载体:“所谓骈文者,义固绝远于经史诸子,而亦以此故,有独立一部之精神,而散不尽然。”从经、史、子三者与集部的区别出发,分论骈散的歧异,成为近代选学文章学理论的独特风景。
相较之下,近代散文文章学虽亦对此有所论说,但其所持论据大多仍未脱离传统文章学的理论框架。孙学谦《文章二论》“溯源第一”强调“溯文之源必于经”,将散文分为三类:“夫文之途百变,其用万殊,而言其派别,则史氏、学子、辞流三者而已。”所谓史氏之文、学子之文和辞流之文,即对应史、子、集三部,其核心仍然是文本于经的路数。林纾曾谓:“经生之文朴,往往流入于枯淡;史家之文,则又隳突恣肆,无复规检。二者均不足以明道。”则对古文阑入经史文字的现象也有所戒惕。而大部分散文阵营的文论家都如前所列,在各自的文章流别论叙述之中,直接在经、史、子、集四部与文章体性论的分合之间为之弥缝,借助文章流别论的新新叙事,为涉及经、史、子等羌杂内容的散文提供具备文学合法性的证明。而国人所撰本土首部中国文学史——林传甲《中国文学史》,其论文立场仍是骈散兼议:“于文章(古文、骈文)取资广博,兼收四部乃至医、算各家,在芜杂中却强烈体现其‘杂文学’观念”,显示出早期文学史仍受到传统文章流别论范式的影响,未可遽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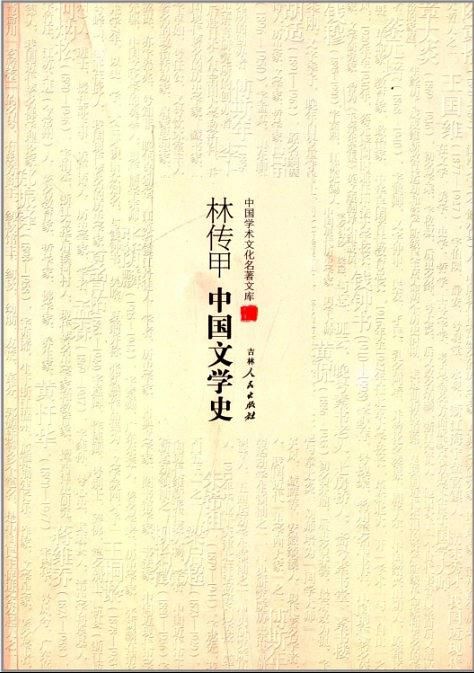
但是,清末的文章流别论逐渐为文学史的书写所替代,前者的侧重点也从四部文章流变和体用改换到了具有文艺美学价值的经典作品赏析:“《奏定大学堂章程》与《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的巨大差别,不只在于突出文学课程的设置,更在于以西式的‘文学史’取代传统的‘文章流别’。”在这之中,文学观念自身的演进无疑发挥了极大的催化作用:“近代作家在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下,对文学本体的认同、文学审美特性的论述,都有助于纯文学观念的确立。”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纯文学、纯文艺观念的确立,充分肯定了集部的独立价值和地位,却也为古代文学史的去取标准设置了新的难题。
中国传统学术与文章往往互为表里,经、史、子、集四部之学既表征了传统学术和知识体系的类型,又由典籍图书目录的分类而衍生出四部之文的概念。受到西方分科治学的影响,清末民初旧有的词章之学面临着爬梳文章流别、书写本土文学史的需要。“文集之兴,盖以学无专师,杂无可投,故以集统之。文史之兴,盖由文章既繁,渐成专业,故有史以名之。”章学诚对传统学术和文章流别分合迁转的梳理,成为近代文章流别论的主要理论渊源。受到传统文章学和域外修辞学击撞产生的影响,大量近代文章流别讲义或教科书将经、史、子、集四部之文和文章体性论加以对接,深化了对传统文章体用论的认识,初步揭示出容受经、史、子内容的杂文学传统和西方文学观念之间存在的龃龉不合。由于纯文学标准的传入和确立,支持骈文或骈散合一的文选派卷土重来,客观上也为集部优先获得文学概念的认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经、史、子、集所代表的传统知识型在西学东渐的语境中不断遭遇祛魅,势必为新的现代知识体系和学科分类所代替。蔡尚思《中国学术大纲》甚至曾提出用文字学、史学、哲学和文学的“新四部”取代老四部:“按诗词一类,实为纯文艺的文学(原注:文学的文学);至于古文反比较不足以为代表。”而小学的文学、史学的文学、哲学的文学和文学的文学,可总之为“广义的文学”。四部之学在近代文章流别论中的演化和新变,折射出过渡时代文章观念和文学概念的变动不居。与此同时,当前本土文学史的书写困境仍未得抒解,与“文学性”更强的诗词歌赋相比,体量庞大的古代文章作品应以何种标准、何种方式、何种比重采入文学史中,始终是困扰文史研究者的难题。郭豫衡《中国散文史》主张回归《文选》传统,将作品有无“沉思翰藻”作为选入散文文学史的基准:“从汉语文章的实际出发,这部散文史的文体范围,也就不限于那些抒情写景的所谓‘文学散文’,而是要将政论、史论、传记、墓志以及各体论说杂文统统包罗在内。因为,在中国古代,许多作家写这类文章,其‘沉思’、‘翰藻’,是不减于抒情写景的。”古典散文进入文学史的标准问题始终悬而未决,回归近代文章学的历史语境,抉发四部之学与近代文章流别论生成的关系,或许能够对这一议题的深入讨论有所推动。
原刊于《文学评论》2020年第2期,有删节。这里发布的是原稿。
参考文献
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学术分科与近代中国知识系统之创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
陈国球:《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朱有献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王水照编:《历代文话》,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桑兵:《治学的门径与取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姚永朴:《国文学》卷一,京师法政学堂宣统二年刊本
余祖坤编:《历代文话续编》,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
[日]儿岛献吉郎:《汉文典续》,富山房1903年版
霍四通:《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建立——以陈望道<修辞学发凡>考释为中心》,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陈柱:《中国散文史》,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刘师培:《论文杂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林纾:《畏庐文集》,民国丛书第4编,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版
郭延礼:《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
张雪蕾:《中国文学史表解》,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
蔡尚思:《中国学术大纲》,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
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作者简介】
常方舟,1988年生于上海,2010年获北京大学文学学士学位,2016年获复旦大学文学博士学位。求学期间,曾赴台湾清华大学、日本国学院大学访学交流。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主编:朱生坚
编辑:张晴柔
运维:任洁
制作:蓝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