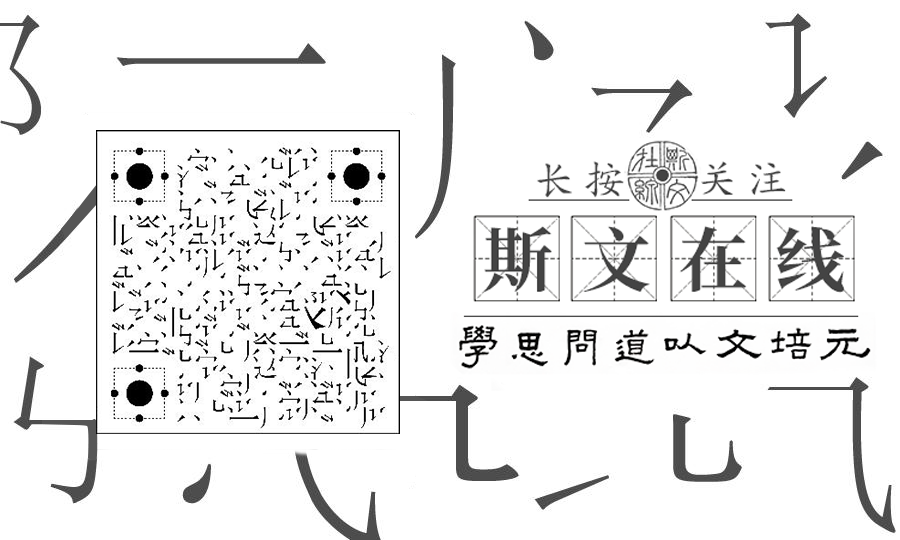在西方人文主义发展史上,维柯是极少数真正具有开创性的思想者之一。而他迄今尚未在中国学界得到应有的认知。朱光潜先生燃尽最后一段生命之火,用于翻译《新科学》;可惜他未能充分阐述,何以由此“稍懂得一点历史发展的道理”。蒯大申老师这篇文章写于三十年前,现在看来当然不无可商榷之处,但是我们更希望它能引起更多人对于维柯的关注、阅读和研究。
翻译意大利思想家维柯(Giambattista Vico,1668~1744)的代表作《新科学》(Scienza Nuova),以及对维柯思想进行系统的研究,是朱光潜迟暮之年所进行的最后一项浩大工程。《新科学》初版于l725年,1744年所出第3版为定本,标准文本是意大利文。全书共5卷,加上序论和结论,英译本是厚达400多页的一部煌煌巨著。中译本加上《维柯自传》,有近50万言。这部巨著不仅结构复杂,文字艰奥,而且内容涉及神话、宗教、西方古代史、罗马法学、哲学、语言学等众多知识领域,其译事之难更甚于黑格尔的《美学》。朱光潜说,这是他一生中遇到最难译的一部书。

Giambattista Vico
朱光潜与维柯有缘,一如他与克罗齐。早在二十年代留学英国时,朱光潜即从研究克罗齐进而注意到克罗齐的精神导师维柯。朱光潜曾说:“我的美学入门老师是意大利人克罗齐,而克罗齐是维柯的学生。克罗齐早已说过,美学的真正奠基人不是鲍姆嘉通,而是维柯。所以研究美学就不能不知道维柯。”六十年代朱光潜在编写《西方美学史》时,曾在上卷专辟一章介绍维柯,对维柯的历史发展观及其“诗性智慧”对美学发展的意义给予高度评价。到晚年,朱光潜在深入钻研了马克思主义一些经典著作之后,越发感到维柯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和美学发展史上的重要性,认为维柯的历史贡献不仅在于他创建了近代社会科学,而且还创立了社会科学方面的历史发展观点,他的历史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有密切的批判继承关系。
为了正确、深入地理解维柯,为了推动中国美学事业的发展,朱光潜从1980年春开始,以83岁高龄,不顾一天衰似一天的身体,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倾全力投入翻译《新科学》的工作,把翻译《新科学》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是一场真正的攻坚战。朱光潜原计划化一年半时间译完全书,后因年老多病推迟约半年,到1981年下半年终于译出《新科学》初稿。《新科学》译出后,他又化了一年多时间进行仔细校改,同时翻译《维柯自传》。在此期间,他还撰写了《维柯的〈新科学〉及其对中西美学的影响》等有关《新科学》的评介若干篇,这些工作到1983年底才基本完工。1984年,《新科学》终于交人民出版社付梓。《新科学》终于耗尽了他的心血,耗尽了他的生命。1986年5月,《新科学》终于正式出版,但此时朱光潜已辞世两个月了。虽然朱光潜生前没能看到这部译作问世,但这部译作却成了纪念这位视学问如生命的粹然学者的永恒丰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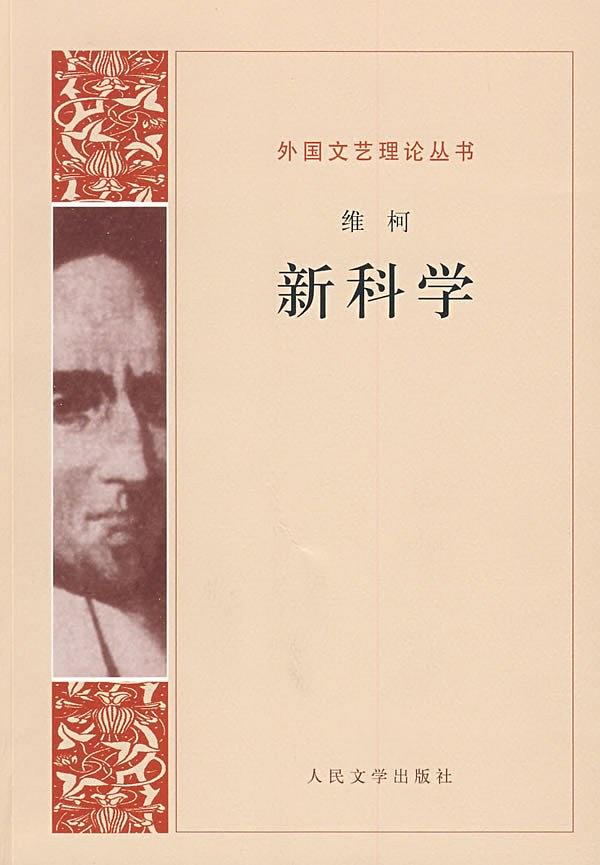
《新科学》书影
朱光潜在翻译《新科学》的同时,曾写过多篇文章对维柯的思想进行研究和阐发。这些研究和阐发就像一面镜子,不仅反映出他晚年倾心关注的问题之所在,而且也反映出他晚年对这些中国当代美学建设和未来美学发展中关键问题的态度和基本看法,从而使我们得以把握他晚年美学思想的基本面貌。
1
朱光潜着重阐发的是维柯三个方面的思想:(1)“认识真理凭创造”;(2)“人类世界是由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3)有关形象思维的思想。朱光潜认为,“维柯的最大功绩在于建立了历史发展观点以及认识来自创造的实践观点。”维柯的这两个基本观点互相联系,成为贯穿《新科学》的两条红线。
“认识真理凭创造”是维柯的一个核心思想,他的这个思想是针对笛卡儿(R.Descartes)唯理主义哲学而提出的。笛卡儿认为,只有理性知识(如几何学的公理)才是最可靠的,而感觉是不可靠的,因此他否认感觉在认识中的作用,把一般原理看成先于具体事实的出发点。笛卡儿指出,认识的出发点必须像几何公理那样清楚明了和确实可靠,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用怀疑的办法来清除一切不可靠的常识和偏见。怀疑一切的结果使笛卡儿发现,只有“我在思想”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我在思想,证明了我的存在,因此笛卡儿将“我思,故我在”(Cogito,ergo sum)视为他的哲学中的“第一原理”。这样,真理便具有了先验的性质。
维柯对笛卡儿的哲学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战。他指出,思维不可能是存在的原因,倒是先有能思维的心灵,然后才有思维:“思维不是我之有心灵的原因,却是它的标记,而标记并不是原因。”在维柯看来,笛卡儿的“我思”只是意识主体,并不能拿来作为真理的标准。与笛卡儿相反,维柯充分肯定感觉在认识过程中的意义,他在《新科学》中引用亚里斯多德的名言:“凡是不先进入感觉的就不能进入理智。”并进一步指出:“人心在从它感觉到的某种事物中见出某种不属于感官的事物,这就是拉丁文动词intelligere(理解)的意义。”针对笛卡儿的观点,维柯提出了相反的口号:“认识真理凭创造”(Verum factum),并认为认识真理和创造是同一回事。
朱光潜对维柯的这一思想作了重要阐发。他认为,在维柯那里,知与行或认识与实践是统一的。“认识到一种真理,其实就是凭人自己去创造出这一真理的实践活动。”例如认识到神实际上就是创造出神,认识到历史实际上即创造出历史。人的认识活动就是一种创造活动,人类的真理就是被这种认识活动创造出来的。这是维柯《新科学》的一条基本原则。朱光潜说维柯的这一原则用现在的话来说,即“认识不仅是来源于实践,认识本身就是创造或构成这种实践活动了。这样,认识并不是让外界事物反映到人心里来,人心本身对认识还起更重要的创造作用,这对流行的‘反映论’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朱光潜全集》书影
在论及维柯可能对中国美学界发生的影响时,朱光潜说:维柯“在一些基本哲学观点上(例如人性论、人道主义以及认识凭创造的实践观点、人类历史由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观点等)”,“都是接近马克思主义的”。这个“问题涉及近年来一直在流行的哲学和文艺方面的‘反映论’,以为哲学思想和文艺创作都应‘如实地反映客观世界’,不应夹带个人主观情感和思想,稍涉主观便成了罪状。我一直坚持的‘主客观统一’,大约在五六十年代之间也一直成为攻击的目标。看轻主观其实就是看轻人,所以人性论和人道主义也就可以构成罪状。自从在维柯的《新科学》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两方面下了一点功夫,我比以前更坚信大吹被动的‘反映论’对哲学和文艺都没有多大好处”。朱光潜还通过自己的“格式塔”(Gestalt,完形)心理体验来说明维柯的这一原理;通过同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J.Piaget)的“发生认识论”原理的对比和与现代结构主义的关系,来证明维柯原理与现代科学发展的契合。朱光潜由此得出结论:“我们的认识,无论是关于宏观世界还是关于微观世界的,任何认识,有哪些能完全不经过维柯所说的构成或创造作用呢?我们的文艺创作有哪些是摄影式的反映而不受作者本人的‘意匠经营’呢?我们都是人而却否定人在创造和改造世界中所起的作用,能说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吗?”
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在今天已成为常识的道理,竟耗费了朱光潜整整后半生的精力。强调审美过程中主体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为艺术把握现实的特殊方式争一席之地,反对美学中“见物不见人”的机械唯物论倾向,是朱光潜后期美学思想中的一个核心主题。他的美在意识形态说、美是一种生产劳动说、美学不只是一种认识论说,乃至美是主客观的统一说,都可视为这个核心主题的逻辑展开。朱光潜晚年高度评价维柯的“认识真理凭创造”的思想,显然是由于维柯的这一思想正好契合了他的“期待视野”(horizon)的缘故。朱光潜对维柯的解读与阐发,一方面反映了他在晚年仍然保持着一种开阔的学术视野和博大开放、善于吸收各种思想的理论襟怀,而且还显示了他对人的主体作用认识的扩展和深化。朱光潜对“人在创造和改造世界中所起的作用”的强调,不仅是对盛行于我国美学界的机械唯物论的有力反拨,而且为中国当代美学研究指示了一个既符合审美客观规律又符合现代学术潮流的正确方向。
2
朱光潜所着力阐发的维柯第二个方面的思想是“人类世界是由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历史发展观点。这是维柯对人类历史的基本看法,也是《新科学》的总纲和主要贡献。
根据“真理与事实互相转化”(Verum et factum Convertuntur)的理论,维柯把人类历史看作是人类用自己的头脑所创造的东西,是人类自己建立起语言、习俗、法律、政府等体系的一个过程,是人类社会和他们的制度发生、发展的历史。维柯最早深入地探讨了区别于自然史的人类史研究的范围、对象和方法,使历史学“第一次达到了一个完全近代的观念”。维柯关于历史研究的方法和原则“在今天的历史学家看来都是些平淡无奇的东西,但在他当时,它们却是革命性的”(R·G·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
维柯明确指出:“人类世界是由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新科学》主要就是探讨人类创造和发展各种社会制度(institution)的历史过程。当时的理性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各种制度都是由“人”创造出来的,在他们眼里,这种“人”已具有充分发展的人性,所以这种“人”能够制定各种制度。而维柯则持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人性”和“人道”都是人类在创造自己的世界和建造各种制度的过程中发展出来的,它们不过是制度创建的“产品”和“结果”。维柯甚至认为,不仅在心灵和精神方面,即使是人类的身体,也是人类自己创造的,人类在创造自己的世界的过程中将自己由野兽变成了人。因此维柯坚决主张:“研究应从问题的开始时开始”,并将这一原则当作《新科学》的方法论前提。以往法学家研究罗马法是从人性已充分发展的近代人开始,这在维柯看来就是根本违反了历史发展的观点。从这个观点出发,维柯把荷马史诗看作人类原始民族的历史,将它作为人类历史的起点来考察,并从中揭示出人类最初的经济、政治、伦理、法律等制度以及哲学和自然科学的思想。
维柯认为,历史发展有其自身的必然性和规律性,“诸民族的全部变化多端,纷纭万象的习俗显出经常的一致性”。他接受古埃及人的方法,将人类历史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神的时代、英雄的时代、人的时代。随着岁月的推移和人类心智的发展,神的时代被英雄的时代所取代,然后人的时代又取代了英雄时代,维柯将人的时代看作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高峰。人类历史发展到人的时代,就又要回到神的时代,接着按原有的次序将三个时代重演。维柯描述的这种人类历史的周期性运动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循环,它不是一个圆而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向上的螺旋,这与古希腊、罗马的历史观念是根本不同的(参见R.G.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维柯的这一思想后来成为黑格尔历史观的先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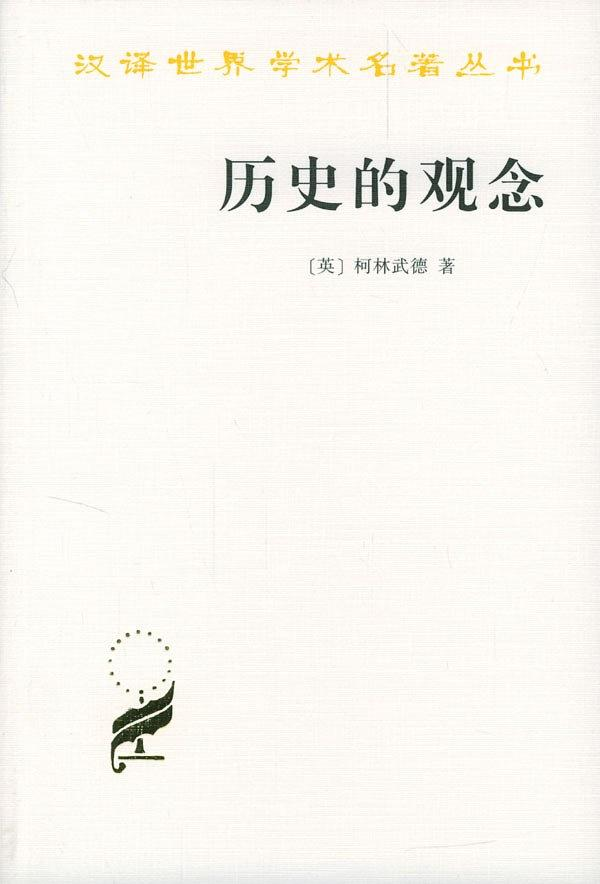
《历史的观念》书影
朱光潜高度评价维柯的历史发展观,并着重强调了它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影响。马克思十分赞赏维柯关于人类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的观点,他在《资本论》第一卷的一条注中说:“如维柯所说的那样,人类史同自然史的区别在于,人类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而自然史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朱光潜说,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与雾月十八日政变》里一开始就明确指出:“人类历史是由人类自己创造的。”这正是维柯对历史的基本看法。马克思所创立的唯物史观作为一种理论形态,是人类认识史的结晶,它既是马克思对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十九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综合性批判、吸收、改造的结果,也吸收了维柯思想的有关成果。朱光潜认为,维柯比费尔巴哈早半个世纪就已认识到神是原始酋长的本质的异化,“维柯在历史发展这个基本观点方面比费尔巴哈更重要”。
3
朱光潜从五六十年代起直到晚年,始终致力于研究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实践观点,特别强调美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因此,他对维柯的历史发展观表现出了极大关注。从这个角度来看,朱光潜结合维柯的“诗性智慧”(Poetic Wisdom)对形象思维理论所作的阐发,实际上可视为维柯的历史发展观在具体美学问题研究中的贯彻。
朱光潜认为:“《新科学》是近代对美学或诗论作出贡献最大的一部著作。”这与克罗齐的看法倒是一致的。维柯的《新科学》对人类历史的探讨是从荷马史诗开始的,而“诗”在古希腊文中的字义就是“创作”、“创造”。原始人类就像人类的儿童,他们凭感官了解外界事物,他们健壮而无知,没有任何概念、理念的束缚,他们凭“一种完全肉体方面的想象力”(参见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以一种惊人的崇高气魄去创造他们自己的历史。这种凭感觉和想象去创造的原始人类的智慧就是“诗性智慧”。古代神话展示了早期人类对周围世界的认识和反应,神话即诗,诗即神话,两者都是“诗性智慧”所创造的“诗性历史”。由此维柯认为,荷马史诗实际上是早期人类的集体创造,是早期人类对现实世界的一种诗性叙述和诗性解释。诗性智慧的发现,使《新科学》成为一部气势恢宏的人类思想、习俗及一切文物制度的创造史。

晚年朱光潜
在朱光潜看来,维柯在《新科学》中化大量篇幅论述的“诗性智慧”,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形象思维”。他指出,维柯所发现的诗性智慧的三条规律也就是形象思维的三条规律,对美学有重要意义。
形象思维第一条最基本的规律是抽象思维必须以形象思维为基础,在发展次第上后于形象思维。维柯说:“人最初只有感受而无知觉,接着用一种惊恐不安的心灵去知觉,最后才用清晰的理智去思索。”朱光潜阐释说:原始人类认识世界只凭感觉的形象思维,他们的全部文化(包括宗教、神话、语文和政法制度)都来自形象思维,都有想象虚构的性质,即都是诗性的、创造性的。人类由儿童期发展到成年期,即从神的时代、英雄的时代发展到人的时代、哲学的时代,他们才逐渐能运用理智,从殊相中抽出共相。可见,人类心理有一个从形象思维逐渐发展到抽象思维的过程。
形象思维的第二条规律是以己度物的隐喻(metaphor)。维柯说:“人们在认识不到产生事物的自然原因,而且也不能拿同类事物进行类比来说明这些原因时,人们就把自己的本性移加到那些事物上去,例如俗话说:‘磁石爱铁’。”“诗的最崇高的工作就是赋予感觉和情欲于本无感觉的事物。儿童的特点就在把无生命的事物拿到手里,戏和它们交谈,仿佛它们就是些有生命的人。”这也就是说,原始人类“把自己当作衡量宇宙的标准”。如原始人用“首”来指“顶”或“初”;用“眼”指放进阳光的“窗孔”;用“心”指“中央”;针“眼”、杯“唇”、锯“齿”、麦“须”、海“角”;说天或海“微笑”,风“吹”浪“打”,受重压的物体“呻吟”……维柯认为这种以己度物的隐喻也就是语文的起源。朱光潜指出,这种事例在中国语文中也俯拾即是,这就是后来德国美学家的“移情说”的萌芽,和中国诗论中的“比”、“兴”也可互相印证。
形象思维的第三条规律是以想象的类概念(imaginary class-concepts)来把握同类事物的共同属性。维柯说:人类心灵有一个特点,即“人对辽远的未知的事物,都根据已熟悉的近在手边的事物去进行判断”。他又说:“儿童们的自然本性就是这样:凡是碰到与他们最早认识到的一批男人、女人或事物有些类似或关系的男人、女人和事物,就会依最早的印象来认识他们,依最早的名称来称呼他们。”因此当原始民族还不能凭理智来形成抽象的类概念(如勇敢、聪明、谨慎、灵巧)时,他们就只能凭个别具体人物来形成想象的类概念,以此来把握诸如“勇敢”、“聪明”这样一些抽象的类概念。如希腊人把一切勇士都称为阿喀琉斯(Achilles),把一切谋士都称为尤里西斯(Ulysses),中国人把一切巧匠都叫做鲁班,一切神医都叫做华佗。根据神话、寓言故事是原始民族“想象的类概念”的创造这一原则,维柯断定荷马不是一个具体的古代诗人,而是在传说中由原始民族共同想象出的诗人,《荷马史诗》是古代希腊全民族共同创造的成果。这就是维柯所发现的“真正的荷马”。朱光潜指出,维柯发现的这一条规律与我们现在常谈的“典型人物性格”有很大关系。
诗性智慧以具体形象代替抽象概念的特点及其创造性想象的本质,加深了朱光潜对形象思维特点及其本质规律的理解;维柯考察诗性智慧历史发展的观点和方法,也在方法论上给朱光潜以启示。如果说,以往美学家对形象思维的研究都是从认识论角度所作的一种共时性研究,即它普遍地被当作脱离了原始阶段的人的一种艺术思维形式来探讨,那么,朱光潜则在维柯的启发下,主张对形象思维进行一种历时性研究,即将其置于自身的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来研究。这种用历史发展观所作的研究,将大大拓展形象思维理论的空间,使形象思维理论获得一种超越个人、时代的普遍性和历史性。马克思指出:“不管是人们的‘内在本性’,或者是人们的对这种本性的‘意识’,即他们的‘理性’,向来都是历史的产物。”如果我们不是将形象思维问题放到特定的历史阶段去进行考察,那么我们对于人类各个历史阶段上的精神活动的特点(如形象思维及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的关系),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物质生产水平和社会生活之间的相互作用,便决无理解之可能。在此意义上,维柯关于诗性智慧的思想以及朱光潜要求将形象思维研究延伸到人类文明源头的看法,都起了一种理论先导的作用。
4
毋庸讳言,朱光潜对维柯思想的阐发也存在着一些尚可商榷之处。
首先,从维柯的整个思想体系来看,他的历史观并没有超出历史唯心主义的范围。朱光潜六十年代在《西方美学史》中认为“维柯的历史观还是唯心主义的。他的基本出发点是共同人性论。”到80年代,朱光潜觉得自己以前低估了维柯:“垂暮之年翻阅旧作,深愧把维柯也看成和克罗齐一样是位唯心主义者,有负于《新科学》这样划时代的著作,因此下定决心把它译成中文。”那么,其前后两种看法哪种更接近维柯思想的真实呢?笔者认为,朱光潜六十年代对维柯思想所作的总的评价是比较正确的。
从人类认识史来看,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对社会的认识,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从神到人的过程。用超自然的意志和力量来说明历史发展和社会生活的神学历史观,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处于支配的地位,神和天意是人们回答历史之谜的总答案。到文艺复兴时期,人道主义思潮的崛起,标志着从神到人的转折。人道主义思想家将人与神对立起来,以人为中心,倡导一种以人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历史观,从人本身探究人类历史和社会制度的根据,把天国的历史变成世俗的历史。但是,由于他们用抽象的人性作为解释人类社会一切现象的最终根据,因此并没有为历史提供真正科学的答案。维柯把历史看成是一个有规律的发展变化过程,他不是在人性中,而是在人性之外,到原始社会各种社会制度的起源和发展演变中去寻找这个规律,因此他的思想中确有不少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这是他超出人道主义思想家的地方。但是,维柯最终还是把人性看作是人类历史发生和发展的本源。在他看来,各民族所经历的历史过程都要经过神、英雄和人三个不同的时代。这三个时代都起源于各自不同的“自然本性”:第一种诗想象,这是一种诗性的或创造性的自然本性;第二种是优于其他物种的属人的高贵性;第三种是理智、良心、责任感。维柯所说的“自然本性”都是精神性的、抽象的。他认为,人类社会的习俗、部落自然法、民事政权或政体,都是从这“自然本性”依次派生出来的。不仅如此,维柯还将人类历史看作是建构人性的过程,把人性看作是衡量历史的尺度。因此,总体而言,维柯并未跳出抽象人性论的圈子。
与此相反,唯物史观则认为,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马克思说:“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仍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不过尽管如此,维柯关于历史规律性的观念对于黑格尔历史观的积极影响,他的关于“人类世界是由人类自己创造的”思想和历史发展观对马克思的积极影响,都是不能低估的。
朱光潜晚年对维柯思想哲学倾向的认识偏差,与他对维柯《新科学》中两个基本命题的理解有直接关系。第一、朱光潜认为维柯的“认识真理凭创造”命题中的“创造”就是“实践”:“认识到一种真理,其实就是凭人自己创造出这一真理的实践活动。”他认为维柯的这一命题用现在的话来说,“认识本身就是……实践活动了。”维柯所说的“创造”是否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实践”呢?不是。其实,维柯的“创造”仍是一种认识活动,在维柯那里,人类认识真理的过程和创造世界的过程是统一的。他说:“这种情形正像几何学的情形。几何学在用它的要素构成一种量的世界,或思索那个量的世界时,它就是在为它自己创造出那个量的世界。我们的新科学也是如此(它替自己创造出民族世界),但是却比几何学更为真实,……认识和创造就同是一回事。”在维柯看来,人类世界是由人类自己创造的,人类各种制度都是人类心智创造的结果,所以人类世界的原理、原因和基本面貌必然“从我们自己的人类心灵各种变化中就可找到”。因此,朱光潜在《新科学》中译本第365页“中译注”中说,“认识事物就是创造事物,这是维柯的主要信条”,这个概括是符合维柯思想实际的,但说由此“可以得出万物唯心的结论,也可以得出认识来源于实践的结论”,却并不妥当了。这里关键在于没有划清认识与实践的界限,将认识过程中认识主体的能动作用与实践活动中实践主体的能动作用混淆了起来。马克思所说的“实践”首先是人类改造客观外部世界的感性活动,是一个真正的本体论意义上的概念。而“认识”作为一个认识论的概念,指的只是一种精神的活动。虽然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和发展的基础,也是检验认识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但实践并不等于认识。在马克思批判地改造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理论,提出实践概念之前,哲学家对人的有目的的活动的解释,以及对人类社会和历史的认识,都只停留在人的主观动机之内,即停留在精神活动的范围之内。维柯也没有例外。
第二、与上述问题相联系,朱光潜把维柯的“人类世界是由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这个命题,等同于马克思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在这里,朱光潜正确地看到了两个命题在思想上的承继关系和一致性,但忽视了两者的根本区别。马克思认为物质生产劳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劳动创造了人类世界,而不是人的认识活动创造了人类世界。朱光潜忽视了这一点,其根源仍在于没有划清认识与实践的根本界限。
朱光潜在解读维柯时出现的失误,反映了他美学思想中深层次的矛盾。他一方面将美的主客观统一说放到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的基础上加以论证,肯定美与美感的客观现实基础:“美是人在生产实践过程中既改变世界又从而改变自己的一种结果”,“美感起于劳动生产中的喜悦,起于人从自己的产品中看出自己的‘本质力量’的那种喜悦”;另一方面又时时游离于这一理论立场,将认识与实践混淆起来,从而使美与美感的客观现实基础受到某种程度的消解。他一方面强调历史发展观点,将美、美感及艺术问题放到人类在劳动生产中改造自然同时也改造自己的历史过程中来加以认识,从而使主客观统一说具有历史发展的形式;另一方面又时不时将这种历史发展过程蜕变为认识、思想和观念的发展过程,从而使历史发展观失去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他一方面强调人的整体观点,主张美学研究与人的研究的统一;另一方面又在某种程度上割裂了人的物质生产活动与人的精神活动。朱光潜身上的这种两面性使他陷入了矛盾,但也正是这种矛盾使他的美学思想即使到晚年仍具有一种诱人的丰富性和开放性,呈现出跳荡的生命活力。这恰恰是那种看去似乎无懈可击、自圆其说的“体系”所不能及的。自圆其说、无懈可击,也许会让他的思想固定为一派而一家独尊,然而这种种矛盾倒使得他的美学成为一个永远向着未来开放的理论空间。
朱光潜的美学生涯起始于克罗齐而终结于维柯,朱光潜一生与意大利这两位思想家结下不解之缘。朱光潜从克罗齐经由马克思而到达维柯,昭示了他一生美学思想的发展历程,即从哲学-心理学取向转向历史-哲学取向。朱光潜晚年力图以马克思唯物史观为基础来整合其美学思想,其美学思想的重心已经靠近马克思。但是,克罗齐与维柯在其思想中已留下了深深的痕迹,其中克罗齐从反面使他走近马克思,而维柯则从正面使他加深了对马克思的理解。朱光潜对马克思的理解中有克罗齐与维柯的影子。无疑,克罗齐、维柯和马克思,是对朱光潜一生影响最大的三位西方思想家。
参考文献
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朱光潜:《朱光潜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维柯:《选集》,剑桥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王水照编:《历代文话》,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R·G·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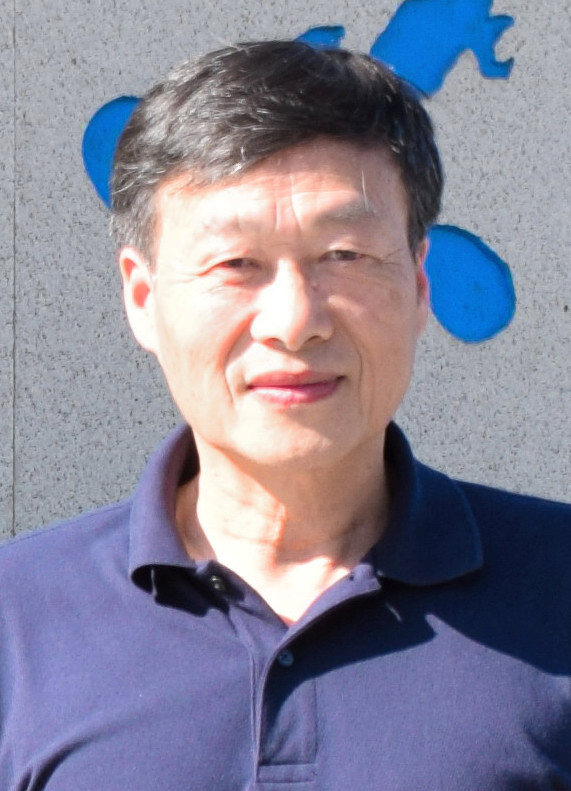
【作者简介】
蒯大申,1953年生于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副所长、研究员。
主编:朱生坚
编辑:张晴柔
运维:任洁
制作:蓝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