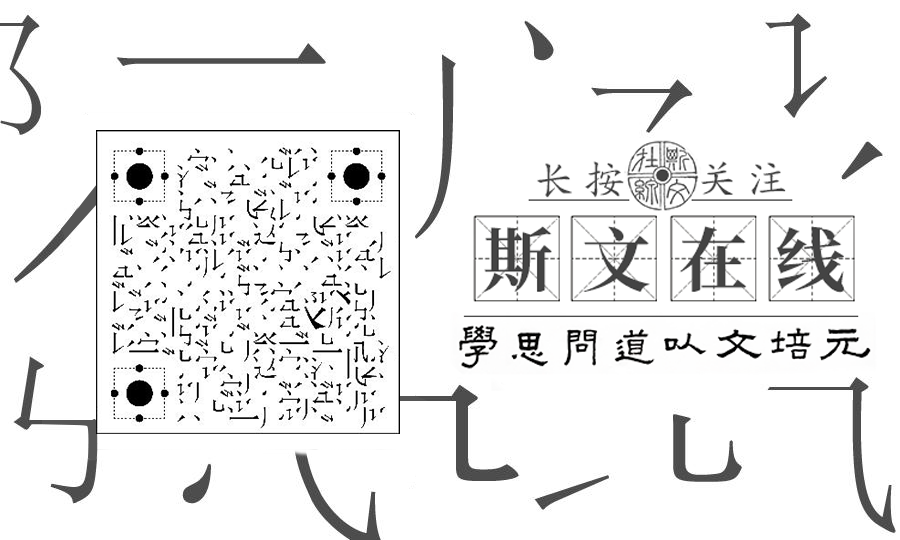在新冠病毒面前,人类一败涂地,付出惨重代价之后,终于换来一点喘息的机会。这时候,既需要真正的专家、实干家来扭转局面,也同样迫切地需要一些思想者“不轻言问题的解决法,而深刻用心于问题的认识”(梁漱溟)。孙周兴教授所做的是后一种工作。他提出了很多问题,不是急于解决这些问题,而是致力于问题的认识,并且衍生出更多的问题。人虽然脆弱,却是会思想的芦苇。更何况,人还有爱。在吸取教训、敬畏自然的同时,我们分明听到,本文结尾提到的那一对不管是真实的还是虚拟的意大利恋人,代表人类发出的宣言:来吧!病毒和死亡,你们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技术终究是靠不住的,“爱才是人类唯一的救赎”(史铁生)。
最近一些年来,随着以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为代表的现代新技术的加速发展,人群中技术乐观主义者趋多,人们信心满满,开始憧憬未来技术世界的新生命形态和新生活方式。要不是如今这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疫情,人们大概还会继续沉湎于新技术的狂想和狂欢中,渐渐忘掉了生命本体,忘掉了自然生命的脆弱和肉体的速朽。从2020年1月初新冠疫情从武汉开始的几十例,到今天(2020年3月31日)的全球逾85万例确诊患者,只花了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全人类已进入普遍的恐慌之中,超过70个国家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而这场全球危机的结局如何,何时结束,目前都还说上不来。之所以说不上来,是因为这种被称为COVID-19的冠状病毒十分怪异,神出鬼没,关于它的来龙去脉,我们还有太多未知。古往今来,人类最大的恐惧就来自未知和不可见,根本上是对未知之物和不可见之物的恐惧。人类在看不见的神秘病毒面前依然束手无策,只能在恐慌中躲藏和封闭。但无论如何,这场关乎人类生存的巨大危机已经迫使我们来思考这个技术时代的人类生活及其危机的来龙去脉。
本文尝试从技术哲学角度来讨论新冠疫情危机,这就是说,本文试图撇开政治意识形态、伦理和社会治理等多样的视角和复杂因素,只把着眼点设定在技术与生命/生活这个核心问题上面——当然不是说其他视角和因素不重要,而是说本文暂时只能采取一个作者假定为重要的视角。由此技术哲学的视角,本文试图提出和讨论如下几个问题:(1)面对这次世纪大瘟疫,人类进步了吗?(2)为什么每一次病毒来袭,人类都只能缩回到自然状态?为什么现代人也难逃此劫?病毒到底意味着什么?(3)人类通过技术最终能够战胜病毒吗?除了技术,我们现代人今天还能指望什么?技术乐观主义是唯一出路吗?(4)疫情改变了什么?疫情是技术世界的减速器还是加速器?在疫情中以及在可以期待的后疫情时代,个体如何自卫和自处?我们需要建立什么样的新生命经验?这些问题都相当宏大和复杂,我这里未必都能展开,只是尝试提出问题。
一、面对这次世纪大瘟疫,
人类进步了吗?
病毒与人类历史相伴而来,在人类文明史上时隐时显,但从未真正缺席过。赫拉利在《未来简史》开篇就给出一个断言:人类自古至今都面临三大问题,即饥荒、瘟疫和战争,而在第三个千年开始时,人类突然意识到在过去几十年间,我们已经成功地遏制了饥荒、瘟疫和战争。估计他自己也觉得这个判断太硬了,赶紧补充了一句:虽然这些问题还算不上完全解决,但它们已经从不可理解、无法控制的自然力量转化为可应对的挑战了。[2]赫拉利的这个断言,无疑是一个“技术乐观主义”的判断。
如果单从历史事实和数据来看,赫拉利的判断似乎不无道理。人类史上最大的一次瘟疫是14世纪的黑死病(鼠疫),通过老鼠和跳蚤传播,主要范围在欧亚大陆,致死人数达7500万至2亿人,全球约1/4的人口消失。紧接着来了一场规模更大、延续时间也更久的流行病,就是梅毒病(Syphilis)。梅毒因为致死率不高或者说是让患者缓慢致死的,所以较少被人记得和强调。15世纪末意大利人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固然是伟大的历史事件,但经常不被人提起的是,航海活动同时把梅毒这种性病带回了欧洲,成为欧洲近代长达400年不治的大流行病,直到1945年青霉素问世。因梅毒病致死的人数恐怕不会比黑死病少,一批欧洲名人如贝多芬、舒伯特、莫泊桑、波德莱尔、梵高、尼采、王尔德、乔伊斯等死于此病——当然也有人说,梅毒造就了一批欧洲天才,此说在此姑且不论。[3]
20世纪人类最大的流行病,当数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和1981年开始的“艾滋病”(AIDS)。“西班牙流感”始于1918年1月的欧洲战场,不到一年时间里使全球5000万至1亿人丧命(当时人类总人口约15亿),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亡人数。至20世纪后半叶,在梅毒病渐渐消失之后,1981年下半年又出现了一种性病即艾滋病,是一种由攻击人体免疫系统的病毒(HIV病毒)引发的恶性流行病,至今致死人数有2500万之多(一说已超过3000万人),尚有感染者超过3300万人。

“西班牙流感”始于1918年1月的欧洲战场,不到一年时间里使全球5000万至1亿人丧命(当时人类总人口约15亿),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亡人数。
那么问题是:还会有大规模的严重流行病吗?赫拉利说,过去几十年间流行病在流行程度和影响方面都大大降低了。这是因为20世纪医学的高度发达,比如艾滋病,虽然现在也还没有根除之药,但新研发的药物已经让它变成了一种慢性病。进入21世纪以后,短短20年间,人类一共碰到5次重大疫情:(1)2002—2003年的“非典型肺炎”(SARS);(2)2005年的禽流感;(3)2009—2010年的猪流感;(4)2014年的埃博拉病毒;(5)2020年初的新冠病毒。不过,21世纪的前4次流行病最终都没有造成大规模的全球大疫情,如“非典”死亡人数不到1000人,而死状特别恐怖的埃博拉病毒一共感染了3万人,致死1.1万人。这当然无法跟20世纪的“西班牙流感”和“艾滋病”相比了。赫拉利认为,这是由于人类采取了“有效的应对措施”。[4]
然而,病毒(或疫情)又来了。这一次来势凶猛,仅就现阶段看,其规模和毒性都已经超过21世纪出现的前4次大流行病。至本文写作时(2020年3月31日),据网上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人数为82615人,累计死亡3314人;国外累计确诊776729人(已经是中国的9倍多),累计死亡38818人(已经是中国的近12倍)。[5]这个数字已经十分吓人了。全球民众进入恐慌时刻。
现在看来,这个“新冠病毒”仿佛是一种综合病毒,它在机理上是“非典”的加强版,又似乎与“艾滋病”难脱干系,在强传染性上又与“西班牙流感”可有一比,据说致死率不算高,中国约为4%,但意大利目前的数据是大于8%。最可怕的是它的隐蔽性,最新研究表明,30%—60%的新冠病毒感染者无症状或者症状轻微,但他们传播病毒的能力并不低,这些隐性感染者可能会引发新一轮的疫情大爆发。[6]这就让人防不胜防,有可能使目前全球各国普遍采取的隔离措施失效。
新冠病毒的神秘性还表现在,尽管全球科学家们做了几个月的努力,但它的来源依然是一个谜,关于“零号病人”和“中间宿主”等相关问题,全球已经展开了专业的和非专业的激烈争论,也还没有可靠的结论。一般研究者都同意该病毒来自蝙蝠,但病毒从蝙蝠向人传播需要有所谓的“中间宿主”,正如我们把前一次SARS病毒归咎于果子狸,这一次科学家们说是穿山甲,但也有人说不是,又说有人造的可能性。可供利用的动物越来越少了,如果还有下一次,我们怪谁呢?
最近,这病毒的起源问题甚至成了中美两个大国争论的焦点。新冠病毒目前最早发现于湖北武汉,但因为存在着一些国家(不仅是美国)研发生化武器的可能性以及各国病毒实验室(所谓P4实验室)的存在,致使各种人工起源的猜测(所谓“阴谋论”)此起彼伏,给出了各种有依据的和无依据的构想空间。可以想象,由于政治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之争,新冠病毒的起源问题最终也许会不了了之,成为一个永恒的谜团。[7]

美国国家过敏症与传染病研究所(NIAID)所长安东尼·福奇博士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言时无奈扶额,一度成为网络表情包爆款
虽然有些国家声称已经研发了疫苗,试验了各种药物,但到目前为止依然没有被普遍接受的技术手段和特效药,赫拉利所谓的“有效的应对措施”至今没有出现。目前在制度性的整体动员之下,中国的疫情看起来已经得到了控制,本土新发病患者已经多日清零,但近期欧洲和美洲告急,特别是欧洲的意大利和西班牙,正在重演武汉市封城后几个星期内发生的崩溃状态,前些天传来的一个悲惨消息是意大利50名神父因频繁探视新冠病人而不幸染病去世;而美国则已经迅速上升为确诊人数全球第一名(新冠病毒感染者,而非新冠肺炎患者)。如果全球疫情下一波高峰推向印度和非洲大陆,后果不堪设想。
一场全球大疫已经到来,有人称其为“第三次世界大战”。无论“战后/疫后”后果如何,我们眼下已经能体会到的恐怕首先是技术的限度与生命的脆弱。眼见技术时代生命的败局,我们不得不感叹:物质依然神秘,而生命依然孱弱。
二、为什么每一次病毒来袭,
人类都只能缩回到自然状态?
面对这场21世纪最大的新疫情,面对这个未知的、神秘的、狡滑多变的病毒,拥有高度发达技术的人类只好采用最笨拙、最原始的办法:隔离和封闭。技术多半成了完成这种围城式禁锢的辅助手段。这真的让人灰心和气馁。而中国之所以取得目前暂时的成功,原因主要也不在于技术,而首先在于全国人民自觉而规矩地进行居家隔离。疫情中心武汉被前所未有地封城,而中国其他城市也相继采取措施,每个人都被禁锢于大大小小的住宅里。甚至有人认为,儒家文化传统在这个时候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人和东亚人是善于自我隔离的。数据显示,东亚三大国,中国、日本、韩国,目前确实都比较好地控制了疫情。
我们要追问的是:为什么每一次病毒来袭,人类都只能缩回到自然状态?我们这一代中国人进入21世纪后就经历了两次冠状病毒:2003年的SARS和2020年的新冠病毒。两次的情形差不多,我们能采取的办法也一样,都是没办法的办法。所谓的“抗疫”,根本上就是隔离和封闭。居民们在家里隔离(与外界隔离),偶尔出门用口罩隔离(与他人隔离);医护人员穿戴全套的防护设备(与病人隔离)。今天全球抗疫的形势也一样,哪里隔离得好,哪里就成功些。没有人会想到,这个看不见的病毒竟然有如此强大的力量,能把全球人类都隔离起来了,让喧嚣的城市变成一片寂静,让野猪在城市高架路上奔跑。

武汉封城第一周,有网友拍摄到一头在高架上奔跑的野猪
疫情下的城市生活可以称为“城市自然状态”。我这个说法听起来不免滑稽。现代城市是技术工业的产物,是一个“普遍交往”(马克思语)的多功能体系,一个不让人“外出”的城市是一个与城市本质逆反的空间,其实就不能叫“城市”了。但现在一切都停摆了,许多社交方式都被取消了,所有体验式的行业都关停了,只剩下了手机微信和快递业务。多亏了微信技术,让我们感觉到自己还在一个有人的世界里生活,也多亏了快递,让隔离的我们还能与外界有物质交流。
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被认为早已脱离了自然状态,然而为什么在病毒面前,我们现代人仍旧难逃此劫,依然只能通过隔离缩回到自然状态?答案当然很简单:时至今日,人类仍旧抵抗不了病毒,所以只好逃避。但病毒到底是什么?这种人类至今依然无法抵抗的病毒到底意味着什么?
“病毒”一词源自拉丁文的virus,原意为“粘液、动物精液;毒物、毒药;臭味、恶臭”。我不知道是谁把virus翻译成“病毒”这样一个阴森可怕的词语。必须承认,这显然是一个人类中心论的译法。如果我们同意病毒是细胞的祖先,我们好像还没有理由用“病”和“毒”两个贬义汉字的组合来表达virus。我想,只是因为对人类生命体来说,病毒是阴损的,许多时候有害的,甚至是毁灭性的,我们才会有此译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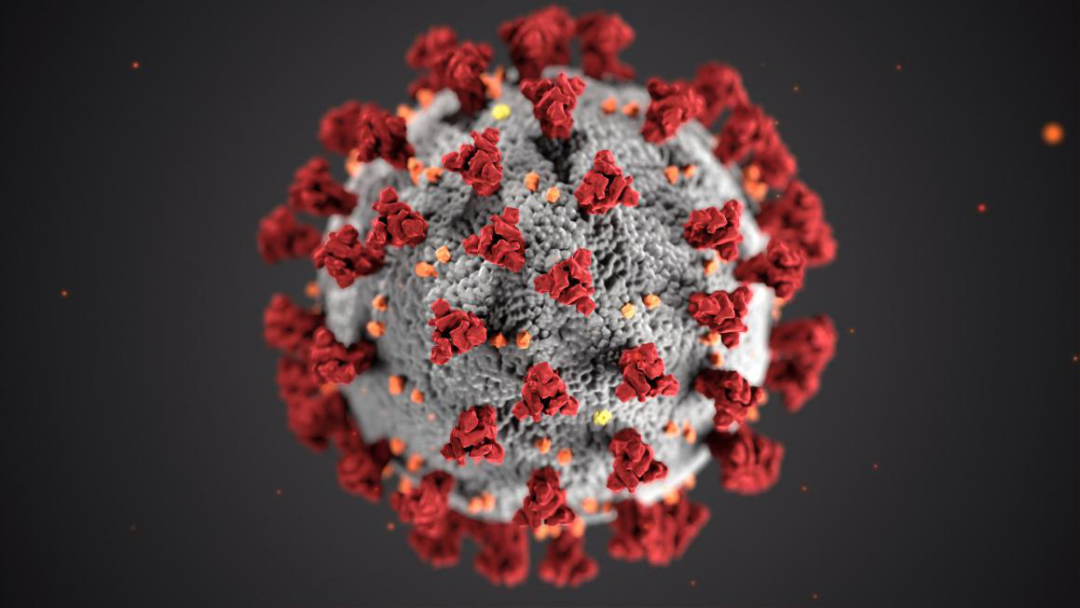
COVID-19(新型冠状病毒)病毒模型
从物质形态上说,病毒是介于非生物与生物之间的存在物,可以说是从非生命物质到生命、从非生物到生物的“过渡”形态。这也就是说,病毒具有“双栖”即非生物与生物的双重属性,它一方面具有化学大分子的结晶功能,另一方面又具有生物自我复制的繁殖特征(它必须进入宿主细胞里才能进行复制和转录)。这样一种“双栖”特性使病毒变得难以认识和掌握。迄今为止,人类还没有弄清楚病毒的起源,比如到底是细胞来自病毒还是病毒来自细胞,都还是不断争议中的课题。从生物进化序列来看,病毒为细胞的祖先的假设更为合理,正如意大利分子遗传学家卢里亚(Salvador Edward Luria)所说的,病毒是在细胞出现前生命“原始汤”中的遗骸。
从生命存在论或物质存在论的意义上,介于生物与非生物之间的病毒实际上可视为生命的边界和底限,是生命起源和存在之谜。近代以来,人类(欧洲人)通过物理学和化学“征服”了非生物世界,又试图通过生物学和生物技术“征服”生物世界。在技术工业的强力协助和支配下,人类通过化工、医药和农药工业彻底败坏了生命环境,加上暴力猎杀,地球上的物种不断灭绝——前述的被认为是冠状病毒的宿主的果子狸和穿山甲都已经是濒危动物。进入21世纪以来,基因工程加速发展起来,开始了对生命本体的技术化加工和改造,比如这次病毒被怀疑为人工病毒,不是完全没有依据的,因为人类已经具有通过基因编辑来人工合成和重组病毒的能力,而且已经有了实体试验。这就是说,病毒不仅是自然风险,也完全可能是生物技术带来的人工风险。无论如何,这就再次为今天快速发展的生物技术特别是基因工程研究敲响了警钟。[8]
值得注意的是,中外研究者的相关研究表明,男性的肾脏和睾丸是新冠病毒的潜在攻击对象,即新冠病毒会攻击男性生精细胞,从而抵制男性生殖功能。[9]这就不禁让人联想到另一个既有事实:在环境激素的影响下,地球上的雄性动物的生殖能力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已经大幅下降,尤其是发达工业国家的不孕不育比例大幅提高。如果按照有的科学家的预测,这次疫情真的将有60%的人被感染,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认为,这次新冠病毒的攻击也许是对自然人类的最后一击——这难道是人类的“宿命”么?
新冠病毒以其怪异特性(综合性、高传染性、隐蔽性、变异性等)显示出自然生命原体的阴森可怕,它造成的后果尚不得而知。但今天不得不缩回到自然状态的人类恐怕真的要想一想:病毒到底是什么,意味着什么?病毒是不是构成了不断被侵犯的自然生命的一种报复和抵抗?为什么人类进入21世纪,病毒出现的频率却越来越高了?然后我们才能更进一步来思考:如何应对这种报复和抵抗?
三、除了技术,
现代人还能指望和信赖什么?
如果我们把工业革命以来的技术称为现代技术,以区别于古代技术,那么现代技术迄今为止也就延续和进展了两个半世纪而已。以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标志,现代技术被确认为一种全球统治力量。有地质学家甚至想把1945年设为一个地质年代的分界线,即“第四纪”“全新世”的结束和“人类世”(anthropocece)的开始。也有敏感的哲学家如斯蒂格勒、斯罗特戴克等,接过了“人类世”这个名称,开展技术文明的哲学思考。不论是否接受“人类世”之说,我们如今不得不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确实具有转折性的意义,因为自那以后,技术工业进入“下半场”,而且进入了加速状态。尤其是进入21世纪,两大新技术领域即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成为突飞猛进的热门新技术,人类生活被带入加速轨道,虽然喜忧交加,但总体上是“技术乐观主义”占了上风,生活世界日益被科幻化。
技术——我特指“现代技术”——当然为人类带来了许多福祉,我们前面引述过的赫拉利的基本观点是可以成立的。更少战争、饥饿和瘟疫,更文明、更卫生的生活,更好的医疗条件,差不多翻了一倍的人类寿命,更规则、更自由的制度体系,更多的国际交流和人际交往,这些无疑都是现代技术带来的“好处”。就此而言,一味地咒骂技术工业,显然属于昧着良心说话了——可惜长期以来,人文学者多半有此爱好,就是一边享受现代技术,一边指控和诅咒技术,有的甚至叫嚷着要回到农耕自然文明。
但另一方面,我们确实也不得不承认,技术是一把“双刃剑”,用斯蒂格勒的话来说,它既是“解药”又是“毒药”。我们已经不用细细列述现代技术带来的风险和危机,只需指出,数学、物理、化学和生物学,这四门基础科学最终都形成了重大技术风险,即以数学为基础的人工智能,由物理带来的核武器、核能,由化学工业造成的生态环境危机,以及由生物学形成的基因工程,其中每一项所隐含的“危险”对今日人类来说都是致命的。技术乐观主义放弃了这方面的考量和评估,而只是守住了技术进步增进人类福祉的假象。
现代医疗观念在根本上也是一种技术乐观主义,或者说是以后者为基础的。人类已经进入这样一个生命阶段:人们对医术、药物和医院的相信和依赖胜过了对自己身体的信念。现代人成了不相信自己身体的一群人,我们已经把“命”交给了医疗和药物。
在这次抗疫过程中,跟往常一样,一批医生成了明星。我们还记得,是钟南山院士首先于2020年1月20日宣告新冠病毒“人传人”,李兰娟院士建议国家在1月23日对武汉实施封城,2月7日一个武汉的普通医生李文亮之死让全国人民愤怒又心碎,性格直率的上海医生张文宏教授成了全国人民追捧的好专家和导师,等等。人们相信医生们。同样,人们期待有效药物的出现,当美国吉德利公司开发的抗病毒药物瑞德西韦(Remdesivir)送到中国武汉临床试验时,人们把它称为“人民的希望”。在医生和科研人员的推荐下,中成药双黄连口服液被认为可抑制新冠病毒,于是一夜之间,双黄连在祖国大地上脱销。有几百种药物问世或被问世,我们可以把这种情况理解为病急乱投医,但其中也掺杂了不少商业动机。

跟风抢购双黄连的人连兽药都不放过,引发网友群嘲
事实是,到目前为止,世上还没有出现用于预防和治疗新冠病毒的有效药物。[10]全球已经开始了疫苗研发竞赛。截至2020年3月19日,世界卫生组织(WHO)称已经有41家公司及机构在从事新冠病毒疫苗开发,而中美两国都已经宣布了新冠病毒疫苗的进展,中国新冠疫苗已开始人体注射实验,美国也公布疫苗进入临床试验阶段。但要进入实际应用阶段,恐怕尚需时日,据中国方面的说法,最快到年底才能上市。必须认识到,疫苗是预防传染病的自动免疫制剂,所以也不是有效的治疗手段,而是终极的“隔离”办法。这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生物技术和医学技术对这个新冠病毒无能为力,既没有特效药物也没有疫苗,所谓治疗只是通过技术和药物让患者提高自身免疫力。
既然如此,我们对这个医疗技术体系的信赖还能成立吗?只不过,对于技术时代的现代人来说,我这个问题差不多已经是一个假问题了。我们甚至不该怀疑技术最后能克敌制胜。因为如果我们不相信技术,不相信技术专家和技术工业生产的药物,那么我们能相信什么?一句话,除了技术,今天我们还能指望和信赖什么呢?
这就是技术统治时代——所谓“人类世”——人类的命运了:人类已经从自然状态进入技术状态,或者说,自然人类文明体系已经开始并正在加速切换为技术人类文明体系,自然人类的“上帝崇拜”已然转向了技术人类的“技术崇拜”。哪怕新冠病毒的打击使我们退缩,迫使我们重新归于一种自然状态,进入一种“假性的”自然状态,我们也还只能抱一种“技术乐观主义”的态度,我们似乎只好相信:这个看不见的病毒的克星正在路上,即使暂时还没有克星,也终归会有最终有效的隔离手段(比如疫苗或者治疗性抗体)使我们免疫,使我们活下来。
看起来,舍此我们便无以安心和安身了。
“四、世界将何去何从?
疫情是技术世界的减速器还是加速器?
新冠疫情之下,我们每个个体都经历了或正在经历忧虑和恐惧。此时此刻,已是深夜,有人正在死去,化作明天早晨全球疫情死亡人数统计表上的一个无名的数字。未被感染者还是大多数。但未被感染者也在恐惧中,在各种担心中。各种预测纷至沓来,比如有美国专家认为,将有20%至60%的人将被感染。中国本土目前很少有新增病例,每天新增的都是从海外输入的,于是有人开始担心,有人建议彻底封国,有人甚至设问:如果疫情在全球继续大面积扩散,那么我们能守得住吗?
正在发生的疫情检测了全球化的成色:通常几乎难以设想短短两个月时间内全球新冠疫情就有如此大范围的流行。1月23日武汉封城,一片哀嚎之时,中国专家们开始担心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成为下一个武汉,但当时没有想到欧洲的意大利和西班牙、美国的纽约成了下一个武汉。今天大概只有南亚和非洲大陆还没有大面积流行,但也开始进入恐慌了。新冠病毒告诉我们,世界确实已经一体化了,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人类确实已经进入“普遍交往”时代了。但另一方面,武汉封城之后,各国开始从中国撤侨,境内各省各地也开始相互封锁,前几天中国外交部发布公告:自2020年3月28日0时起,暂停外国人入境。一场疫情让我们见识了全球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存在,同时却也让我们看到全球化体系是多么脆弱和不堪一击。网络全球化还在(虽然也有隔离),而物理全球化已然降至冰点。就在3月26日,比尔·盖茨在电视上呼吁:向中国学习,全美应严格封锁,持续6—10周的时间。
新冠疫情让人们认识到了技术时代人类的普遍交往带来的普遍风险,于是各种逆全球化的声音在世界各地响起。有人声称这次新冠疫情是经济全球化的终点,有人说这是全球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将彻底改变全球工业的生产方式和供应链,等等。其实最近一些年来,反全球化的保守主义和地方主义思潮已经日益高涨,而这次疫情进一步强化了这股势力。可以想见,在疫情时期和后疫情时代,人类不得不面临一种在加剧的地方孤立、隔离倾向与全球团结协作倾向之间的紧张关系。

《马德里日报》镜头记录下的西班牙马德里市中心,
昔日熙熙攘攘的格兰维亚大道空空荡荡
有人问:全球化是可逆转的吗?自欧洲殖民时代开始的全球化进程将因为这次新冠疫情终结吗?我们必须看到,全球化以及人类的普遍交往是技术工业的后果。我们在今天普遍隔离的状态中还能听到各种反全球化的声音,这本身就已经表明:我们依然在全球一体化的体系之中,我们依然摆脱不了全球“技术统治”的机制。疫情固然导致各国、各族物理上的隔离以及国际人际交往的萎缩,但另一方面,全球疫情也将进一步刺激全球化,因为通过疫情,虽然政治“嘴炮”不断,各种猜疑、埋怨和指责不断,但人们也终于认识到,各国、各族如今都已经不可能独善其身,只有全球协作才能战胜疫情。[11]
技术工业已经彻底改变了我们。今日人类处境已经不一样了,我们使用微信和手机,随时随地可以接收和传播信息。在中国抗疫过程中,微信和互联网技术无疑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帮助隔离、求助求救、病情申报、疫情发布等,可以说是最大的抗疫辅助工具。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微信和互联网技术也使恐慌情绪的即时传播、大面积传播成为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放大了恐慌,因而放大了疫情风险。
互联网和数字技术在放大和操控民众情绪的同时,也使人变得麻木、冷酷。当疫情成为一条条曲线,而死亡成为一串串数字时,人类除了患者及其亲人们,多半渐渐失去了对病患和死亡的具身感受。我自己的经验就是如此。在疫情开始的最初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我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手机,登上百度的“疫情地图”,搜查各地确诊患者数据和死亡数据,内心是伤痛和恐惧的,但随后渐趋麻木,甚至不再经常看了。问了一些朋友,都有类似的情况。这当然跟个人经验的适应和习惯化有关,但无疑也跟数字技术的抽象和疏离作用相关。一句话,这种“技术人类”的抽象经验已经跟“自然人类”的具身经验相去甚远。今天我们真的需要想想:当死亡成了数字,具身感知丧失,我们的死亡经验发生了何种变化?或者说,我们把死亡当成数字来理解,意味着什么?
疫情中最令人紧张、也最令人沮丧的是我们的“他人经验”。萨特所谓的“他人即地狱”这一“实存主义/存在主义”的基本哲学命题似乎已经在疫情中展露无遗。疫情让人们对外部世界和他人产生了普遍的恐惧和不信任,我们把每个他人都当成一个潜在的病体或病毒传染源。更尴尬的是:我们一边叫喊着“武汉加油”,一边排斥武汉人(湖北人),视他们为瘟神,见他们就躲避。地方保护主义兴起,各省各地都采取了隔离措施,在封城前离开武汉的武汉人成了一群不受欢迎的人,四处流浪;即便在结束封城后,人们仍旧把武汉人(湖北人)视为病毒载体,3月底在九江发生的因拒绝湖北人跨境而引发的两地人员冲突,令人哭笑不得。
自然人类之间正常的交往经验是具体的、温暖的,包括亲吻、拥抱、握手等身体直接接触,以及聚餐、聊天、开会等间接接触,也包括我们大学里的讲课和讨论,但现在,情形完全变了,直接接触大概只在亲密家人之间,而跟“外人”的间接接触也被降到了最低值。从疫情开始到今天,我只跟几位朋友有过一次私人聚餐,虽然环境应该是安全的,但当时的情况是:没有握手,自觉保持一定距离,开餐前就有朋友提出来“用公筷吧”,隐隐中透露出相互间的“不信任”或“不放心”。可以预期,疫情过后,人群中会出现不少交往恐惧症和自闭症患者。从三月开始,我所在的大学实行“开课不开学”,学生不能返校,一概在网上上课。有人问我:上网课是什么感觉?我说:基本上是对虚无讲课,感觉十分不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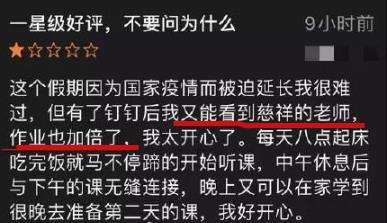
网课压力下学生给钉钉打一星好评

上海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教授多次提倡使用公筷
前几天网上有一个感人的短视频:女友感染新冠肺炎在医院抢救,男友希望见上一面,见面后男友果断脱掉防护服,掀开隔离的帘子,来到病床上与女友相拥相吻,视频字幕最后显示,这对意大利情侣已经双双离开人世。这个视频的真实性未知(现在网络传播的虚假信息太多),我们也可以不予追问。如果这是真的,这大概是这场疫情中发生的最唯美、最凄惨的爱情故事,着实令人唏嘘。
疫情使人类本来已经越来越被技术架空和抽离的具身经验进一步丧失了。这是在我们的生命和生活中正在发生的事。我们完全可以设想,通过这次疫情,互联网和虚拟化数字技术将获得一次加速机会,从而推动从自然人类文明向技术人类文明的转换进程。在此进程中,个人自由权利不得不进一步被让渡给技术极权主义,上述具身经验的丧失与个体自由的缩减是一体的。为了肉身的健康和生命的安全,我们只能屈服于技术控制,不得不进入“数字集中营”。
有朋友问我:疫情过后一切都会恢复正常吧?我说:放在以前可能会,因为人是健忘的,我们很快会忘掉伤痛,回归常态,继续前行;但这回可能不一定了,有些东西被激发了、被重塑了,或者被伤害了、被颠覆了,就不一定能重现和复原了。往大处说,这次疫情与以往在自然人类生活世界里发生的瘟疫不一样,它发生在“人类世”这一技术人类文明得以确立的时代,它也许跟原子弹一样,也算得上是“人类世”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技术在进步,自然在反抗,生命在衰退。技术已经改变世界,不变的是它的基本逻辑。这场世纪大疫情彰显了这个技术世界的各种矛盾和冲突,外与内、进与退、放与收、要与不要,都成了这个可以被称为“人类世”的技术世界多元交织的张力关系,经常令单一的立场和简单的判断变得愚蠢不堪。遗憾的是,我们在政治表态和互联网争论中经常见识这种愚蠢。我们承认我们今天处于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但我们却经常喜欢采取一元独断的立场和态度,并且诉诸媒体。
同样,技术也改变了自然生命。纵然已经受伤,已经颓败,但生命本体依然神秘,只是更需要呵护了,只是我们不知道如何珍重了。透过疫情,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技术对个体生命经验的改造和重塑,包括前面讲的世界经验、死亡感知和他人意识等。在技术时代里如何安顿生命?我们需要建立什么样的新生命经验?如何保存个体存在,保卫个体自由?这将是疫情中、疫情后人类面临的更尖锐、更艰难的问题。

张文宏今年2月提醒群众注意社交距离
(本文刊于《上海文化》2020年4月号)
注释
[1] 本文系作者为《上海文化》杂志组织的“生命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专题而作。文中涉及的与疫情相关的数据和资讯更新截至本文定稿的2020年3月31日。
[2] 赫拉利:《未来简史》,林俊宏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第1页。
[3] 德博拉·海登:《天才、狂人的梅毒之谜》,李振昌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4] 赫拉利:《未来简史》,第9页。
[5]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有统计标准方面的问题,中国的统计是“新冠肺炎患者”,而美国统计的是“新冠病毒感染者”。
[6] 《自然》(Nature):Covert Coronavirus Infections Could Be Seeding New Outbreaks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0-00822-x。
[7]2020年3月26日,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弗朗西斯·柯林斯发表题为《基因研究显示新冠病毒起源于自然》的博客文章,他援引几位科学家的研究得出结论:SARS-CoV-2刺突蛋白与人体细胞ACE2受体的结合水平要远远强于目前所有计算机预测的模型,所以它大概率只能靠自己的努力来进化出感染人类的能力。目前的生物工程师都不可能设计出有SARS-CoV-2这样的刺突蛋白的病毒。此文的判断是否确当?是否能终结“阴谋论”?恐怕还需要学术界来回答。
[8] 我们刚刚经历的前一次警钟是在2018年11月26日,世界首例基因编辑婴儿在中国深圳诞生,关于基因编辑的种种讨论成为全球关注的重大话题。
[9] 《多项研究称新冠病毒爱攻击男性这两器官》澎湃新闻网。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6489989。
[10] 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于2020年3月30日在白宫举行新闻发布会,宣称一种快速、方便的新冠病毒检测方法问世,同时力荐一种羟氯喹、阿奇霉素和硫酸锌的联合用药,被证明能100%治愈未转为重症的新冠病毒患者。但这两项技术尚未得到普遍认可和应用。
[11] 最近中美两国政府都转变了立场,从相互“甩锅”到合作抗疫。本文完稿后,第74届联合国大会于2020年4月2日通过了题为“全球合作共同战胜新冠疫情”的决议,强调新冠疫情已给人类造成巨大影响,国际社会应以世界卫生组织为指导,强化基于协调一致和多边主义的“全球应对”行动。
【作者简介】
孙周兴,1963年生,绍兴会稽人。1992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96年起任浙江大学教授;德国洪堡基金学者;现任同济大学特聘教授,同济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美术学院南山讲座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学会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等。主要从事德国哲学、艺术哲学、技术哲学研究。著有《语言存在论》《后哲学的哲学问题》《以创造抵御平庸》《未来哲学序曲》《一只革命的手》等;主编《海德格尔文集》(38卷)《尼采著作全集》(14卷)《未来艺术丛书》《未来哲学丛书》等;编译有《海德格尔选集》《林中路》《路标》《尼采》《悲剧的诞生》《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权力意志》等。
主编:朱生坚
编辑:曹晓华
运维:任洁
制作:蓝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