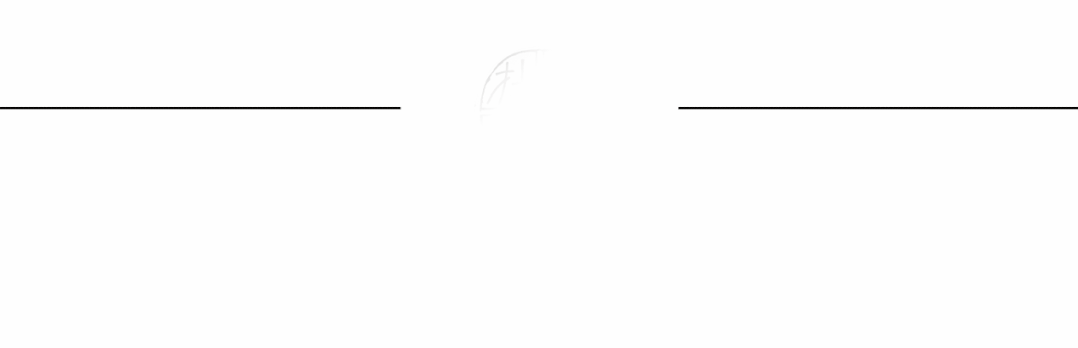
编 者 按
这个春节对于很多人来说有些特殊,为了响应政府倡议,不少人选择“就地过年”。因此,也有了不少“异乡客”眼中的过年情景。本期斯文在线推出一组笔谈,由文学所几位师生从不同角度向大家讲述这个难忘的春节。
就地过年:让异地变故乡的一次民俗试验
毕旭玲(上海社科院文学所副研究员、民俗与非遗研究室主任):回乡过年习俗起源于农耕社会,是守土安居意识的重要表现。在土地作为最重要生产资料的传统生产方式中,劳动力的数量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农业生产的丰歉,因此客观上要求将土地和劳动力通过种种方式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守土安居的民俗意识就产生于这样的背景下。
西汉永光四年,汉元帝为了缓和社会矛盾,下令普通百姓不用再去守卫皇家陵园,诏曰:“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安于本乡本土,不愿轻易搬迁,是农耕社会的黎民本性;而与亲人团聚,和骨肉相依,是民众在感情上的愿望。所以农业社会的民众围绕着耕地聚族而居,家庭意识浓厚,乡土民俗观念即使对外出谋生的人群也具有极强的约束力,吸引着他们形成了按照农业生产的节令,在农闲时返乡与亲人团聚的习俗。民俗具有不会被外力轻易更改的“惯性”,所以尽管我们早已步入工业社会,返乡过年的情结却依然扎根于每一个“外乡人”心中。

但民俗文化也处于不断的汰旧更新之中,比如唐宋时期的公务员们不会想到皇帝专门给假的寒食节在千百年后竟然不为人所知了;又比如今日我们称之为“春节”的节日,在民国之前的数千年中却被称为“元旦”“元日”等,而“春节”一词则曾指向整个春季,或立春节气。既然返乡过节习俗起源于农耕社会,那么随着经济生产方式的改变,作为上层建筑的民俗文化必然也会改变。早在新冠肺炎流行之前,就有不少父母投奔子女过年之事,而新冠肺炎的流行不过是给春节节俗的改变提供了一个契机
现代社会的流动性造就了大量在上海工作生活的新移民,但在以返乡过年为代表的传统习俗的影响下,不少新上海人仅将上海当作“他乡”,对于上海城市文化缺乏认同感,难以真正融入上海。而由防控新冠肺炎倡导的就地过年则提供了一个让新上海人融入上海城市的良好契机,不仅使新上海人可以感受充满海派气息的上海年俗,还能通过新春娱乐活动使他们加深对上海城市文化的了解,更能通过互访活动增进新上海人与同事、邻居基于业缘、地缘的情谊,这些都增强了新上海人对于上海城市文化的认同,将新移民从文化上尽快地“塑造”为上海人。
春节是中华民族最盛大的传统节日。2021年新春,数亿人的就地过年行为是一次让异地变故乡的民俗试验,不仅大大增强了移民对移居地的文化认同,更增强了各地民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知,将成为中华传统节俗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
传统的民俗文化与现代都市的理性文明还在磨合
程鹏(上海社科院文学所助理研究员):春节民俗的变化,是适应城市化进程和科技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则增加了新的变量。“就地过年”既是当下疫情防控的变通之策,也给未来都市春节民俗的发展方向带来了新的思路。
从消费主义的泥淖中抽身,变旁观为亲身参与,通过身体力行的实践来体验和感受春节,减少对购买服务的依赖。比如,可以居家练一下厨艺,做出一道道家乡的美食,安慰最想家的胃。同时,也可以深刻感受所在城市的年味美食,让味蕾带动身体,从了解到熟悉到喜欢,对所在城市产生更多认同。此外,亲自撰写一副春联,亲手制作剪纸窗花、中国结等饰品装饰自己的家,带领小朋友体验传统的民俗娱乐活动,都是感受春节的重要实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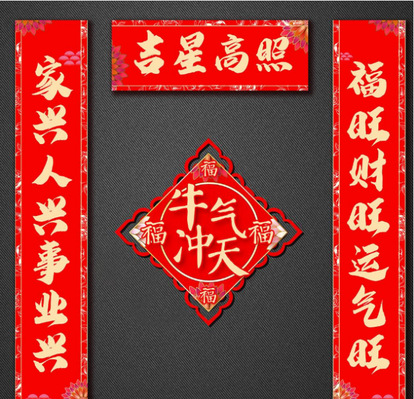
春节是面向未来的,春节的祝福表达的是对未来生活的信念,是面向未来的情感和愿望的表达。都市中的春节民俗一直处于重构之中,传统春节的民俗文化与现代都市的科技理性文明还在磨合。春节民俗需要创新,但在创新的同时,也需要了解传统春节民俗的深厚内涵,根深才能叶茂,只有守住传统的根基才能走得更远。
在物质生活丰裕的都市,人们的生活方式与观念早已改变,但过年那份浓浓的情怀始终未变。要让春节更有年味,需要激活传统春节的核心价值,融进新的时代内涵,让每个群体都参与其中,从而对这个节日产生深刻的感知和认同。
“形式”与“仪式”在这里有些混淆
任明(上海社科院文学所副研究员):作为在上海工作生活16年的“新上海人”,我还是第一次留在上海过春节。虽说是因为疫情响应号召的缘故,但也令我想到,“过年”对我来说已经不知不觉变成了一项责任性事务。回老家过年是为了陪父母;留在上海过年的几天,感觉跟平时没什么不同。
一直想去看的豫园灯展到现在还没实行。离正月十五还有几天时间,希望不要时间如流水地流过去。春节晚会才是我真正的“民俗”,因为我感觉自己并无期待,却如仪式般地每年都要“膜拜”——遗憾的是,“形式”与“仪式”在这里有些混淆。我希望自己的“膜拜”能够带着更多喜悦与虔诚,希望春晚四个多小时的节目能够给平时不看电视的自己带来惊喜,但这些希望都如“New Year’s Resolution”一般从来没有实现过。也许原因在我自己身上。今年春晚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上海歌舞团表演的舞蹈《朱鹮》。那一幕极美。令曾看过现场演出的我与有荣焉。
如果说仪式重要的话(对于节日来说尤其如此;“观看春晚”令我感觉自己过了大年三十),那么很多不知不觉从城市生活中消失了的仪式则令人感到遗憾。譬如,外滩的新年倒计时与烟火表演,背后当然有种种原因与考虑,或许也是指日可待,但缺失的日子确实令城市文化生活出现了那么一点儿空白。也许从环保的角度可以指出放烟花的种种危害,但如果一年一度,有那么多双明亮的眼睛共同仰望夜空的璀璨,有无数美好的心愿与祝福随烟花共同升起,这些足以抵得过暂时的环保危害。
就像豫园灯展,虽然16年尚未踏足,但是知道它在那里,就很好。那些灯一定很美。

2009年上海的豫园灯会
感受上海独特的年味,可谓色香味俱全
吴晗(上海社科院文学所助理研究员):在上海就地过年,感受上海独特的年味,可谓色香味俱全。
首先是色。走读上海成为春节期间体会城市民俗和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上海的建筑颇具特色,有江南传统园林代表之醉白池,体现明清文人风雅意趣;又有外滩万国建筑群,展现西方建筑美学。此外,还有豫园,除古色古香建筑外,特别是春节灯会,展示浓浓年味与地域风味。更值得关注的是,红色文化建筑群,诸如龙华烈士陵园、陈云纪念馆、鲁迅纪念馆等,纷纷开展系列活动,展现红色文化脉搏。在走读中,进一步体味海派文化兼容并包的精神。

陈云纪念馆新年一景
其次是香。此处的“香”有多重意蕴,是花香、硝烟与香火的糅合。上海的城市绿化颇为成熟。暖冬时节,梅花怒放枝头,清新淡雅的腊梅、白梅,艳丽招展的红梅,已吐芬芳;余味悠长的水仙,成为重要组成;松柏长青,带有清冽气味;又有含苞欲放的玉兰,作为随处可见的市花,雀跃传来春的香气。身处外环,还能隐约耳闻炮竹声声,硝烟的气息,也成为年味的重要一环。上海寺庙众多,亦是地域一景,民间宗教祭祀、法会等活动也在除夕、年初有条不紊地举行。在新年伊始,于袅袅的香火气息中,寄托对未来的美好向往与憧憬。多层次的气味,构成了上海春节之丰富与独特气息。
最后是味。除夕年夜饭是传统文化中必不可缺的一环。一家老小相聚餐厅,在人声鼎沸中享受美食。除地方节庆必点菜色八宝饭、汤圆、熏鱼之外,还添以牛年为主题的“牛气冲天”“牛年大吉”等菜品,融入西北等地风味。上海美食以鲜甜与浓油赤酱为特色,油而不腻,香气扑鼻,摆盘小巧,妆点别致,充分体现地方审美特质,以精致、细腻为重。但同时,作为移民城市,随着全国甚至是全世界各地民众的融入,本帮菜系也引入了各地美食中的精华,使得除夕菜色更为丰富,层次多样,充分体现“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特点。
愿家乡疫情早日平复,愿家人一切安好!
陈君然(上海社科院文学所研究生):今年就地过年的意义可能是让我们以后的每一个年都能陪在家人身边吧。
其实上大学以来我没有过过几个舒畅的年,总有一种完成任务式地哄姥姥姥爷开心的感觉。所以当我决定就地过年,我能想到的最大好处就是远离家里的琐事,和平万岁。况且还有几个好友也没回家,约好了一起吃饺子、打牌、看春晚,总之没有家里的许多规矩过得更自在。
但是当我知道姥姥再次生病,虽然赶在年前出了院,可好不容易请的护工也回家过年了,只能让几个身体一个比一个差的“老人”(大舅、我妈、小姨)去轮番照顾另一个任性的“老小孩儿”,又听到姥爷因为照顾姥姥没睡好觉而委屈地“抱怨”,而我什么忙都帮不上的时候,心疼的感觉无以复加,甚至有点想要放弃在江南生活的规划。
大年初三上午去看了电影《你好,李焕英》,午睡梦到我初中上学忘记带胸卡,我妈让我自己回家,但我不是真的回到了初中,有一种我在快速长大变老而我妈只会老得更迅速的感觉,这种感觉让我发自内心地恐惧。醒来又想到,我妈参与了我成长的全过程,但是她变老的过程我却没有参与,就觉得有点不太公平。
虽然我妈总安慰我说“这么多同学都没回家”,但其实这个安慰真的不是很有效,我只觉得对她一个人在家的担心更多了,对不能陪她的牵挂更多了,对没能帮上家里的忙的愧疚也更多了。
所以现在,我只能想到就地过年的诸多“坏处”了。

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
愿家乡疫情早日平复,愿家人一切安好。
发现过年的“仪式感”其实是不可或缺的
马晓萌(上海社科院文学所研究生):2021年的春节过得很快,对于第一次“就地过年”的学生党来说,这是一个特殊而难忘的春节,于我而言更是带来了一份永久独特的记忆。
说起留校过年的理由,除了最主要的要响应国家防疫政策、遵守当地防疫工作安排之外,还有自己的毕业论文、工作等事情要着手处理,由于新冠病毒引发的疫情带有复杂性和未知性,担心开学后无法按时返校,索性留校度过寒假。
以前在家过年的时候,只要按部就班地按照已有的传统流程来即可,包括提前打扫卫生、准备年货、走亲访友、祭奠祖先等等,你来我往,好不热闹。无论哪一年,我家当地的超市永远都会播放《恭喜发财》这一首歌,走在街上都能看到各式各样又大同小异的红色新衣,小城特有的烫发造型也似乎在一夜之间迅猛增多。节礼送来送去也都是那么几种,每年买的种类都差不多。新年忙了大人、乐了孩子,肯德基麦当劳里拥挤着无所事事而又乐于聚会的年轻人;孩子们无论做错了什么,都可以因为“过年了”而得到原谅。这是我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春节,无比熟悉,周而复始。

在老家过年特有的这些零零碎碎的仪式,我原以为我不屑于去记住,潜意识里总觉得这都是大人的任务。尽管自己一年年地长大,早就应该独当一面去替父母分担一些,但过年时总还可以被当作小孩对待。直到我今年自己一个人在异地过年,过去的在老家过年的记忆都涌现出来,我才发现我对那些仪式已经如此熟记。当这些仪式离我远去,我竟然觉得冷清和不舍,我很想去放鞭炮看烟花,想回老家看望爷爷奶奶,想自己贴春联福字,想去人挤人的繁忙的超市买年货,想在年三十的晚上和家人一起守岁吃饺子。以往我不觉得是仪式的这些仪式碎片,零散地拼成了一个完整的老家春节。
以前我总觉得过年的“仪式感”太过,是一种负担,总想着这么麻烦能省就省。但这次自己经历了一个人就地过年之后,才发现过年的“仪式感”其实是不可或缺的。没了仪式感,好像过年也不像过年,跟平时上学的日子无法区别。幸好学校为了照顾我们这些留校的学生,给我们准备了零食年货、围巾,还专门免费供应了新年一周的餐食。这些物质和精神上的关怀,让我惊喜和感动,同时也让我意识到,这些是学校给我们的仪式感,让我们能有过年的氛围,给我们力所能及的温暖和体贴。对我自己来说,尽管每年都不能完整地看完春晚,但今年留在学校,看春晚却成为了我重要的仪式之一,是我为数不多的能让自己感受春节氛围的载体。父母从家里给我寄来了自己做的年货,我和家人朋友的视频电话几乎每天都要有。这些仪式感支撑着我,让我在异地得到依靠和慰藉。就地过年的经历也使得我重新审视自己之前的生活方式,是否正是因为欠缺了必要的仪式感,而因此忽略了不少美的事物和感情。
对年轻人来说,我们可能倾向于要更新一部分过年的仪式、淘汰掉不合时宜的繁文缛节,想要更加自由便利的空间。但是站在父母这一辈还有老人的立场上,也许对他们来说,他们有他们特定的“仪式感”,有了这些才是真正的过年,一年的盼望和收获就在此中得到展示和终结。我们无论身在何方,必须尽自己所能地去关怀他们,让他们也能逐步和时代接轨,让“年味”有更多更丰富的色彩,让“仪式感”成为新年回忆的闪光。

今年你在哪里吃元宵呢?
主编:朱生坚
编辑:曹晓华
运维:任洁
制作:大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