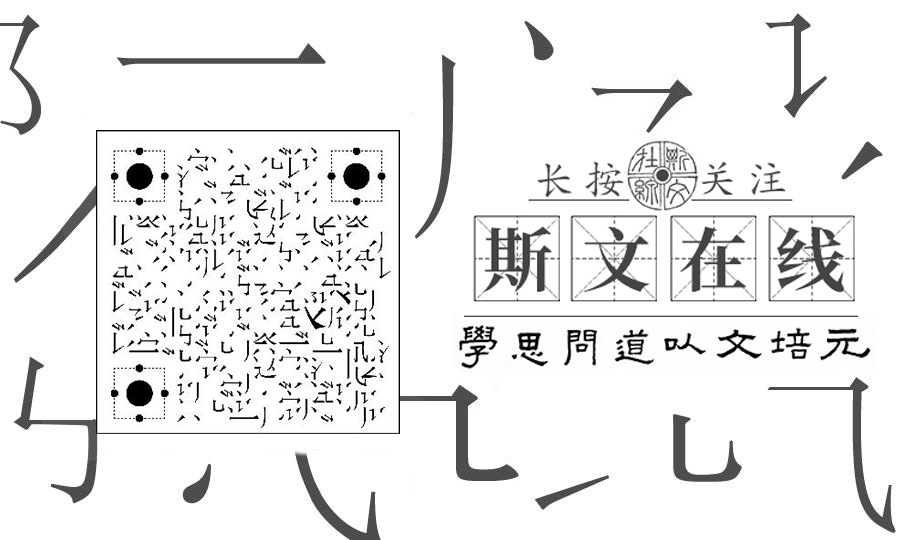中国当代文学的思想性问题近来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和讨论。作品的思想性,取决于作家的思想能力。十几年前,王光东教授曾经深入探究当代作家的思想能力问题,撰写了一系列文章。这里刊发的是其中一篇,属辞平淡,寄意深远。时至今日,文章涉及的一些社会表层问题依然存在,却已然淡出了学界的视野;而其中的根本问题,即当代作家穿透现实、回应现实的思想能力,以及与此相关的当代文学的思想性,仍然是不容回避的问题。然而,“此道非争竞务进者能知,惟静退者可入”(陆象山),中国当代作家、批评家之中的静退者,而今安在哉?
文学家不是思想家,文学作品不是思想论文,对文学作品似乎不能完全以“思想的深度呈现”来衡量作品的优劣,但优秀的作品大多数都蕴含着深刻、独到的思想却是文学史证明的事实。这种“思想”不是外在的观念,而是内在于文学审美世界的重要因素,它与作家的经验、情感、想象、甚至叙述方式联系在一起,无法分开。这种思想的生成和呈现能力就是文学的“思想能力”,这种能力从根本上说是与作家的人格、精神向度、文学情怀等问题密切相关的,在当下的文学语境中提出这一问题,并不是为了说明作家的人格精神、文学情怀与文学的“思想能力”之间的关系,而是因为文学的思想能力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的变化和上世纪80年代所确立的文学观念的影响下出现了一些值得我们思考的新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影响着当下文学的思想深度的生成和呈现。

我们先来讨论第一个问题。自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已有的社会文化构成因素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日益强化的物质——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和经济——商业的利益主导性现实,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也影响着文学发现生活真相的能力和思想的能力,这样说的原因在于:(1)当下文化语境中出现的与物质消费主义和经济商业活动密切相关的新的文化因素表现为“日常生活需要的满足成为相当部分大众的基本目标和生活理想,文化的生产与消费呈现为大众享乐动机的赤裸裸地满足,处处洋溢着感性的快乐情调,沉浸于日常生活直接满足中的大众,不再追求自身生活的历史意义和价值深度,而是主动寻求能够体现当下感官满足的文化活动形式。物质功利主义的企图直接引入了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过程,使得所谓‘审美’与人的物质欲望之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同构和互动”[1]。这种感官的、日常化的欲望审美活动所呈现出的是私人性、娱乐性、物质性、肉欲性的强化趋势,与此相对应的必然是公共性、批判性、精神性、理想激情在审美活动中被遮蔽或忽视;(2)与这样一种新的文化因素相关的是部分作家产生的中产阶级心态,这一问题许多批评家曾讨论过,中产阶级心态的最大问题就是“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在平庸的生活活动中,追求日常化的审美情趣,而不去关心时代与现实所面临的“大问题”。显然“日常生活的欲望审美”和“中产阶级”心态对作家的影响是深刻的,特别是当这样一种日常生活需要的直接满足成为大多数人认可的一种思想意识时,作家与这样的生活现实是建立一种肯定、认同的关系,还是看到现实背后更为复杂的问题而形成独立的思考方式、呈现深刻的思想力量呢?

风靡一时的“葛优躺”有了不同版本的表情包,
生动诠释了当代青年之“丧”
文学的思想力量是在作家与现实生活有意义的联系中产生的,所谓有意义的联系就是现实的人的活动构成了作家“思想”的内容,文学创作区别于其他精神生产的重要特征就在于它是对于整体的社会的人的活动的呈现,人又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文学的思想能力在文学创作中就具体表现为对人性的理解和表现的能力,只有在具体的现实情境和社会关系中才能见出人性的丰富、复杂和独特,也才能与现实构成某种意义关系。正如卡西尔所说:“人并没有什么与生俱来的抽象本质,也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永恒人性,人的本质是永远处在制作之中的,它只存在于人不断创造文化的辛勤劳作之中。因此,人性并不是一种实体性的东西,而是人自我塑造的一种过程。”[2]“人的哲学一定是这样一种哲学:它能使我们洞见这些人类活动各自的基本结构,同时又能使我们把这些活动理解为一个有机的整体”。[3]那么,在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创作中,作家是怎样理解和表达人性是有着很大的差异,为了说明这一问题,不妨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作一具体分析:(1)突出人性中的欲望化因素。人性中的欲望化因素在上世纪90年代的许多作品中就已经被作为文学的重要内容得到重视。但是在新世纪以来的某些作品中,这种欲望化更多地与“日常生活的享乐”联系在一起,欲望往往呈现出的是物欲、情欲的内容,并且文学的叙述和想象都带有“私人”的性质,忽视了现实诸种力量和因素在“人性”形成过程中的作用。(2)新世纪以来社会生活发生巨大的变化,人处于这种社会的变化中,其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变化,虽然有些作家也力图去写出变化中的“人”,但由于种种原因,对变化的现实缺少整体的、深入的把握,“人性”的复杂性也难以呈现。有些作品甚至带有浓重的“观念化”痕迹,从先验的社会判断去图解现实的生活,使文学作品缺少鲜活的生活气息,思想的深度也就无从说起。(3) 对于“70后”和“80后”的部分青少年作家而言,他们的作品表现出一种“脱离历史和社会”的非现实化倾向,这些青少年作家所喜欢的“玄幻文学”有一个主要特点就是所谓的“架空性”,“一种类似网络电子游戏的非现实性体验(这不是我的发明,而是学界的基本共识)。这种‘架空性’的实质是彻底的逃避社会历史和政治责任,或者体现出一种‘脱历史’、‘脱社会’和非政治化之后的‘不能承受之轻’”。[4]如上几种类型的小说显然对人性的表达存在抽象化的倾向,这些作家在消费——满足——感官享乐的过程中,误认为人的自我欲望的满足就是人性的全部内容,忽视了人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还应有精神的、理想的、责任与良知的等更多的社会性内容,也就忽视了对影响人性塑造的各种社会因素——政治的、伦理的、道德的、法律的、经济的等等方面的认识和理解,从而对消费文化意识形态取一种简单的肯定和认同态度,使文学作品与日常欲望化审美之间获得了某种同构关系,那么作家也就不会去思考人的欲望产生的机制、现实在引发欲望的过程中又存在着怎样的问题,也就不会对这样的现实用一种批判的态度去思考,思想的力量也就难以呈现。

第二个问题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所形成的文学价值观念的影响。在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创作中,提出了“纯文学”的观念,这一问题的提出是在反抗“文学的政治工具化”过程中产生的,当时为了获得“文学”表达的合法性,突出强调人与外在政治规范的对抗以及文学自足的内在特质,这种“自足的内在”特点在1980年代是包含有强大的现实力量和针对性的,它的意义在于恢复“文学的审美性”特质,把文学从非文学的工具论中解放出来,在今天仍然强调文学的“自足”和“内在”,仍旧有重要的意义,因为今天许多非文学的力量仍然对文学构成强大的压抑,这也正是今天文学的复杂性所在,文学理应对这种复杂的现实做出思想的回应,但由于某些作品把这种“自足的内在”和消费意识形态的私人性、物质化、欲望化相联系时,这种“文学的内在性”同样暴露出抽象性的弱点,因为在这种联系中,“内在性”与“私人的欲望”具有了某种同构意义,成为“个人”的自言自语,也就弱化了思想能力在作品中的呈现。由此,我们可以说“文学的内在性”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它和外部世界始终有着深刻的有机联系,就是西方文学中极端的唯美主义者,也是以对“庸俗社会”的否定建立起了与现实之间的有意义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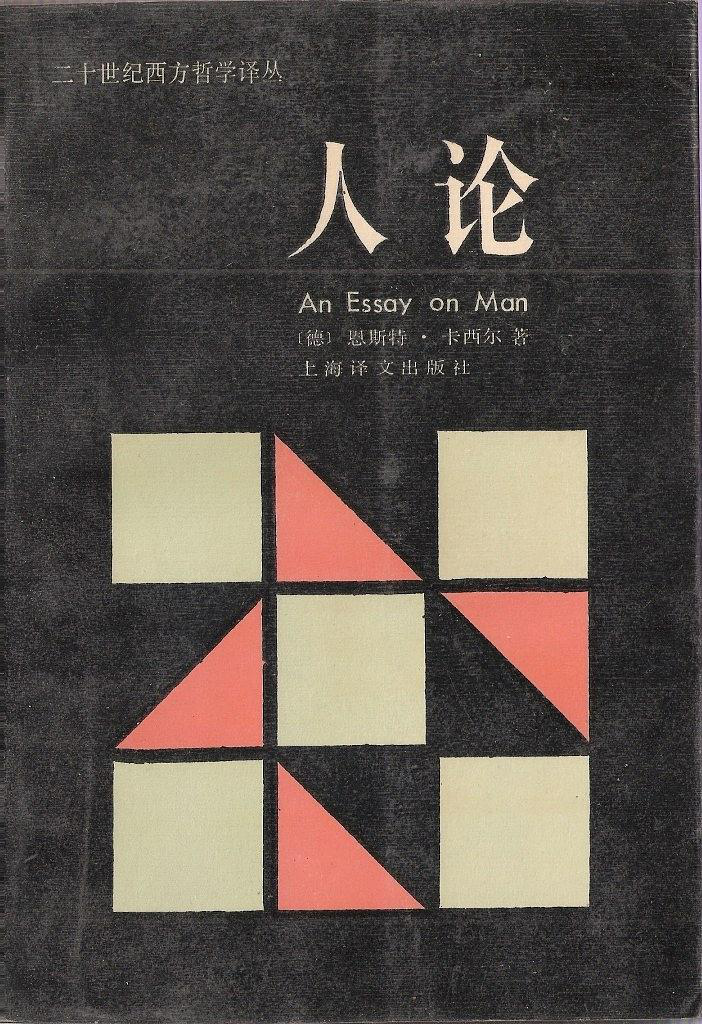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12月版
影响新世纪以来文学思想能力的表达因素,除了如上两个方面之外,当然还有其他诸多方面的问题,但如上两个方面的问题显然是值得我们特别重视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新世纪以来的一些优秀作家,并没有对消费意识形态影响下的日常生活取一种简单的认同和肯定的态度,而是在现实和历史的联系中,思考着人的命运和人性的呈现形态以及人的行为方式,通过“人”的理解,表现出把握现实的主观能动性和思想的力量。譬如阎连科的《受活》、莫言的《生死疲劳》、贾平凹的《秦腔》、王安忆的《上种红菱下种藕》、尤凤伟的《泥鳅》等等。在上世纪90年代,“由于大多数作家对市场经济大潮缺乏精神准备,采取了回避当下生活的态度,有的从历史的角度继续知识分子的启蒙理想,有的则以更加遥远的历史题材寄托个人情怀,淡化地处理个人理想与现状的尖锐冲突,既使一部分新生代作家与当下生活保持了近距离描写,也大多局限在个人的狭窄生活空间 (陈思和语) ”。[5]在此情况下,新世纪以来所出现的这些长篇小说就具有了重要的意义,不仅“人”在市场经济大潮下的浮沉起伏、生存困境、精神冲突进入了作家的思想视野,而且表现出了作家以独立的思想认识生活、把握现实的能力。虽然由于作家经历和审美倾向以及生活经验的差异,对现实的表达、人性变动中的复杂性的理解有很大的不同,并且有水平高低之分,譬如有些作家在进入现实层面的叙述时,人物形象有时流于粗疏和观念化,对现实中“人性”的复杂性缺少充分的理解,但是他们艺术世界中的“人”具有了较为浓郁的、鲜活的生活气息,现实文化因素不仅拓展了作家自身的思想视野,而且使艺术与现实中的“人”有了更密切的联系和开阔、复杂、丰富的境界。贾平凹的《秦腔》和王安忆的《上种红菱下种藕》是特别值得重视的两部作品。《秦腔》是一部当代“经典”,人性在现实生活巨大的变动中,呈现出各种各样的色彩,人与土地、人与城市、人与人、人与历史的诸种纠缠鲜活地呈现出了人性的复杂形态,呈现出了当代社会生活中的尖锐矛盾和冲突所导致的人的辛酸和痛苦。《上种红菱下种藕》是一部新世纪的风俗画卷,它从一个小孩的眼睛,看到了改革开放后小镇发生的种种混乱而又富有生机的生活场面。在这里已有生活秩序被搅动后,相对稳定的人性、伦理、道德也开始出现了变化,人与人之间开始了一次又一次不愉快的碰撞,每一次碰撞后的和解都是人性向善的一次调整,就在这种调整过程种,文学与当代现实保持了深刻的内部联系。这两部作品证明:只有人自身的现实存在,还有他周围的外部世界和日常生活,同时进入作家的意识视野,共存于作家发现的艺术世界中,人性呈现的因果因素和发生学因素才能得以理解,艺术的审美力量和思想深度才能得以呈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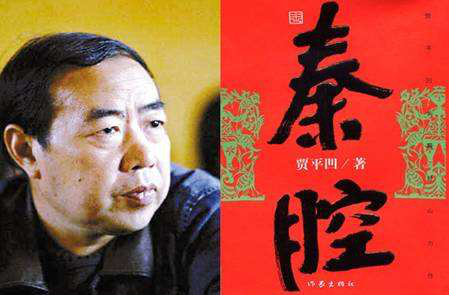
贾平凹与《秦腔》
文学的思想能力自然与多种因素有关,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作家从什么样的立场上去理解和认识目前的生活。从认同消费意识形态的主场去理解生活,肯定是以日常生活的物质满足为描述对象,将审美兴趣转向私人生活的物质方面,这样的写作不仅忽视人的精神世界在当下文化语境中的复杂性,而且会遮蔽对当代社会中出现的重大问题的认识。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一个作家的思想能力的获得需要一种民间立场。所谓民间立场就是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叙说老百姓的故事,依据民间的思维方式理解民间的生活。一个作家有了这种理解世界的方式,肯定把现实包含于思维之中,获得深厚的思想能力,因为老百姓构成了一个时代的主要力量,他们生命经验、情感的表达过程,就是人在现实中挣扎、生存的过程。换句话说我们只有与民众处于同一文化价值的言说过程中,才能理解、发现他们的喜怒哀乐、精神渴求和生活的真相,才能发现我们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存在着怎样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正是“文学的思想能力”产生的前提。《秦腔》、《受活》、《生死疲劳》等优秀作品就都体现着这种精神。
由上论述可以看到:在一个文学被“消费文化”和“市场经济”所影响的时代,文学的思想能力虽然遭遇了许多新问题,但真正优秀的作家仍然具有穿透现实、揭示生活真相的艺术能力和思想的能力,这种能力正是优秀作品得以产生的重要因素。
注释
[1]陶东风:《告别花拳绣腿,立足中国现实》,《文艺争鸣》2007年1期。
[2][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5、6页。
[3] 同上。
[4]陶东风:《告别花拳绣腿,立足中国现实》,《文艺争鸣》2007年1期。
[5]陈思和、王光东:《文学能否面对当下生活》,《文汇报》2002年5月13日。

【作者简介】
王光东,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已出版《现代•浪漫•民间》,《民间: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视野与方法》,《城乡关系视野中的新世纪小说创作》等著作多部,发表论文多篇。
主编:朱生坚
编辑:曹晓华
运维:任洁
制作:蓝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