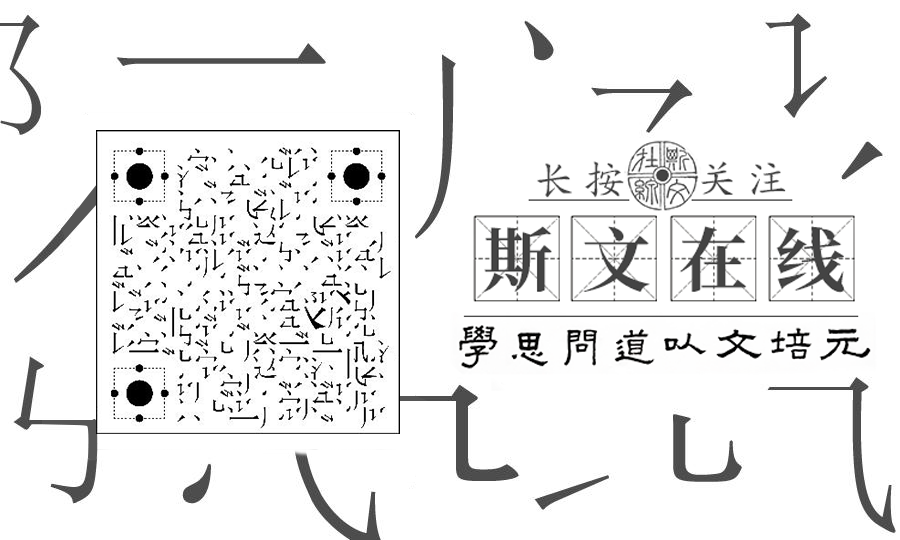今年是汪曾祺先生(1920.3.5—1997.5.16)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斯文在线转发李庆西老师这篇名文,以志纪念——正好晚了四个月,想必散淡的汪先生也不会见怪吧.
一
汪曾祺的小说很好读,有点文化的人都能读。他写得平淡。
平淡不是淡而无味。姜白石评论陶渊明说过“散而庄,淡而腴”的话,汪曾祺的小说就这样。譬如,他要写出一个中学校长的庸俗,落笔只是那人的日常起居和他周围那些人的闲事儿;都谈论什么,喜欢什么,一帮人如何在一起打发礼拜天,如何有滋有味地过着那种腻歪的日子(《星期天》)。如此有一搭无一搭地扯来,构不成故事,却很有一些人生况味。他这里不用讽刺,更丝毫没有外国小说里常用的那种“灵魂拷问”的笔法。这种“宽容”形诸散淡的笔墨很是表里相宜。作为一种叙事态度,这本身就含藏丰富的意味。当然,“丰富”只是感觉上的说法,倘要细辨汪曾祺的文体意味,那得另做一篇文章,这里不多说。
从艺术渊缘上看,汪曾祺明显继承了中国士大夫诗学传统。他的笔墨很有古代诗词、散文的韵致。具体说,在古人的风范中,他更趋近宋人的格调,明人的情趣。汪曾祺自己讲到,他爱读宋人笔记甚于唐人传奇(《<晚饭花集>自序》)。虽然他不曾说喜爱宋诗甚于唐诗,却也表示过“诗何必盛唐”的看法(《谈风格》)。他自知学不来盛唐诗人雄浑、刚健之风,似乎甘愿为“开元天宝以下人物”。这种真率也不简单,现在不多见。他还一再说起明人里边的归有光,喜欢的不得了。
他并不勉强自己去喜欢什么,去做什么。他的风格中有着古典的人格意味。

当然,这些都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汪曾祺。他早先的情形知道的人恐怕不多,因为他六十岁以后才为人瞩目。他六十岁那年,也就是一九八○年,写了《受戒》。文学史上,像这样“大器晚成”的例子也算少见。其实,汪曾祺早年的有些作品跟现在的风格相去不远,如《老鲁》(一九四五年)、《落魄》(一九四六年)等。但也有一些就不像是他汪曾祺写的。有一篇《复仇》(一九四四年),几乎是意象派诗人的笔调,讲着一个沉重的故事,文字里却飘荡着轻盈、流动的意绪。
太阳晒着港口,把盐味敷到坞边的杨树的叶片上。
海是绿的,腥的。
一只不知名的大果子,有头颅那样大,正在腐烂。
贝壳在沙粒里逐渐变成石灰。
…………
来了一船瓜,一船颜色和欲望。
一船是石头,比赛着棱角。也许——
一船鸟,一船百合花。
深巷卖杏花。骆驼。
骆驼的铃声在柳烟中摇荡。鸭子叫,一只通红的蜻蜒。
惨绿色的雨前磷火。
一城灯!
嗨,客人!
客人,这仅仅是一夜。
你的饿,你的渴,饿后的饱餐,渴中得饮,一天的疲倦和疲倦的消除……你一定把它们忘却了。你不觉得失望,也没有希望。你经过了哪里,将去到哪里?你,一个小小的人,向前倾侧着身体,在黄青赭赤之间的一条微微的白道上走着。你是否为自己所感动?
“但是我知道我并不想在这里出家!”
他为自己的声音吓了一跳。这座庙有一种什么东西使他不安。他像瞒着自己似的想了想那座佛殿。这和尚好怪!和尚是一个,蒲团是两个。一个蒲团是和尚自己的,那一个呢?……(中间有删节,用省略号表示——笔者)
这就是另一个汪曾祺。笔墨澄澈、透明,也单薄。惆怅,却不粘滞。这故事本身很有几分机巧。母亲让儿子去给亡父报仇,将那仇人名字刺在他腕上;儿子涉水越山,走过许多地方,结局竟是遇上另一个复仇者——在别人腕上刺着自己父亲的名字!这里不光是意象派的抒情,还有点欧·亨利的味道哩。这般诗情和哲理,足以说明汪曾祺年轻时候的才气。
也许,用“少喜唐音,老趋宋调”的说法来概括汪曾祺的创作生涯不太确切,但是可以肯定,其前后确实有过一番不小的变化,无论是叙事风格还是审美心境。跟现在的许多青年作者一样,汪曾祺最初也是从“洋”路子上走过来的。他回忆四十年代初在西南联大读书时,也和许多年轻人一样,“一开始总喜欢追求新奇的、抽象的、晦涩的意境。”(《美学情感的需要和社会效果》)现在我们看八十年代复出的汪曾祺,从他平易恬淡的风格中还能想见那个年轻的有点浪漫和躁动的汪曾祺吗?
八十年代的汪曾祺是彻底皈依传统了。看上去他似乎早已丢开了一切个性鲜明的自我追求;他艺术上那种温和的姿态,笔下流露的那种瞩意琴棋书画、草木虫鱼的女人情趣,很容易使人想到禅家所称“平常心”之道。一些评论者认为汪曾祺的思想与老庄玄禅有关系,汪曾祺自己不在意这种说法,他倒表示更多地认同儒家。(《我是一个中国人》)当然,不管怎么说,他是在传统文化中找到了寄托。对此,批评家们还可以从个体心理发生角度再做探讨。不过,事情既然发生在与汪曾祺文学历程相始终的特定社会历史阶段,个体的心理发生必然受诸其间各种复杂因素的制约。在他面前,有现实的也有包含在现实之中的传统迫力。而正是在这种条件下,透过那种温柔敦厚的美学情调,恰恰可以看到一个灵魂的挣扎。
不是没有自我,而是“无我”之我。汪曾祺最近十年来的作品都可以印证这一点:他是用逃遁的方式较为完好地保持着自由的个性。他在“皈依”的过程中,逐渐完成了自己。事情正如大诗人艾略特所说:“诗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自然,只有有个性和感情的人才会知道要逃避这种东西是什么意义。”艾略特这段话出自《传统与个人才能》那篇著名论文,在那篇文章里,他对诗人如何真正有效地维护自己的个性作了出色的阐发。

九十年代的汪曾祺
二
汪曾祺认为“小说是回忆”。他说,作家的情感要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才能形成小说。(《<桥边小说>后记》)这是“因静照物”的意思。其实,别人的创作过程并不都是这样。他说这话,跟他写小说一样,伴有某种回忆的心境。他在想自己是怎么走过来的。早年写《复仇》的时候,也许还没想过小说跟个人经验有那么多关系。人们都有回忆自己往事的时候,却不是每个人都能获得那种回忆的心境。汪曾祺在对一切文学问题进行思考或者随便想想的时候,总要追溯自己某个兴趣、某种看法的来源或形成。他倒不在乎别人在关心什么,也很少谈到当前的学术思潮。他复出以来,写小说同时也陆续写下一些讨论创作的文章,又把这些文章集拢来,出了《晚翠文谈》一书。前文引到汪曾祺本人的说法都在这书里。他这本书,行文是大白话,内容是大实话。但是,其间的妙处及种种意味并不那么容易领会。因为这里不需要拿专门的学问去做解释,不必找到海德格尔那里去。就像齐白石画上的一棵白菜一把葱,看不出什么深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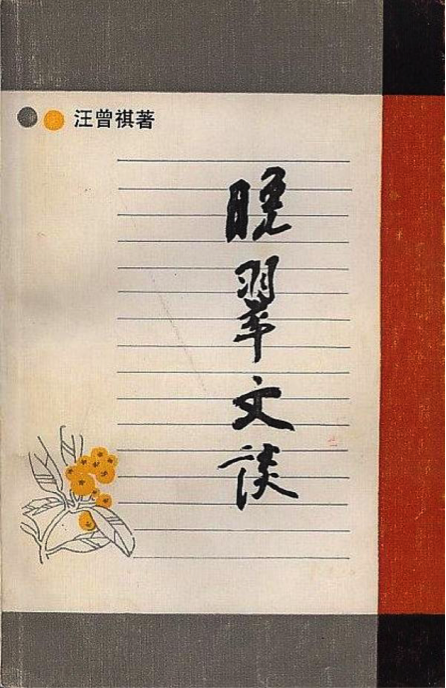
汪曾祺《晚翠文谈》
可是,世间的有些道理可不可以从“深刻”那儿绕过去呢?且不说超越吧。
事情是这样:当一个人经历过孤独、苦闷、迷惘以及孜孜不倦的摸索之后,回头再看那个世界,许多复杂的事物在他眼里反而变得简单明了了。这大概就是一种超越。汪曾祺写《晚翠文谈》那些文章时,正到了这个“蓦然回首”的境界。几十年的政治风云和文学潮汐恐怕并不比生活本身重要,尽管那也是一种经验。而那种早已沉淀在理性中的经验,在感觉中就模糊掉了。一个真正热爱生活并重视体验的作家,记忆的鸿爪倒是会停留在些许小事上。比如童年时看草台班子演戏的情形,汪曾祺现在想起来还是饶有兴味。他文章里一再提到,曾在一段很无聊的日子里读吴其浚的《植物名实图考》,读得津津有味。那是四十年代末,他在上海做中学教师。很难说这本植物学著作对一个作家的思想和艺术有所影响,但对于他,却真是比萨特的学问来得重要。一切追求“深刻”的理论,大抵对这种缺乏价值判断的个人兴趣不屑一顾。可是,又如何知道这不是一种价值选择呢,价值一定要以通常的(或流行的)价值取向为准则么?汪曾祺对植物的兴趣还有一件例子。那是他被错划右派下放到张家口坝上的时候,他在一个农科所干活,劳动之余有一桩他很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画马铃薯图谱。那跟艺术创作毫无关系。可是事隔那么多年,他文章里回忆起来,还陶然其中。可见那不是当时处境下的聊以自慰。
也许,汪曾祺这方面的兴趣跟幼年时聆受的“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儒学祖训有关,也是一种修养。但是这一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他接受过许多新鲜的人文思想理论之后,还又不断回到那些初始的经验和日常兴趣中去,在那里边确证自己,培养自己的情志。为什么要这样呢?也许这本身又是一种兴趣,或者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孤独。从客观看,这是脱俗的做法。文人的脱俗实际上倒要采取近俗的姿态,因为他想摆脱的往往是文人堆里的风雅,或者说某种文化形态的东西。按古人行例,一个人如果由于习性或因受限而不能从大处去开拓,那么他可以在某些小事情上确立自己的品格。虽然是小事情,只要真正注入一种个性,也便产生不可言尽的意义。譬如,古时的王子猷雪夜访戴,“乘兴而行,兴尽而返”,阮仲容七夕晒裈,“未能免俗,聊复尔耳”,都是很有名的例子,都各有精神所在。一部《世说新语》多半是这类话题。汪曾祺虽不学晋人的任诞,却也有一点士大夫文人的自由意志。
《晚翠文谈》这书里有不少地方说到读书的体会和乐趣。这种话题比讨论文学更直接的映见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在《谈谈风俗画》一文中,汪曾祺说起自己爱看讲风俗的书。“从《荆楚岁时记》直到清朝人写的《一岁货声》之类的书都爱翻翻。”他回忆上初中的时候,看了《岭表录异》和《岭外代答》,对讲地理的书和游记之类产生了嗜好。他说,“不过我最有兴趣的是讲风俗民情的部分,其次是物产,尤其吃食。对山川疆域,我看不进去,也记不住。”从这种阅读兴趣中可以看出,汪曾祺喜欢的都是跟生活有直接关系的东西。或者说,那些东西本身就是世俗生活的一部分。这个自幼就在儒家文化中熏染过的读书人,倒没有治国平天下的志趣。

所谓“治国平天下”,不完全是一个出处问题,它也是一种责任意志。对一个在基本人生态度上比较恪守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没有那种责任意志是很奇怪的。
当然,汪曾祺不是一个正统的尊孔习儒的知识分子。他那一代人中,地道的孔孟之徒大概很少了。但汪曾祺对于儒家的文化思想,还是有着与人不同的选择。他说,他“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具体说,他欣赏的是孔子的人情味,喜欢的是“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情调。他还喜欢陶渊明诗中的“人境”气息,“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他觉得很美,很亲切。他认为陶渊明是一个“纯正的儒家”。(《我是一个中国人》)显然,这样的认同是把儒家的许多“道理”都排除在外了。
说到陶渊明,倒有一个可以补充的话题。据陈寅恪考证,陶渊明家世宗教信仰为天师道,而其本人于斯亦习气未除,实际上是“外儒内道”。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流之关系》一文中,陈寅恪曾以数语概括陶渊明的思想特点,其中的一些关系对理解汪曾祺的思想情趣会有帮助,不妨抄录如下:
渊明之思想为承袭魏晋清谈演变之结果及依据其家世信仰道教之自然说而创改之新自然说。惟其为主自然说者,故非名教说,并以自然与名教不相同。但其非名教之意仅限于不与当时政治势力合作,而不似阮籍、刘伶辈之佯狂任诞。盖主新自然说者不须如主旧自然说之积极抵触名教也。又新自然说不似旧自然说之养此有形之生命,或别学神仙,惟求融合精神于运化之中,即与大自然为一体。因其如此,既无旧自然说形骸物质之滞累,自不致与周孔入世之名教说有所触碍。故渊明之为人实外儒而内道,舍释迦而宗天师者也。
从陶渊明看汪曾祺,那种既入世又超脱的姿态,很难说不是“外儒内道”。但正因为存在这样一条“自然”与“名教”的妥协之路,汪曾祺对儒家思想便可以有选择的接受。这倒比他者有更大的自由。

然而,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汪曾祺内心是否也曾有某种使命感和责任意志的冲动呢?这是一个很难讨论而又很值得想一想的问题。汪曾祺在谈到自己创作时一再说,他对自己写作的要求是“有益于世道人心”。这是作为一个作家的责任感来说的,其实并不能代替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知识分子的基本责任和应对现实负有的使命。在近百年来中国的历史状态下,知识分子的责任意志似乎比以往任何时期更显示出它的重要。试想,在鲁迅和“五四”前贤那种“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壮烈情怀面前,在当今中国众多有识之士为“球籍”而忧虑而疾呼的时刻,汪曾祺那种恬淡之境,是不是跟整个时代精神有些不协调呢?提出这一问题同时,你可以想到(说不定已经想到了)林语堂、梁实秋、“第三种人”,想到汪曾祺极其推崇的老师沈从文,等等;想到革命文学家对他们的批判……
但是,这事情还可以从另一端来作想:汪曾祺这种超脱的自由意志是否本身也含有某种深刻的责任意志呢?
也许,往深里追究,我们发现自己缺少的还是真正的自由意志。返视中国近世以来知识分子的忧国忧民,其结果是什么呢?诚然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的复兴与发展,但是到头来知识分子还须对自身发生忧虑。事实上,孤立地强调责任意志很容易被导入对自由意志的压抑。而情况一旦如此,知识分子产生自我忧患的时刻,维护自由意志又不得不作为一种责任提出。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命运怪圈的形成,固然有着种种外在的复杂原因,但不能说没有他们自身的问题。比如,将责任意志与自由意志作对立观的思想格局,在中国实在是由来已久。古人所谓“君子之道,或出或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便已规定了读书人的行为只能偏执一端。而且,他们也自觉地以圣命(乱世或听从“天意”)的用舍来决定自己的生命形态。可见,中国文人的责任意志从来就是以牺牲自由意志为代价的。他们从来都很谦卑地把自己摆到社会客体的位置上。
陈寅恪揭示的那条“自然”与“名教”妥协之路,实际上很少为中国知识分子所领会。那倒是一条可以自己去走的路。陶渊明就是以儒道精神的融合获得入世的自由。用现在的话来说,他有了主体性。
那么,汪曾祺呢?也许,他不需要从“道理”上接受这一点:捍卫自由意志也就是捍卫责任意志。
三
个性逃避和人格的超越,一方面是回到自我,同时也是回到真实的生活世界。在汪曾祺的艺术思想中,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就是从人的基本生存状态上重观人生。这一命题体现了作家的人格意识与艺术思维的同一。
作为一种价值取向,汪曾祺的回归无疑具有“反文化”意义。尽管他采取超脱的而不是对抗的姿态,但这其中却有着更深刻的否定。他以超脱的姿态入世,那种意在回到直接经验世界的努力,要摆脱的正是某种意识形态障碍——由不同时期意识形态层累地造成的文化堆积物。
具体说到艺术思维,汪曾祺的“反文化”意向也同样显示出返朴归真的目标感。他很干脆地说:“小说是谈生活,不是编故事。”(《<桥边小说三篇>后记》)他把自己的创作作为对“小说”这个概念的一次冲决。将“生活”与“故事”作如此对立观,也可以说是一种“反技术”态度。
如果用技术的观点看,《晚翠文谈》这本书里有些说法很可以怀疑。反对编故事是他一再讲到的,他还表示不喜欢那种“太像小说的小说”(即故事性很强的小说)。说到结构,他认为应当“随便”(又说是“苦心经营的随便”)。当然,这些都很难凿实论之。结构精巧、故事性强的小说未必都属下乘,实际上这样的作品好的也不少。但是,汪曾祺并不从技术上讨论这些问题。他说的“随便”,他喜欢的那种“起止自在”的笔墨,都是跳出了技术范畴来说的。他说喜不喜欢,实在是一种情趣或态度。情趣和态度不是一种学说,你只能考虑是否理解、认同,而无法与之纠缠。
汪曾祺不喜欢编故事,是他自己不善此道么,好像不是。像前边提到的《复仇》,故事性就不差。细看他的作品,许多叙述关系的开阖中都隐伏着可以推衍、发展的故事线索。如《晚饭后的故事》中郭庆春一生的坎坷与机遇,如《八千岁》中米店老板的惨淡营生,如《五四海的黄昏》中的英雄美人……等等,想想都不难使之跌宕、流转起来,却都被撂下了。汪曾祺自己是搞戏曲的,显然知道故事该怎么编。他反对编故事的理由没有多说,似乎就认为它跟生活是一种对立关系。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美学问题。
许多人不会赞同汪曾祺。这里不光那些瞧不着热闹就觉得不过瘾的,也包括一些正在“叙事学”、“语言学”和米歇尔·富科指导下从事创作和研究的实验派作家、评论家。抽象说来,谁也不认为小说就该跟生活拧着来。但由于对生活本身的理解或感受不同,以及对文学与生活之审美关系上产生的差异,使各人在这上面看法很不一样。喜欢故事的人,实际上认为生活是按照某种逻辑关系发展的。比如,在巴尔扎克笔下,拉斯蒂涅这种贫寒的外省青年之所以能踏入巴黎的上流社会,主观上因为他有出人头地的欲望,也有些能耐;客观上他凑巧碰上一些用得着的关系。这种逻辑程序很容易输入到别处,如进入到中国革命文学就成为:某人苦大仇深,主观上有一定的革命意识,客观上正好碰上赵大叔那样的革命者,于是就投奔八路。听起来也合情合理,汪曾祺不能说这里缺乏可能性。但是,这种合乎逻辑的可能性显然存在于更多的不可能之中。巴尔扎克的做法是把那些不可能的因素都剔除了。当然这需要一种技术。这样一来,逻辑关系显然就明晰了,故事就得以进展。用现代“叙事学”眼光看,这未免太简单,技术上也嫌粗糙。现在,一些懂得“叙事学”的小说家也主张小说回到故事上去,但不是主张重新来写巴尔扎克那种偶然因素太强的故事。他们认为,现代小说应当建立在更复杂的逻辑关系上。
现代哲学、心理学、语言学以及其他多种学问的发展,使一切有头脑的人都懂得事物的因果逻辑决不会是一对一的关系。脑子里只要有了“格式塔”、“熵”定律一类名堂,哪怕是一知半解地听说过那回事儿,你就不会把任何一桩小事看得太简单。那都是可以大做文章的。譬如,一个人离家出走,你可以找出十七八条导致这一事件的原因,也可以推测出随即而来可能出现的三十六种情况。一切因果关系背后都可能埋伏着其他因果关系,而真正原因恐怕还不在其中。现在一些被称作实验小说的故事,往往就在这种迷宫般的逻辑关系中展开。如果说,巴尔扎克的故事只是认定一种可能性,那么如今这些讲故事的小说却尽量搜罗一切可能性,把一切变故都考虑在内。当然,这种扑朔迷离、关系复杂而又暖昧不清的故事,读起来就像摆弄电脑似的。它跟巴尔扎克处于相反的一端。可是,这种新故事跟巴尔扎克的老故事却有着基本相同的一面,它们都把小说中的生活作为一种技术构成。也许,故事这东西本义就是将生活素材(或别的什么材料,反正都可以看作“代码”)按一定逻辑关系加以编配。从技术上看,现在的实验小说家的确比巴尔扎克高明得多,当然这不等于说他们要比巴尔扎克伟大。在文学中,最重要的不是逻辑操作。
汪曾祺反对小说的技术化倾向,主要是反对那种虚拟逻辑。
他说,“我主张按照生活本身的形式来结构作品。”(《小说创作随谈》)这句话可以看作现实主义口号,但决不是一句肤浅的口号。什么叫“生活本身的形式”呢,这提法倒也有点“格式塔”的意思。你可以说吃饭、睡觉、上街逛商店、玩蛐蛐、听形势报告、倒卖国库券、给单位头头上眼药……都是“生活本身的形式”。生活中一桩事跟另一桩事之间恐怕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它们就这么存在着。当然,你可以去发掘它们背后的深层结构,但那样找到的东西就不是它原来的形式了。就像阿Q即便能证明自己姓赵,而且也即便从姓氏学上证明了天下姓赵的本是一家,也不等于他和赵太爷的实际关系。一个人玩蛐蛐的时候可能会记起童年生活的某些片断——这作为一个故事来写写倒也不错,如果硬要在这里做一些技术处理,比如这样叙说:此人当时玩的不是蛐蛐,而是蚂蚱;不过那只不幸的蚂蚱倒底是不是蚂蚱也还难说,因为历史不可能被复述……按这个思路下来,逻辑上当然没有问题,而且评论家也会欣喜地发现一只蚂蚱颠覆了一个世界;但是,这跟人们的经验相去太远,人们有理由怀疑这是不是生活。

所谓“生活本身的形式”,是自然的,实在的,直观的。它是先于语言逻辑的存在。它不同于“许多年之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百年孤独》这句著名的开头语,是用语言编织的一种现实。它启发了许多作家的想象力,甚而诱使人们产生更为大胆的想入非非。如今,当这些小说家将想象力驰骋于逻辑世界的时候,汪曾祺依然留在自己的经验世界。他知道技术将会带来什么。
汪曾祺老人坚守一个古老的戒条:“修辞立其诚。”
一九八九年五月杭州翠苑
(本文原刊于《读书》1989年第9期)

【作者简介】:
李庆西,1951年出生于大连,1982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中文系,现居杭州。曾为浙江文艺出版社编辑,现任上海《书城》杂志执行编委。从事文学创作与研究四十年,著有小说《人间笔记》《不二法门》《大风歌》等,评论与随笔《文学的当代性》《话语之径》《三国如何演义》等。
主编:朱生坚
编辑:张晴柔
运维:任洁
制作:蓝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