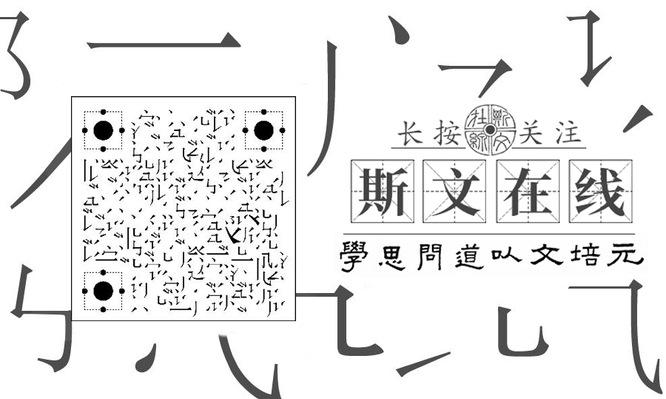伦敦的历史与泰晤士河相伴相生。河岸边错落的码头、工厂、商业区里既萦绕着啤酒花和橡木桶的醇厚香味,也有机器隆隆间飘过的焦烟。人类文明在泰晤士河边留下璀璨的文化艺术,也留下历史的伤痕和阴霾。彼得·阿克罗伊德是土生土长的伦敦人,他的《泰晤士:大河大城》将泰晤士河的潮起潮落放置在伦敦乃至整个西方文明发展的进程中加以审视,经过任明老师细致的考证和翻译,泰晤士河背后“英格兰的尺度、一种美学的和谐”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该书以追溯河流历史开篇,将泰晤士河的寓言娓娓道来,和读者共同见证河流的诞生和奔涌。泰晤士河作为“神圣之河”承载了诸多传说,人们赋予其宗教意义;与此同时,作为城市贸易的重要集散地,泰晤士河又与伦敦商业的运营和工业的发展密不可分,是名副其实的“贸易之河”。接着,围绕河流而生的文化艺术在书中的各节中次第展开,泰晤士河的歌声在“乌鸦石”和“伦敦石”想象中相连的直线处停歇下来,之后便奔向了茫茫来日。
泰晤士河,不是只属于伦敦人的镜子和寓言。现节录《泰晤士:大河大城》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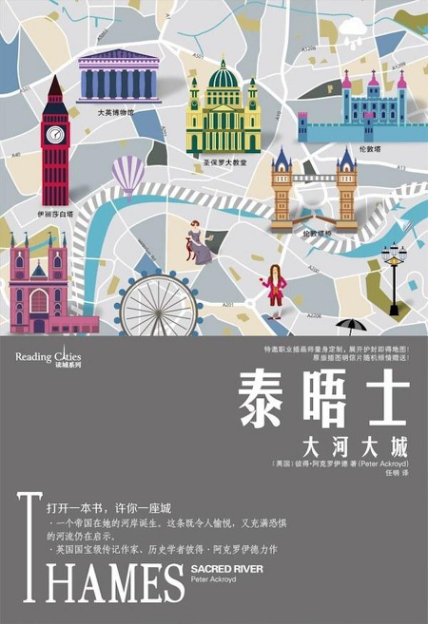
《泰晤士:大河大城》
[英]彼得·阿克罗伊德/著,任明/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
“银色的泰晤士河”
在《不列颠全岛游记》(1724)这本书中,丹尼尔·笛福计算得出,任意一天在泰晤士河上都有2000艘左右的船只。但他的主要兴趣在这条河所能产生的“利润”、或者说是“收入”上。对他来说,“银色的泰晤士河”确实是“银色的”——是流水般的钱币穿过伦敦的心脏。泰晤士河一直是一条贸易的河流。它的潮汐所及,从诺尔到伦敦及其郊区,一直都在努力工作。泰晤士河浸染着汗水、劳作、贪婪、贫穷和泪水。它的船坞、码头和工厂一度是帝国的宏大机器,但它重商主义的历史要比那久远得多。
12世纪时它已是一个古老的港口。有关那个世纪有一些现存的诗句,作者是威廉·费兹史蒂芬(William Fitzstephen),在他有关托马斯·贝克特的传记《圣托马斯的一生》一书的前言中,描写了商人从海上所带来的商品与财富:
来自阿拉伯的金子,赛伯伊的调料及香料,
塞西亚的锋利武器及
来自巴比伦的富饶土地上的棕榈油,
尼罗河的珍贵宝石,
挪威的温暖毛皮,俄罗斯的昂贵貂皮,
塞拉的各式服装,还有高卢的美酒,
都被送到这里来了。
当时已经有了装卸小麦、黑麦、酒、亚麻、大麻及亚麻布料的码头。13世纪时有一个靠近伦敦塔的码头,被称作“大船码头”——因为每年威尼斯商人来伦敦时,都要将他们的大木船停在这里,由一队弓箭手保护着。当时英国最重要的出口货物——也是被装上威尼斯人的大木船,以交换糖、香料及丝绸服装的——是生羊毛。到了14世纪,据估计每年有十万麻袋的羊毛被运往海外。14和15世纪时,贸易活动已经如此频繁,在沙德维尔、罗瑟海兹和德特福德都建了一些主要的造船及修船中心——它们在那里运作了400年。随后的16世纪,位于布莱克沃尔的大造船厂也建成了。这些码头的出现,意味着河两岸将随之迎来箍桶匠、修帆工等手艺人,他们将加入搬运工及各种劳工的行列,直接从泰晤士河获得赖以为生的收入。图利街(Tooley Street)那里住着做饼干的点心师和商店发货人,沃平住着船具商,莱姆豪斯住着颇有名气的制绳匠。其他的河流贸易在16世纪以后开始兴旺起来。都德王朝时期(Tudor),火药在罗瑟海兹的磨坊工厂里生产,后来搬到格林尼治和伍尔维奇的河边进行生产。大炮和铅弹也是在泰晤士河边制造的。

泰晤士河上的船夫
17世纪时,有人宣称,“在海上航行的最伟大的船来到伦敦,在其最中心的地方卸货”;这些船只,“或者带来货物,或者带走货物,都是这个世界所能给伦敦、或者伦敦所能给这个世界的,最好的商品”。商业活动总是很繁荣。1606年,詹姆士一世赐予伦敦金融城政府向所有沿河而来的货物,如煤、谷物、盐、苹果、梨、李子等征税的权力。三年后,这一权力被扩展到油、啤酒花、肥皂、黄油和芝士上。大约过了七年,又颁布了第三项法令:所有的煤都要被卸在法定码头。当时“尽人皆知”,泰晤士河对维持伦敦的生活是如此“方便、必要且实用”。确实,17世纪末期,伦敦的码头已在处理英国80%的出口贸易、69%的进口贸易。一位外国旅客——《英格兰之旅》(Travels in England,1669)一书的作者马格洛蒂公爵(Count Magalotti)——观察到有1400艘大船停在伦敦桥和格里夫森德(Gravesend)之间,“此外还有其他各种较小的船,几乎数不清,它们不停地来来去去,覆盖了整个河面。”有人告诉他,“有超过60万人睡在河上”——这应该是当时欧洲住在河上人口的最高数字了。
……
泰晤士河所进行的贸易活动改变了其河岸的外观。达勒姆大厦(Durham House)被推倒了,代之以货币交易所及拱廊商店。索尔斯伯里大厦(Salisbury House)被拆除了,土地被用作新的住宅开发。阿伦德尔大厦(Arundel House)也是同样的命运。埃塞克斯伯爵的儿子罗伯特·德弗罗(Robert Devereux)名下的埃塞克斯大厦(Essex House),1674年被地产投机商尼可拉斯·巴本(Nicholas Barbon)买下后,大部分被拆掉了,拆下来的石头被用在巴本在原地所建的住宅上。巴本利用了伦敦大火后人们对“标准化住宅”的需求。在他的直接影响下,斯特兰德大街和泰晤士河之间形成了由狭窄的街道与住宅所构成的网络,偶有小餐馆或客栈出现。河岸自身也为了利润与商业的需要而进行了重建。在过去一直伸展到河边的贵族花园的土地上,建起了供酿酒商和木材商人使用的码头和防波堤。这是河流生活发生改变的信号。

1666年9月的伦敦大火,泰晤士河边一家面包房的火星引燃了周边仓库和商店的易燃品,火灾足足肆虐了4天。
一位外国观察者,J.H.梅斯特(J.H. Meister)在《信件》(Letters,1791)中写道,这里的港口已经成为“令所有人既困惑又崇拜的对象”。他同时极力奉劝旅行者“乘船顺泰晤士河而下,观看这条高贵的河流承载着上千艘上千艘的船……然后你会承认这是你从未体验过的、由人类的勤勉与劳作而带来的高贵而愉悦的感受。”
如果说十八世纪是进一步扩大化、并且需要大量投资的贸易时期,那么伦敦第一份报纸在此时出现,就不是一种巧合。《每日新闻》(The Daily Courant)创办于1702年,从一开始,这份报纸的目的就是为城里的商人提供海外贸易新闻——以及有可能影响贸易的各种事件。办报地点所在的弗利特街,离河很近。成立于1734年的《劳埃德船舶日报》(Lloyds List),主要关注驶入伦敦及其他地区的船只动态。成立于1785年的《每日环球记事报》(The Daily Universal Register,现在变身为《泰晤士报》),正像其名字所暗示的那样,主要是对海外新闻的文摘。
……
泰晤士河也打造了其他商业活动。沿河两岸建起了磨坊厂及其他工厂,还有声名狼藉、建在远离人口中心但能够就近使用泰晤士河奔腾的能量(及排水口)的“恶臭产业”(‘stink industries’)。在兰贝斯和富汉姆那里有各种陶器工坊,在切尔西、鲍(Bow)和莱姆豪斯有瓷器工厂,在沃克斯豪尔和萨瑟克有玻璃厂,在沙德维尔和德特福德有油漆、墨水和染料加工厂,在拉特克利夫(Ratcliffe)和白教堂(Whitechapel)有炼糖厂。伯蒙德塞的制皮业与酿醋技术很出名,两者都是气味难闻的产业,使得当地直到20世纪初期还有着不佳的声誉。当然还有酿酒厂——泰晤士河最古老的商业活动之一。杜松子酒和啤酒制造商在皮姆利科(Pimlico)和萨瑟克可以找到,在罗瑟海兹、兰贝斯、莱姆豪斯、麦尔安德(Mile End)和更上游的汪兹沃斯(Wandsworth)、奇思威客(Chiswick)和毛特莱克(Mortlake)都有酿酒厂,啤酒花交易所(The Hop Exchange)建在萨瑟克那里,该建筑现在仍能看到。
载着啤酒花的船,加入了过去5个世纪以来一直从英国东北角往伦敦运煤的驳船,这些煤来自海上。这些驳船就像大船一样宽敞,很多都能容纳200吨的货物。再一次借用汤姆森的说法,“煤烟熏黑的大船缓慢地驶来。”煤实际上是泰晤士河上最重要的商品。在任何一个时刻,都有700艘左右运煤船往来于泰晤士河上,为上百万户人家提供燃料。伦敦大火之后,是煤炭进口所缴的税为伦敦建新教堂提供了资金,因此实际上是河流贸易承担起了伦敦城的建设与发展。煤灰形成永久的云层,悬浮在港口上方,这是城市的依赖性的一个肉眼可见的象征。
“有关劳作与苦难的梦”
泰晤士河的奇观之一是其码头系统。伦敦第一座专门为货物而建的码头——布兰斯维克船坞(the Brunswick Dock),落成于1789年。其旁边建了一座桅杆厂,约有120英尺(36.5米)高,多年以来,都是伦敦海洋贸易与权力的象征,俯瞰并统领着该地区——它也是已经宣称泰晤士河归他们所有的商业之神的“五朔节花柱”。这第一座码头当然与河有着紧密的联系,是在比林斯盖特和昆恩海兹的古老遗址上发展而来的。在罗马人和撒克逊人统治时期,这里都曾经是港口。罗马人的仓库是用石墙和木地板建的,非常坚固,建筑物被分成不同的“单元”,以方便储存。码头附近的土地,几个世纪以来都被称作“罗马地”(‘Romeland’),虽然名字的起源人们并不太清楚。
中世纪时的港口由主要的深水港比林斯盖特和昆恩海兹组成,后来再加上更上游一点的唐盖特(Dowgate)。1170年,德国商人在唐盖特那里为自己建了一座大厦——也可以称作是他们的“居住区”。……当然大多数进入伦敦的船会停在河中间,商品被驳船载到岸边。
后来有一个主要变化改变了港口的性质。费兹史蒂芬表示,12世纪末,将城市与泰晤士河隔开的城墙已经年久失修,变成废墟;这使得紧邻河岸的地区被打开了,新建的拱廊商店和仓库为繁荣的市场创造了条件。在接下来的500年中,这里以没有人能够预料、也无人管束的方式在不断增长。渐渐地,这里的贸易活动发展得需要向下游扩张,离开了那20座被称作“合法船埠”的地方。所谓的“合法船埠”,建于伊莉莎白一世统治时期,位于伦敦桥和伦敦塔楼之间,都在河北岸。船埠(Quays),意味着轮船可以在这里合法地卸货与装货,码头(Wharves),最初是被设计用来从驳船上装卸货物的,但后来也供商船使用。拉特克利夫(Ratcliff)和鲍泼勒(Poplar)变成了新的泊船处,被称作“默许码头”;……伊丽莎白女王时期的另一个禁令是禁止在河边建私宅,以方便泰晤士河供商业目的使用。这体现了“商业”在泰晤士河历史上的主导性。

如今有的伦敦居民区还保留了船坞码头上的大型塔吊
船坞(Docks)基本上是伸入河岸的小型开放港口,每种船都可以使用。第一次提到泰晤士河上的“船坞”——至少是以一种我们所熟悉的样子——是在查尔斯二世统治时期。佩皮斯(Pepys)在他1661年1月15日的日记中记载道,在他坐船去布莱克沃尔时,在那里看到了一个新船坞和一个“放着一艘崭新的、很快要下海的商船”的湿船坞。
……
新船坞所产生的影响是即刻而深远的。船在三四天之内就可以卸完,与之前所需要的一个月时间形成鲜明对比。安全问题成为头等大事,在继续往上游航行之前,所有船的舱口都会在格雷夫森德被钉死或封住。手推车和搬运工都不允许进入这些新港口,以防止偶尔或系统性的偷窃行为发生。货舱里散落的糖甚至也被捡起来,销售所得归货主所有。新船坞的围墙都高达20英尺(6米)。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一只新的警察队伍——英格兰第一支法律意义上的警察队伍——也被组建起来,负责保护河上交通。
……
19世纪时,进口的朗姆酒多得可以让整座城市喝醉。西印度船坞的朗姆码头的一个大桶就可以容纳7800加仑(35450升)的酒。这里有足够的糖可以让泰晤士河变甜,足够的靛蓝染料可以将河染成蓝色。被捆在一起锁在仓库里的,有成本就达1000万英镑的胡椒、成本达2300万英镑的烟草及成本达5100万英镑的茶叶。还有橡胶、咖啡、肉桂、椰枣和各种肉灌头。皇家阿尔伯特船坞的单个冷藏室,就能容纳25万只羊;瑟瑞船坞可以容纳100万吨木料,西印度船坞的存酒处可以容纳近100万加仑(超过450万升)的红酒。
在建了这些船坞以后,伦敦的贸易活动变得更庞大、更有异国情调了。从殖民地进口的小象獠牙与小鸵鸟羽毛;从西伯利亚的冰冻废墟中挖出来的猛犸象的巨大獠牙,也被运到了伦敦的象牙市场;来自鲸鱼肚子里的龙涎香及液体芦荟,被泼在猴子皮上,制成标本。
……
因此伦敦带着它永远的、如光环一样的烟雾,带着灰尘、噪音与气味,在河岸显现。19世纪末,世界上第一座高压电厂在德特福德的泰晤士河边落成,随后在巴特西、富汉姆(Fulham)和班克赛德(Bankside)也建了发电站。还有着其他有关未来世界的代表。1880年,第一批美国产的石油在泰晤士港靠岸,在一艘帆船上寄售,它是后来将要出现在泰晤士河口两岸的大型炼油厂的先锋。

莫奈画中的泰晤士河,有着灰蒙蒙的光晕点染
20世纪初期,人们好像感觉河流上的贸易活动会永远持续,只要大洋与潮水还在。1909年,伦敦港务局(the Port of London Authority)被创建起来管理这一持续进行的工程;……1930年时,伦敦的港口和船坞为10万人提供了工作机会,他们大多数住在泰晤士河的周边地区,负责处理它700英亩(283公顷)河岸帝国中的3500万吨货物。
20世纪刚开始时,泰晤士河沿岸的工业实际上在以一种当时看起来值得警惕的速度在发展着。布兰特福德地区的泰晤士河已经完全工业化了,在兰贝斯、九榆(Nine Elms)、巴特西、万兹沃斯和富汉姆也都有了工厂和磨坊加工厂。在艾尔沃斯(Isleworth)有肥皂厂和橡胶厂,在特丁顿有卷帘制造厂,在汉姆(Ham)有汽车制造厂,在皮姆利科(Pimlico)有锯木场——这里成为木材贸易的中心之一。10万包括码头工人、装卸工、驳船夫和水手在内的劳动大军,全将自己的生计交付给了泰晤士河的潮水。
1931年,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写了一篇题为《伦敦的码头》的散文,描写泰晤士河两岸如何“成排耸立着昏暗、看起来破破烂烂的仓库。它们挤在满是平坦而粘滑的烂泥地面上……桅杆和烟囱后面,是一座凶险而低矮的、由工人住宅组成的城市。前方,吊车和仓库、脚手架和储气罐一起在岸边组成了一副建筑物般的骨架。”对她来说,这是一幅“忧郁阴沉的景象”,而她未能理解贸易的必要性也许能得到人们的谅解。
……
然而在随后的两代人之间,这些全都消失了。在该世纪前50年还无法想象的大型集装箱船获得了发展,货物现在可以直接从船上运到货车上,不需要仓库,而且这些船本身也太大了,现有的码头设施容纳不了。世界上其他地方所出现的大港口、伦敦船坞工人在工作中所受到的限制,这些都加快了结束的进程。船坞开始变得萧条了。东印度船坞在存在了160年之后,于1967年关闭;伦敦船坞和圣凯瑟琳船坞也在两年后关闭了。西印度船坞苟延残喘到1980年,存在了178年——当时泰晤士河的贸易已经衰落到无法挽回的地步。最后一批船坞——皇家维多利亚、皇家阿尔伯特和国王乔治五世——在1981年关闭。到20世纪末,那些船坞全都消失了,消失得好像它们确实只是一场梦一样——存在于泰晤士河两岸的有关劳作与苦难的梦。
“蒸汽是未来,蒸汽是进步”
蒸汽船第一次出现在泰晤士河上是1801年,当时它主要被用来拖拉更大的帆船。第一艘蒸汽渡轮的出现,于1815年1月23日在伦敦报纸上进行了预告:“请周知,新的伦敦蒸汽渡轮‘马杰里号’(Margery)在船长考第斯(Captain Cortis)的率领下,将于23日星期一早上10点钟准时从靠近伦敦桥的沃平古台阶处出发。”它的目的地是格雷夫森德,然后在第二天一早同一时间返回。水手同业公会——可以理解其对成员生计的关心——开始了针对考第斯船长的诉讼活动。然而地球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这种变化。1830年左右,泰晤士河上大约有57艘蒸汽渡轮。它们的到来预告了后来在河面上无所不在的“一日游”的出现。便宜的蒸汽船开始被人们称作“河上公共汽车”。
在使用笔名“博兹”发表的早期散文《河流》(The River,1835)中,年轻的查尔斯·狄更斯描绘了在“蒸汽船码头”,乘客们爬上“格雷夫森德渡轮”或“马尔盖特渡轮”时的混乱场景。他们上错了船,或是找不到舒服的座位,或是行李放错了地方。“拥有季票的长期旅客到下面去用早餐,买了晨报的人让自己沉浸到报纸中去,而以前没有坐过船的人,都在想船和河都是从远处看要更好一些。”到了布莱克沃尔,柳条编的手提篮被打开,为乘客提供油腻腻的三明治及瓶装的白兰地和水。某人拿出随身带的竖琴,开始演奏舞蹈音乐。
……
蒸汽是未来,蒸汽是进步,在为赢得泰晤士河而进行的斗争中,蒸汽将会赢。
然而另一种蒸汽的力量也已经到来了,它将所有有关船只运输的计划都打乱了。1834年,一项野心勃勃的计划——在伦敦、雷丁和布里斯托之间为新发明的火车铺设铁轨的“大西部铁路计划”——被提了出来,担心河流交通的前景的泰晤士河委员们宣称:“所有住在泰晤士河边的人,不论他们是被河的美丽、健康还是实用所吸引,都会为阻止议会通过像大西部铁路这样毫无用处的项目提供帮助。”然而19世纪的所有力量,在它对能量与速度的专注中,在它对发展与创新的追求中,在它对“激动人心”的理解及对“改革”的需求中,正在全速向前进。伦敦与雷丁之间的铁路线在1840年完工,4年后,在伦敦与牛津之间又建成了一条支线;伦敦到温莎及亨利镇之间的铁路线随后也被建了起来。

《雨、蒸汽和速度——大西部铁路》,特纳,1844。“该画作洋溢着一种光辉,色彩与光线都十分灿烂,显示了特纳对这一相对较新的力量的前景,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激动”
特纳的画(《雨、蒸汽与速度——大西部铁路》,1844),在某种程度上是对“速度”的赞歌,而布鲁奈尔的桥位于对“力量”进行展示的中心。该画作洋溢着一种光辉,色彩与光线都十分灿烂,显示了特纳对这一相对较新的力量的前景,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激动。作为艺术家的特纳,其实是在向布鲁奈尔这位深具远见的人致敬。然而这里还缺了某种元素。这幅画的视线是向东,朝向伦敦,伴随着通常被认为是来自城东、由“灰尘”和“疾病”所交织的云雾。在19世纪中期,任何来自“城东”的东西都会被认为是可疑的。在画布一侧,在色彩与光线迸发的区域之外,有人在河里泛舟,附近的田里有一位农民在劳作。这些是一种古老的存在及泰晤士河所养育的古老生活方式的象征——而这一切似乎都即将被铁路所终止。在特纳的画中,有一只野兔从奔驰的火车头所即将开过的路上逃开——代表了“自然世界”从“机械制造”那里撤退。
……
然而在巴扎尔盖特的积极努力下,19世纪才是真正的变革世纪。1863年,议会通过了一项新的法令,以加快他为泰晤士河修建新堤坝的进展。他将打造一个巨大而错综复杂的下水道网络,将垃圾和腐败物运出伦敦,同时在下水道上面,将在河两岸打造宏伟的石头人行道,作为泰晤士河的新景观。这项工作首先从在威斯敏斯特和坦普尔之间建维多利亚堤坝开始,在建造过程中,有约40英亩(16公顷)的河滩被改造。然而巴扎尔盖特只是在辅助一项更为平常的发展过程——在泰晤士河的历史中,从凯尔特人时期到现在,威斯敏斯特那里的河流宽度已经从750码(686米)减少到250码(228.6米)。
维多利亚堤坝很快有了随后建造的阿尔伯特堤坝和切尔西堤坝的陪伴。它是19世纪最大的土木工程之一,包括一个地下铁路系统的建造。在维多利亚堤坝那里,有一座为巴扎尔盖特而建的纪念碑,上面刻着一句带有传奇色彩的话:“他为河流戴上了锁链”。
……
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泰晤士河的角色与地位投射了一道更为暴力的光芒。作为交通要道的泰晤士河,又一次被侵略者作为进入伦敦中心城区的通道。它变成了一条火与血之河,一条比冥河和阴间更为黑暗、更为危险的地狱之河。在它整个历史之中,泰晤士河一直都是一个最具吸引力的目标。1930年代末和1940年代早期,河的两岸是汽车工厂、石化设施、各种工厂与发电站。它包括着“金融城”和“威斯敏斯特”两个世界,政治权力和金融权力联合组成了泰晤士河上的巨大拱门。战争甫一开始,泰晤士河及其两岸就开始实行非常严格的“宵禁令”,但德国轰炸机仍然将磁性水雷扔进了泰晤士河。
1940年9月7日,专门用于对付港口的火弹被扔了下来。所有的船坞和仓库——除了蒂尔伯里那里——都在大火中熊熊燃烧。轮船和驳船都着火了,并且随着潮水危险地朝防波堤和码头漂去。伦敦没有足够的消防员来终止这场“地狱之火”,燃烧的火苗如此明亮,在12英里之外都能清楚看到。沿岸大火产生了另外一个效果——它充当了引导第二天晚上接着赶来的轰炸机的火炬。
9月8日晚上8点30分,入侵者编队来到正在燃烧的河流上空。这里好像不再是泰晤士河,而是来自未知火源的流动的火山岩浆。德国轰炸机瞄准了前一天晚上没有被摧毁的船坞与仓库,火焰与硝烟再一次占领了泰晤士河。河面上覆盖着一层燃烧着的汽油薄膜,辛辣的烟浪从河岸各个角落喷涌而出。朗姆酒燃烧着落在河面上,存放羊毛的仓库变成了燃烧的炉子,石蜡也在熊熊燃烧。伦敦塘变成了火光之湖。兰贝斯和罗瑟海兹这些地方也沐浴在像白天一样明亮的火光之中。
……
然而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晚期和五十年代,因为一些更日常的原因,泰晤士河逐渐关闭了。它的市民不再使用它。十九世纪的度假者、邮轮旅行者及通勤者都消失不见了。它变成了一条沉默的河,人们将其描述成一条“宽阔、白色而空洞的通道”。人们对它失去兴趣与关注的原因是多样的:有通达性的问题——一些港口和台阶现在都已经弃置不用了;有因为忽视而变得死气沉沉的问题——当然还有令人愤怒的下水道问题。南岸已经成为“绝望与耻辱的代名词”。问题的关键是没有人真正关注有关泰晤士河的问题。伦敦人中很少有人知道这一位于城市中间的巨大港口,对船坞的性质与范围有所了解的人就更少了。泰晤士河已经变成了一个不为人知的领域。伦敦朝它背过身去。

1940年代二战期间,英国在泰晤士河上布置的炮台
……
反过来说,这里有了新的复苏形式。从1981年7月到1998年3月之间,一个名叫“伦敦港区发展公司”(London Docklands Development Corporation)的机构成立,致力于之前被船坞所覆盖的8平方英里河岸空间的改造与更新。该地区包括萨瑟克、陶尔哈姆莱兹和纽汉姆。一度遍布矮树与野草、由旧船坞摇摇欲坠的墙或是有倒钩的铁丝网所守卫的的荒地,上面建起了新的建筑与住宅。港区一度在物理空间上与伦敦其他地区是隔开的;对大多数市民来说,这是一个未知领域。新开发者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采用新的公共交通方式,将泰晤士河与伦敦其他地区连起来。……人们通常认为“很不幸”的狗岛,被重新规划为“创业区”,以吸引投资者与新企业。泰晤士河似乎得到了来自城市生命力与能量的“充电”。
“发展”,以一种有时是“偶然”的姿态在向前推进,更多地服从于“利润”原则而不是公共利益,但这就是“城市”的故事,这也是贯穿泰晤士河整个历史的故事。
……
“河景”又一次变得有趣了。刚开始时,“需求”跟不上“供给”,在仓库之间经过翻新的狭窄街道上——过去是搬运工和推着手推车送货的男孩们工作的地方——现在更多的是房地产中介,而不是商店。当地居民的利益常常被忽视;他们要求能更多地参与到各种发展计划中来;他们当然也要求自己最关注的一些问题——譬如工作岗位与住宅等——能够得到解决。一项有关住宅与翻修建设的长期过程开始了,到现在也还没结束。
……
位于南岸的建筑——包括1976年建成的国家剧院(National Theatre)——具有一种人们称之为“流动”的韵律。国家剧院的建筑师丹尼斯·拉斯顿(Denys Lasdun)说他想打造一种感觉,“观众——像河流的潮水一样——流入观众席,然后,潮水退潮,观众们退场进入那些由阳台组成的小空间——就像潮水涌入溪流。”
“你好!风与雨”
……
洪水是泰晤士河永远要面对的状况。泰晤士河第一次有记载的洪水是在公元9年——虽然还有无数的洪水与河水泛滥在我们祖先有记载的历史中无法找到。随后在公元38年的一场大洪水中,死亡人数被认为在一万人左右。公元50年记载了另一场洪水泛滥。考古学家发现在公元360年左右,伦敦及其周围地区的人类活动减少了,有证据显示,这10年中人类活动衰减是大量洪水频繁爆发的结果。

泰晤士河两旁不断扩张的建筑使河道变得狭窄
这是一个涨潮与不涨潮的泰晤士河段都不断被侵袭的故事。1332年,塔普洛(Taplow)完全被洪水摧毁了;1768年,雷丁那里的河水在半小时之内就升高了2英尺;1774年,亨利镇的桥被洪水冲走了;1821年,泰晤士河旁边的道路因洪水变得无法通行;1841年,伊顿的商业大街被淹在水里了;1852年和1874年的大洪水都发生在11月17日。泰晤士河非涨潮河段发生的最大一次洪水是在1894年,当时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下了1/3的年降水量。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泰晤士河容纳不了那么多的水,因此多出来的水会到处乱流,并在所到之处制造灾难与混乱。1947年,彻特西以下的河水宽达3英里,梅登海德被淹没在水下6英尺(1.8米)。事实上,梅登海德周围地区一直都很容易受到洪水影响;为减轻这种影响,本世纪初,人们在那里修了一条运河。
……
令人好奇的是,洪水的发生好像永远都是出人意料的。洪水会被人们遗忘,直到再一次发生。现在大家有一种奇怪的假设,认为泰晤士大坝(the Thames Barrier)将会在某种程度上防止河水继续造成侵害。除了大坝下游的河段及河口区的数英里地区没办法受到大坝保护这一明显事实之外,大坝对泰晤士河非潮汐河段的洪水也并不具有防护效果——而该河段眼下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同样容易受到洪水袭击。2003年年初,该河段有550座房屋被洪水淹没;梅普尔德汉姆水闸(Mapledurham Lock)的水位仅比1947年发生灾难性大洪水时低12英寸。
让我们试想一下,特丁顿堰坝(Teddington Weir)平均每天的流水量为4500加仑,每年有一两次可以达到日流水量55亿加仑——这被认为是“满岸”状态或是处于洪水爆发的边缘。1947年洪水爆发时,特丁顿堰坝的日流水量急升到135.72亿加仑;1968年,日均流水量达到11404加仑;1988年,达到7650加仑。这些巨大的水量代表了泰晤士河所拥有的力量及潜在的破坏力。
然而最恶劣的洪水还是发生在涨潮河段。在那里,极端天气状况与潮水的突涨可以联合起来形成巨大的水墙。1090年,伦敦桥被骚动的泰晤士河摧毁了;9年后,《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载道,“圣马丁节当天,海浪涨得如此之高、造成如此大的损害,在人们的记忆中,前所未有。”这场发生在1099年的洪水,有另外一个意料之外的后果:古德温伯爵(Earl Goodwin)的一处房产被决堤的泰晤士河水淹没,此后再也没能恢复干燥——那里变成了一处沙丘,被称作“古德温沙丘”,现在还是渔夫和水手所担心的地方。1236年的洪水规模是如此之大,据斯托所说,沃尔维奇那里“完全变成了一片汪洋”,平底货船被冲到了威斯敏斯特大厅中央。
……

如今的泰晤士水闸夜景
每个世纪都有导致灾难的“怪潮”发生。1641年2月4日,据当时一个小册子记载,“在一个半小时之内,在伦敦桥那里发生了两波巨浪,后一道浪来得非常凶猛和声势巨大”,甚至连水手都“感到害怕”。在这两道反常的巨浪之间,泰晤士河有一个半小时停止了移动,看起来就好像“睡着了,或者是死了”;然后第二道浪开始“以一种愤怒的姿态翻滚、咆哮和冒泡,令所有目睹这一切的人都感到恐惧”;这是“一种奇观——连最年长的人也从未看过或听说过这样的事。”然而这个记载稍微有点夸张,因为18年前——1623年1月19日——就有一次,在5个小时内接连发生了三波巨浪。1663年12月7日,佩皮斯在其日记中写道,“昨晚泰晤士河发生了一次英格兰所能记得的最大潮水,怀特霍尔全部被淹了。”沿泰晤士河曾有一道著名的“缺口”,就在达格纳姆村附近,这道口子是在1707年被撕开的,有100英尺(30米)长,曾经有长达7年的时间就那样敞开着。1716年9月14日,一股巨大而持久的风阻止了洪潮抵达其目的地,泰晤士河的水变得非常浅,根据斯特莱普(Strype)对斯托的《对伦敦与威斯敏斯特的调查》(Survey of London and Westminster,1720)的修订本记载,“数千人步行过河,既在桥上也在桥下。”
1762年,泰晤士河的河水涨得如此之高,“人们不记得还有同样的事发生过”。在不到五个小时的时间里,河水涨了12英尺(3.6米),很多人被淹死在城市的主干道上。19世纪有六次重大洪水——1809、1823、1849、1852、1877和1894年——导致了生命与财产的巨大损失。当时住在河边的人最熟悉的喊声是“洪水来了!”1881年,巨浪在威斯敏斯特那里达到了17英尺6英寸,据《泰晤士报》报道,“人们看到了最令人心碎的景象。”
……
所有灾难中破坏力最大的一次,发生在1953年1月31日的夜里,来自北海的大潮淹没了泰晤士河口。那是一个寒冷的夜晚,狂风咆哮,凌晨2点钟时,一个巨大的“水壁”形成了,并且稳步向前推进。据报道,有三百多人死亡,2.4万处住宅被摧毁,16万英亩的田地被淹,12座煤气罐和2座供电厂被洪水毁坏;坎维岛被淹,很多岛民撤退了,但还是有83人失去了生命。这是自“二战”以来最大的一次灾难。如果堤岸没有被摧毁、河水没有溢出到埃塞克斯和肯特的农田,灾难就会抵达伦敦,导致不可想象的严重后果。
这样高的潮水与水位所带来的威胁,意味着泰晤士河对伦敦的危险也在增加。伦敦有60平方英里左右(155平方公里)的土地位于高潮位线以下;在高潮位线时,城市的某些部分可能会被淹没在10英尺(3米)深的水下。如此大的水量冲进地铁系统的话,伦敦的交通将会瘫痪很长时间,生命丧失的可能性也非常大。
(节选自《泰晤士:大河大城》,[英]彼得·阿克罗伊德/著,任明/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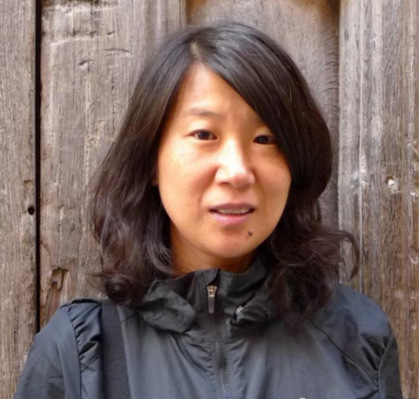
【译者简介】:
任明,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电影研究、城市文化研究;出版电影研究专著《光影叙事与时代风云——上海城市电影60年变迁(1949-2009)》(2014)、译著《泰晤士:大河大城》(2020),偶有电影评论、艺术评论散见于《解放日报》、《文汇报》、香港《文汇报》、《新民晚报》、《21世纪经济报道》、《上海文化》、《上海戏剧》等报刊杂志。
主编:朱生坚
编辑:曹晓华
运维:任洁
制作:蓝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