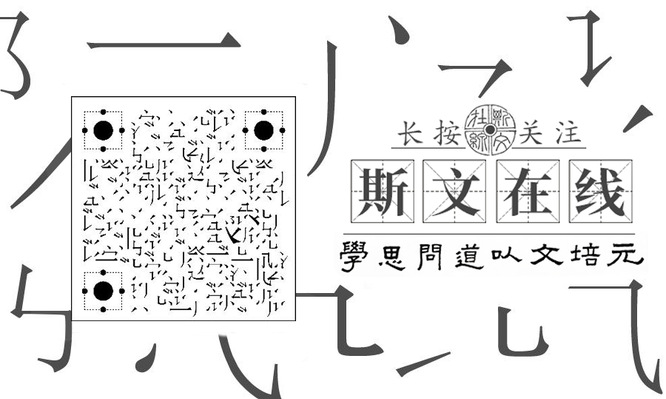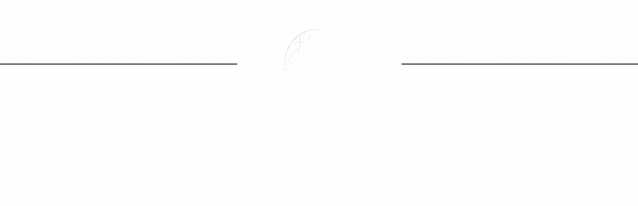
李洱为何要从文人的角度写这个时代?从历史上看,大凡时代转型比较快的时候,士人反应最大,“莺啼如有泪,为湿最高花”,李商隐这首感伤身世的诗在小说中出现多次。鲁迅也是从文人生活来考察魏晋时代,他所谓的“大时代”即指“可由此生,也可由此死”的时代转折点。从魏到晋、元到明,从晚明、晚清再到民国,从《世说新语》到《围城》,知识分子因时代急转,罹乱世,而产生迷惘和种种怪行。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90年代的市场经济转型力度空前,《应物兄》以大学为中心,以济大兴办儒学院为线索,以别致的形式,画出了这个时代的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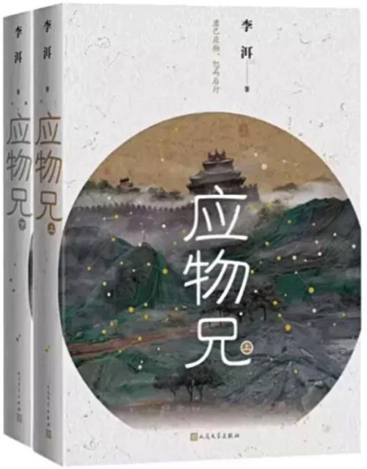
李洱《应物兄》
李洱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曾说:“1980年代是个信奉进化论的时代,而1990年代则是另一个逻辑起点。90年代文学的重要性,还没有被充分发现。它是对文学史、精神史都特别重要的转折。在90年代写作,沿用以前的语言、句式、范式显然不行,很多东西都失效了,需要有新的一种语言和视角。”李洱野心很大,他要站在一个新的认识起点,造出新句子,状写新症候——用新的语言、句式和视角。“应物”何以成了问题?这个世界的词与物的链条断裂了,词语泡沫膨胀得越来越高,正如小说第90节中说,当代社会出现了“麦克风现象”,在麦克风前,你所说的就不是你想说的话了。作家试图带领读者穿越词语幽暗的隧道,回到词和物有本真性亲密联系的世界,正因为考掘一个时代的“关键词”可以看出社会实践历史的浓缩,时代的总体症候,可以凸显其中蕴含的政治谋略、统治策略,雷蒙·威廉斯才会对词的“肌质”和“意蕴”有着凯尔特人式的感受力。
小说的及物性首先表现为词的及物性。文学高于思想和历史的地方在于,它能链接着社会的最下层,因此文学是体现地方民歌小调的“风”。《诗经》中很多诗以花鸟草和食物命名,其中有古意,这些实词来自大自然,所以简短有力,它们链接着的自然人事,牵一发动全身,这就是及物性。比如小说写“吃什么”就是一个唯物主义的命题,鲁迅研究魏晋思想,就从魏晋文人的吃药和喝酒着手。《应物兄》中济州的地方食物、烹饪方法介绍了很多,如“套五宝”、“杂碎汤”、鱼咬羊等,也直接作为章节的题目。好的小说就在于它通过看得见物质形态,给看不见的思想赋形。在《应物兄》91节“譬如”一节以像喻理,小说借小说人物之口,说明一个时代喝酒容器的变化(觚),如何体现了时代的形制、礼制变化。因此观一个时代的物,就能很好把握这个时代的心灵。
李洱又说:好的小说是去探溯一个神秘的声音:就像走进密林,听见树叶的声音,没有人知道那声音来自哪里。读懂了树叶的声音和密林中鸟语,你就记起了芝麻开门的暗语。“像尼采那样”(李洱),走出破碎的现代世界,回归词语诞生的大地。《应物兄》以“物”为方法,带领读者重新去发现和倾听世界:“京都郊外的山势”,“郁金香花丛中的秋风”“海上风雨中的船帆”,“苍鹭在黑夜中飞过时的叫声”,认真听一次,让物归其本位,让一砖一石重新聚拢,重建语言秩序和世界秩序,回归美好的真理性世界。

如何来写当代分崩离析的现实?如何汇聚现代社会碎片化的经验?作家不仅要回答“为什么要写作”,作家还必须回答如何写作。《应物兄》格式的特别之处很多,首先在于章节安排,看似随意,每小节独立成篇,总体组合成一个魔方。每小节的标题的特点,上文已经略有交代,标题都用开头一个字词或短语。这有点戏仿了《论语》的章节安排模式,但又有差异。在90节中,作者有意“考证”了《论语》各章节编辑顺序,也为我们的解读小说留下了蛛丝马迹。作者借小说中人物之口说明小说之道:一部真正的书,常常没有首页,像《论语》断章残简,后人整理编纂,标题只能如此。如此可以理解《应物兄》的开头其实不是开头,它没有描写,没有引子,像飞来之石,直接切入现实画面。那么第101节也不是结尾,它只是从几百节的人间喜剧中截取而来。这样的开头也隐喻着开端的不可能性:90年代,从哪里写起?
据说《应物兄》这本书本来应叫《应物》,作者和编辑之间的叙事也参与到这个“随意”中,小说开始于“应物兄”三个字,按本书的凡例,似乎两种命名都可行,《应物兄》则将一个待人接物的动宾词组“应物”,变成一个待人接物的人,一个字的增加改变了小说的形式,将 “虚己应物,恕而后行”、“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的抽象道理变成为演化故事的“这一个”。鲁迅写《阿Q正传》时,开头便是写作的焦虑,无法给小说起名,苦于不能名正言顺地为阿Q作传,旧有的称呼都无法指认阿Q,传统史学分类也无法纳入这个“新”人,新的事物已经出现,新的名称还没产生,名实之间无法对应,鲁迅以此深刻质疑了现有世界意义链条的断裂。我们可以在语文学的意义上来思考《应物兄》,小说章、节命名的独特,还体现在,它大致采取了辞典编撰的方式来归档、分类各个小故事,这是不得已为之吗?但这是一本奇特的辞书,它的词条上有名词,也有短语。这本书上下两卷共101节,可以看成101个词条,通过百科全书式的编纂方法,李洱试图将这个时代的碎片缝合起来。全书开端没有传统小说的章回,也没有现代长篇小说的目录。小说最初发表在《收获》上分了章,但成书时去掉了试图划分结构的“章”,词典叙事的方式是述说体,作家力图去掉对小说世界的主观分断,保留事件客观性。这种独特的编纂方式,是对传统写作的挑战,也质疑了传统小说形式中的章回名目。
李洱通过济大儒学院的故事,试图让一些重要的词和物的关系水落石出,并且厘清词和物背后的人和人的关系。《应物兄》词典的及物性首先体现在对单个词的知识考古,如狗,小说的对《山海经》、《论语》等传统“字”的溯源更不必说,很多章节都直接出现了词典,如43节解释“儒驴”一名,因此这本小说也是注释最多的小说。《应物兄》的更大的及物性,不仅通过一物还原历史,如考据仁德路的历史。更重要的哪一个物能打开我们记忆的闸门,像普鲁斯特的马德兰小甜饼,勾起我们的情感记忆,70节“墙”的述说中,通过一个不隔音的墙,不仅复原了一个时代的生活方式,还呈现了应物兄情感挫折,以及失败后的坚韧宽恕豁达。

写作是一种世界观,对百科全书来说,新词的出现不仅意味着要修订辞书,更意味着对就有分类和叙事方式的反思和冲击,新词的出现,让传统词条分类方法失效,进而指向一个新的乌托邦世界。79节“Illeism”是一个生创的词,“指第三人称谈论自己的方式”,《应物兄》中好几节的辞条从不同叙事角度写应物兄。看出作家对应物兄作为主语或宾语,作为名词和代词的不满足,他想寻找完全将自我对象化的冷静的叙事方式,有时又对“我们的”应物兄饱含同情。与此相关,89节标题“The Thirdxelf”(第三自我)也是属于未来世界的新词,新到无法用中文表述,这个词代表书写未来人类词典的新文体,一种新的尽力客观的述说物的方式,这是属于未来世界的百科全书,这也是文德能毕生想写的一本“沙之书”,“它能将时间和空间连接,包含知识,故事和诗,同时又是弓手,箭和靶子,互相冲突又彼此和解,聚沙成塔又化渐无形;它是颂歌,挽歌和献词,这将是一部时代百科全书,里面的人既是过客又是香客”(见89节),这是一个出口,能进得去的世界。在语言命名世界,创造世界的意义上,作为百科全书的《应物兄》还没有编写完,我们期待着作家成续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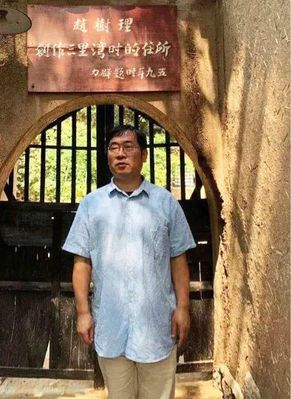
【作者简介】:
孙晓忠,1969年12月生,安徽合肥人,200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
主编:朱生坚
编辑:张晴柔
运维:任洁
制作:蓝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