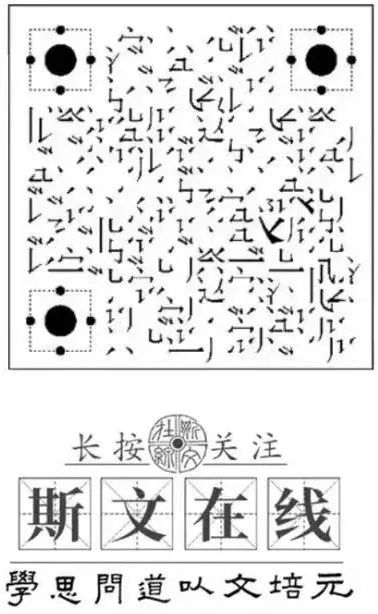城市“创意”从何而来?又将往何处延展?《上海文化》(文化研究版)十月号关于创意城市的圆桌讨论,邀请三位学者,从海派文学、城乡创意产业以及疫情中的全球创意城市等不同角度,分享了“回溯”与“展望”交织中的城市文化思考。“斯文在线”摘录精彩片段,以飨读者。
《“海派”文学之始:仿古即写真的城市创意》
陈建华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
有关海派的源头众说纷纭。从地缘政治与历史传统的角度似乎离不开“老城厢”这一根基,最初的“洋场”就是在城外形成的。上海开埠后不久,传教士以徐家汇的土山湾为基地,引进了新的印刷和西画技术,因此说徐家汇是“海派之源”也有其历史依据,虽然略为夸张,含文创性质,在推进城区文化建设方面很能起激励作用。
其实所谓“起源”意味着历史的断裂,对其追溯不免迷思性质,却自置于某种断崖式危机之中,受一种有所发现的心理驱动,在近代的曙光中捕捉种种新变创意的轨迹。
先来看1871年在《教会新报》上刊登的醒世子《洋场赋》:
华俗薄,洋人入;沪江浊,洋场出。延袤一二十里,不知天日。由城东北而西折,半属洋行。黄浦溶溶,环绕其旁;人杂五方,商通四域;洋货杂货,丝客茶客;相尚繁华,勾心斗角。挤挤焉,攘攘焉,蜂屯蚁聚,真不知其几多数目。煤烟贯地,有火何红?电报行空,不胫何通?曲折冥迷,不辨西东。有得意者,春光融融;其失业者,风雨凄凄。一日之内,一街之中,而兴废不齐。
吴姬绝色,浪子消魂,勾情卖俏,渔色宣淫,朝歌夜弦,无间晨昏。明星荧荧,开烟灯也;片云朵朵,出局票也;娇喉婉转,酒水拳也;妙舌诙谐,茶会套也。彼豪此侠,无非狂也;一朝金尽,犹不自知其误也。昔日何荣,尽态极妍;今日何辱,冷眼加焉。有如此情者,不下万千。
乃祖之收藏,乃父之经营,乃身之精神,几世几年,积聚而成,倚之如山;一旦供挥霍,输来其间。衣服首饰,罗绮金玉,弃掷如遗;伊人视之,意犹不足。
嗟乎!习俗移人,一倡而百和也。彼爱纷奢,而不念其家;奈何入之仅锱铢,用之如泥沙?使沉湎之酒,蠢于骂座之灌夫;珍羞之味,多于墦间之樽俎;鸦片之烟,甚于三餐之啜哺。赌局之胜,哄于三军之部伍;华侈之衣,丽于王侯之服色;淫靡之曲,乐于生旦之歌舞。使千金之躯,极淫佚而不顾;荡子之疾,日益沉痼。烟瘾攻,疮毒举;曾几何时,可怜黄土。
呜呼!杀人者,夫人也,亦财也。殉身者,财也,亦自取也。嗟乎!使夫人各惜其财,则足以保身。吾必谓夫人之财,可由立身而至;富贵而寿考,谁得而杀之也。夫人不暇自哀,而吾人哀之,吾人哀之而不鉴之,将使他人而复哀吾人也。
对于这篇《洋场赋》,若用迄今流行的文学史眼光来衡量,既用古文写成,又是模拟之作,简直毫无价值可言,难怪迄今似未见有所关注。但编者说它“新而隽,奇而警”,的确,虽是仿作,“洋场”却是中国被迫打开国门之后的产物,必新无疑。原作慨叹王朝兴衰,全由“秦”之“独夫”穷奢极欲,残酷奴役天下之人,以致“楚人一炬,可怜焦土”。后作也是对“自作孽,不可活”的道德训诫,但稍加分析,不难发现主体的诡异置换。尽管“洋场”可恶,并无谴责“洋人”之意;笔下的“洋场”方兴未艾,毫无衰亡之迹。虽是仿古之作,却不止是旧瓶装新酒。一开头运用“华”“洋”对照的修辞策略:“华俗薄,洋人入;沪江浊,洋场出。”简赅地展示了19世纪中国的屈辱境遇与全球文化流通之交的上海。寥寥数语不仅显出华洋之间的交杂特点,也决定了作品的叙事视点与口吻。就像这篇《洋场赋》出现在由传教士林乐知1868年创刊的《教会新报》上一样,也是华洋杂处的文化现象。从模拟《阿房宫赋》来看“醒世子”是个熟悉古典的文士,把“洋场”描写得如此恶俗不堪,不失传统的道德立场。但作品并未追究造成洋场的权力机制。作者确乎讳言洋人入侵的原因,却反客为主,在洋场空间中呈现华人的主体性存在,因此这篇作品能出现在一份洋办刊物中,从华洋之间的张力看有妥协也有进取。
在我看来,这样一篇最早出现在半殖民上海的文学作品,以华人视角凸显华人主体,所描写的正是近代新型的上海,富于文化杂交的时代性与新旧之间创造性转化的特征,其于“海派”的开创性意义是不应忽视的。在文化方面,1843年传教士麦都思和雒魏林在上海城东门外开设墨林书馆,翻译出版西学,其间形成“麦家圈”文人群体,包括王韬、李善兰等人,是一批最早与洋人合作的中国文人。他们大多是仕途失意的边缘文人,迫于生计为洋人打工,却成为最早的近代口岸“新型”文人。思想上中外交杂,一面赞赏西洋的“奇技淫巧”,一面眷恋老城厢,那里不乏文人的诗酒酬唱,谈艺论文,仍具文化上的优越感。“醒世子”应当属于这类文人。但随着租界物质上的不断发展,这份文化优越感愈益相形见绌。在19世纪60年代上海安装了电报线,英租界的马路上换上了煤气灯,并修筑了南京路、汉口路、北京路和九江路等马路,老城厢里的街道依然逼仄如故,一到雨天便泥泞难行。《洋场赋》中“煤烟贯地,有火何红?电报行空,不胫何通?”此即反映了当时先进技术带来的新景观,也体现了仿古即写真的特点。
《申报》开张,可说是上海文化的一件大事,开启了市民共情想象的新媒体时代。在报馆社论、朝廷报摘、国内外新闻、各类广告等众多栏目之间诗文也占了一栏,犹如开了一道文学闸口。所刊作品表现洋场生活感受,一般署笔名,也有妓女写的,日常地、源源不断地出现。在诗词歌赋各种体式中“仿”作一类如雨后春笋。像《洋场赋》之类涉及“海派”文学之源,固然不宜忽视。而“仿”作的数量如是之多、内容如是之广、延续时间如是之长,似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文学史甚至文化史现象。当然我们不提倡模仿,而对这个“仿”字却不能等闲视之。如安德森所言,近代的报纸和小说起了建构民族“想象共同体”的作用,其实仿作也具相似的功能,当它在报纸中蒙太奇般与天南地北的信息并列,叙事空间映射出全球景观的镜像,负载着一种新的思维。

《“逆城市化”背景下城乡创意产业的关系演变》
张昱
上海社科院文学所助理研究员
由于城市在制度环境、生产要素聚集度和文化开放性等方面的优势,使得“创意产业”自1998年首先在英国被提出后,始终与城市话语紧密相关。城市被视为创意产业的驱动力,而创意产业也能够为城市整体革新路径带来文化赋能。相较之下,乡村地处偏远、交通连接不畅、互联网覆盖面不足,创意产业在城市的发展模式和经验无法在乡村被复制,在一段时期内乡村创意产业的推进显得步履维艰。20世纪上半叶以来,“逆城市化”现象逐渐在欧美各国出现。到20世纪70年代后,不少大都市地区演变为由中小城镇和乡村地区组成的大功能城市地区,乡村和城市之间的界限变得愈发模糊。一开始,人口流动主要集中在城市富有阶层,他们开始向城市近郊迁移。紧接着大量中产阶级将生活重心移至郊区,甚至是更偏远的乡村。与过去由产品生命周期和廉价劳动力等经济因素促使的企业向乡村转移有所不同,这种人口迁移更倾向于人们对舒适生活的追求和对产业潜能的发掘。在此过程中,创意产业凭借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力和文化韧性等优势,能够改善自工业革命以来人口大量涌向城市而导致的乡村经济活力下降、地方感退化、文化特色式微等问题。同时,乡村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也盘活了乡村新移民的生活品质观念和创业活动之间的互动关系。
在过去的十多年间,创意产业随着“逆城市化”现象的延伸而在各国乡村有了越来越多的尝试。在乡村创意产业的初创阶段,需要倚靠中心城市,将乡村作为城市创意产业效益溢出的承载地。一种“城市干预”的乡村创意产业发展模式由此形成。该模式既能够帮助创意人士利用近郊与中心城市在地理位置上的接近性获得来自城市行业网络的基础设施、经费、供销渠道和政策支持,也能够为城市创意产业主体找到新的创意点和作品落地平台。城市创意产业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扶持了乡村创意产业的发展,尤其是在网络通讯设施不断普及和优化的当下,在线培训、在线设计、在线营销等数字内容的出现,有力提升了除乡村新移民之外的本土居民对创意产业的认同和创意策划经营的能力,为乡村个性的复原重塑和有效表达开拓出了新的方式,并在小规模的乡村市场基础上,不断强化对外部市场的吸引力。
不过,“城市干预”模式也存在明显的问题。首先,来自于城市的支持和激励政策难以避免地沿袭了“城市逻辑”,机构网络也仍然以城市为中心。其次,资助机构通常会偏好为高增长行业提供特权的创意产业分支,为其制定规范化和标准化定义。因此,该模式可能很难真正与乡村多元、自由、灵活的生活结合起来。
随着“逆城市化”进入深化期,内陆乡村和偏远乡村的经济文化振兴与城市发展被同等对待,各国乡村大力建设基础设施,积蓄了更丰富的社会资本。乡村创意产业开始探索自主发展模式。在并不占据明显区位优势的情况下,“人才”、“技术”和“领导力”成为了决定乡村创意产业是否成功的关键要素。
就“人才”要素而言,城市中产阶级向偏远乡村迁移是乡村创意产业重要的支撑力量。他们注重手工业、传统地方文化与新创意产业的结合,如文化遗产的商业化经营等,激发经济发展的潜能,而不必刻意追随特定的城市艺术和社会趋势及流行风格。创意人士也为乡村贡献了更多的社会效益优势。他们会策划实施不同的社区项目,旨在增强和传播“地方感”,为不同的参与者创造良好的互动环境,赋予他们解决地方问题的权力。创意人士从某些角度来看充当了社会活动家的角色,他们需要有较强的能动性和自我效能,通过知识技能和资源网络,协调、动员和筹集资金,提供组织能量以帮助乡村创意产业在更大的区域范围内运作。
就“技术”要素而言,信息和通讯技术在乡村创意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十分重要,提高了乡村与外部环境的连通性。信息和通讯技术既可以改变创意产品的性质,让创意人士购买到不同的材料和工具,培育所需的供应链,也可以为他们创造更直观便捷的产品展示和推广平台,开辟新的替代市场和全球市场。同时,降低了远距离沟通成本,为他们争取到新的协作关系网。乡村创意人士自身也有不少“数字创意者”,数字技术作为其创作实践的一部分。这种实践成为乡村的重要资源以提供数字包容性策略,即拥有高数字资本的创意人士可以作为良好的数字中介,以正式或非正式的形式参与到乡村社区的创造性或通用性数字技能的普及工作中。
就“领导力”要素而言,从政府层面来看,国家和地方政府在乡村创意产业的发展中扮演着资源协调、政策支持、经费资助、组织管理等角色。通过政府的制度支撑可以有效帮助乡村创意人士改善经营和管理效用,推进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从乡村社区层面来看,一些地方创意企业和创意人士也表现出有助于建立乡村社区韧性的领导力。作为社区成员,他们有意识地发展个人和集体能力以应对和影响外部环境和客观条件变化,维持和更新乡村社区,为社区资源开发出新的发展轨迹,鼓励乡村居民的参与,弥合了社会分歧,也强化了自然环境和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合理利用。
乡村是一个充满想象力和理想化生活方式的地方,“逆城市化”导致了复杂的城乡迁移、阶层冲突和土地利用变化。从城市在创意产业领域占绝对主导地位,到城市近郊发展出“城市干预”模式,再到更偏远乡村的自主探索阶段,城乡创意产业的发展并不是乡村衍生于城市而后脱离城市的过程。而是在城市中产阶级向乡村迁移的过程中,持续激发了乡村创意产业发展的潜能,为乡村振兴创造了多元的社会资本,尤其是知识经济时代所强调的文化资本,让他们有能力迎接行业疏离和市场规模有限的挑战,建立新的合作关系来维持和提高乡村的经济、文化和环境福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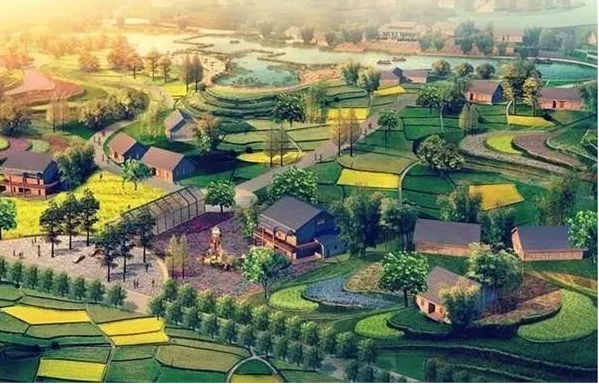
《创意再生长:新冠疫情中的全球创意城市》
曹晓华
上海社科院文学所助理研究员
查尔斯·兰德利(Charles Landry)曾经满怀信心地断言,创意是崭新城市架构中最主要的“通货”之一,“好奇心、想象力、创意、创新与发明这五个关键词,则形成了无懈可击的五重奏”。20世纪末开始,创意城市的蓝图已经呼之欲出,而五重奏的“音符”如今早已溢出了城市实践的边界。创意几度演化,可以和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感受城市的“人行步道”相媲美,那些陌生人群组成的物理屏障,那些承载社区文化的一砖一瓦,在创意城市的框架里成为无形的集聚渠道,将一切资源引向大城市搏动的心脏。
只是,新冠疫情的爆发改变了事情的走向,五重奏一度被迫停歇。如果说疫情之前的行业滤镜已经让人疑窦丛生,那么在疫情爆发后,“滤镜”就彻底支离破碎了。创意的“萧条”是否只是“天灾”?已经有学者试图跳出这种思维定势,指出文化创意行业目前面临的是一种结构性的问题,疫情只是加剧了原有的矛盾罢了。疫情封锁措施严重影响了行业经济,对于本就缺乏保障的低端劳动力群体而言,情况着实不容乐观。在与“创意阶层”这个概念配套的“3Ts”指数(即人才、科技、包容)中,根本没有后勤辅助等“编外”人员的一席之地。核心阶层之外的群体创造的价值一直被忽视。创意产业从业者的流动性很强,大部分时候也谈不上有稳定的工作环境,由此也可以理解核心阶层外围的“普通人”在遭遇疫情时更加容易成为弱势群体。现在我们讨论的已经不是毕业生们的底层求生,而是底层群体的绝处求生。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创意城市网络(UCCN)已经遍布世界各地,在疫情期间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对话渠道,为各国共同应对疫情提供了帮助。UCCN在疫情期间反应迅捷,成为阴霾中的一条“银线”。2020年3月13日,UCCN向世界各地的成员城市发出号召,收集各地已经和正在采取的疫情应对措施。在随后发布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案例集》中,可以发现全球创意城市在疫情中做出的种种尝试。文化和创意产业转到线上,同时各类网上博物馆、图书馆、网络学习平台等在世界各地开放,线上的音乐会、诗歌会等人文娱乐活动不胜枚举。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去年发布的《危机中的城市:打造韧性创意产业政策指南》中,介绍了世界各国政府在疫情中采取的三种主要行动类型:对艺术家和文化专业人士的直接支持,对文化和创意产业的间接支持以及增强文化和创意产业的竞争力。
尽管文艺界的线上尝试,是行业自救压力下的一种生存模式创新,创意在困顿中的网络传播也可视为向资本“借东风”,毕竟每一场线上直播背后都有平台的支持,而直播归根结底是一种数字经济。但不可否认的是,借助互联网平台,创意城市的人文精神得到彰显,人们更容易找到归属感和认同感,而这种最基本的同理心和共情能力,给予我们抵御风险和担当责任的勇气。
创意转向虚拟世界早有预兆,纽约、伦敦、巴黎等城市也深谙通过社交媒体塑造网络形象的诀窍。而网络数字产业的确可以成为振兴创意产业的利器,非但可以推动产业在后疫情时代快速复苏,还可以促成城市的数字化转型,简直一举多得。然而一个残酷的现实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享受到数字的红利。根据2019年ITU的数字发展报告,2019年全球网民数量达到41亿,但是在这样庞大的群体背后,有着令人担忧的数字鸿沟。数据显示,在发达国家,网民占总人口的近87%,发展中国家的这一数字是47%,最不发达国家仅占19.1%。这样的差距在移动端的使用率上同样显著。而这也是联合国所担忧的,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音乐会和音乐节一直在网上举行,这加速了产业的变化,但世界上约有46%的人口无法使用互联网,几乎有二分之一的人在隔离期间无法接触到艺术。长期以来的发展不均衡导致了这些比例悬殊的数字,以及这些数字背后被忽视的群体。
作为不断“演进”的城市发展策略,创意城市着重于灵活吸纳各种新兴元素,以吸引和优化城市资源的配置,包括利用网络平台与互联网用户共同经营城市的网上形象,以打通线上和线下、虚拟与现实的联结。科学技术作为充分体现人类智慧的发展动力,在今天爆发出了巨大的能量,即便在疫情的考验下也能延续城市精神,体现城市韧性。然而,互联网资源对于弱势群体而言依然是稀缺资源,疫情只是再一次凸显了原本就存在的“数字鸿沟”,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使本就很难接触到此类文化资源的人们失去了与他人共情的机会。
如同创意产业中有不同利益的群体一样,科技时代创意城市中的居民也并非铁板一块,不仅有“弄潮儿”还有“尾随者”,创意城市的实践需要更加精细化的考量——考虑到“数字鸿沟”和人群差异,让数字革命“以人为本”。“云演出”、“云刷馆”、文创产品的直播带货之所以制造了诸多热点,就是因为这些文化创意的传播更加接地气、为绝大多数普通人“喜闻乐见”。而这些都是另一种形式的“科技向善”,是一种数字的“温度”,也是打造城市品牌、塑造城市形象、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方式。随着国民经济整体复苏,互联网资本迟早会恢复本来的角色,产业布局中的角力已经悄然开始。线上的创意形式已经不只是一种应急的方案,更是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而这种文化表现形式是否挤压了其他形式的生存空间,文化创意的多样性是否会在数字化的浪潮中受到负面影响,现在还是一个未知数。
或许这次全人类面对的危机可以促成一种深度的反省,看到那些昔日不可见的人群和结构性的缺憾,真正推动创意的“再生长”。毕竟,所有的努力,只为将城市筑造为每一个人的安憩之所。每一次的技术更新,不为斩钉截铁地抛却往昔,也不为实现人群的“优胜劣汰”,而是为了达成对现实的某种超越。

原刊于《上海文化》2021年第10期,
有删节,注释参见原文。

【新刊目录】
《上海文化》(文化研究版)
2021年第10期
新时代新视野
胡俊飞 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传统及其弘扬观
访 谈
许纪霖 面对“后浪”文化,如何“降维启蒙”
讲 堂
王兆胜 当前中国散文创作偏向及其调适
经典新读
李 创 略论西方古典学对黑格尔美学的影响
理论前沿
伊娃·科藤 西方艺术观念与东方哲学的碰撞(仓恺延 周晓燕 译)
王奥娜 “否定的辩证法”与阿多诺的音乐分析
文学经纬
王 琼 论王安忆笔下的中国与西方
汪一辰 “细读”与“理论”的对话共生——论毕飞宇的文学批评及其方法论意义
城市文化
陈建华 张 昱 曹晓华 圆桌:创意城市的本土溯源与多维延展
文艺纵横
齐 伟 徐艳萍 互动电影研究:以交互界面的媒介考古为中心
旺达·斯特劳文 早期电影中的可触摸的银幕——“screen”的媒介考古学研究(王棵锁 译)
笔 记
李金燕 文人相重——从徐中玉与钱谷融先生的交谊说起
书 评
薛 毅 鲁迅研究的内在视野——重读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
英文目录
封二 谢稚柳《粤北锦江山色》
封三 好书经眼录
《上海文化》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扩展版)来源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引文数据库来源刊
社长:徐锦江
常务副社长:孙甘露
主编:吴亮
执行主编:王光东
副主编:杨斌华、张定浩
编辑部主任:朱生坚
编辑:木叶、黄德海、 贾艳艳、王韧、金方廷 、沈洁 、孙页
《上海文化》(文学批评版)
主办单位:上海市作家协会
地址:上海市巨鹿路675号
邮编:200040
电话:021-54039116
电子邮箱:xinpiping@163.com
邮发代号:4-785
出版日期:单月20日
《上海文化》(文化研究版)
主办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地址:上海市中山西路1610号2号楼928室
邮编:200235
电话:021-54908148
电子邮箱:shwh@sass.org.cn
邮发代号:4-888
出版日期:双月20日
主编:朱生坚
编辑:曹晓华
运维:任洁
制作:小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