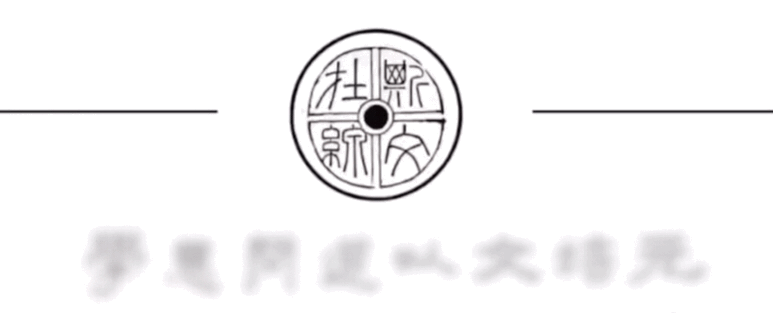
【编者按】
孙甘露先生的最新随笔集《时光硬币的两面》,收入了他三十多年来的散文随笔,包括《南方之夜》《我所失去的时代》《上海流水》等经典篇目。在这些缓慢而优雅的文字中,我们能够看到一座城市与一代人的改变。本次“斯文在线”,选取书中《我所失去的时代》一文,让读者体会哲思之深邃,文学之永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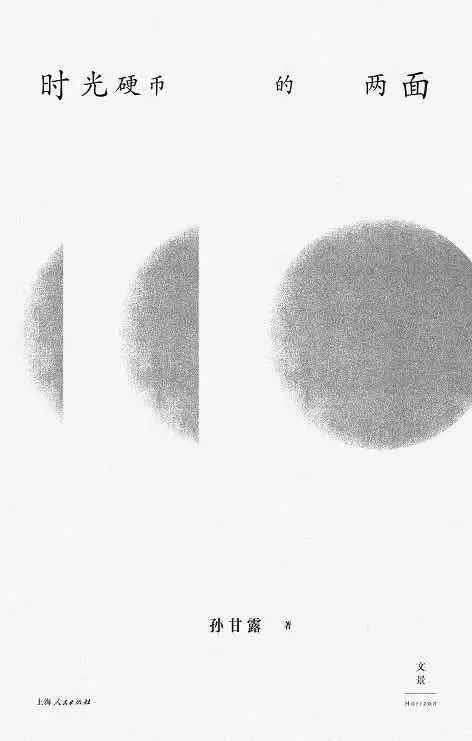
孙甘露《时光硬币的两面》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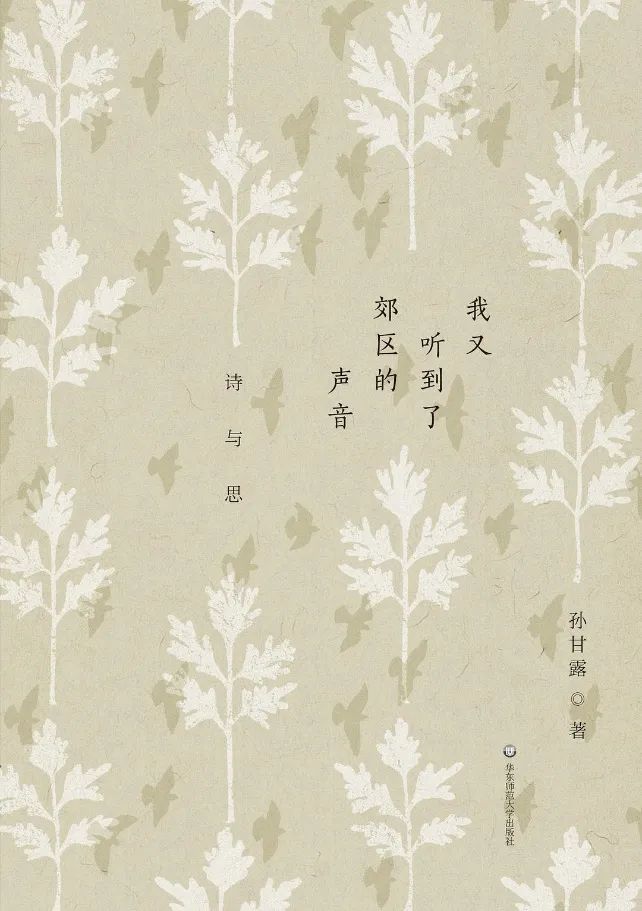
孙甘露《我又听到了郊区的声音:诗与思》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
我不是说我失去了曾经拥有的时代——时间、世代、生活方式以及智力氛围,而是失去了我曾经孜孜以求的、足以建立的、使我们寓于其中而又置身其外的某种可能性,而且它一经失去就永远失去。这种对丧失的体会,加缪称之为:人与环境的分离。它并不首先由社会统计给出指标,预示事物的朽败和坏死,它由那些孤寂的、沉思的、自愿流放的心灵所捕获。也由妇女、劳工、失学儿童和疾病所衬托。我指的是贝克特那样的心智以及一些众所周知的风物。污染,这是一个现代工业裹挟而来的词语,谁都不会认为这是一个不可引申之词。那样也不合近代中国的用语习惯。紧接着出现的另一词就是:荒谬。我的意思是,到了重读加缪和萨特之时了。这不是向起点的返回,因为没有起点,这也不是朝着温柔的乌有乡的归宿之行,因为漂泊才是唯一的归宿。这只是开端和终结并置的时刻。犹如一扇老式的转门,透明、多重,同时敞开和关闭着,运动着,并且被间隔成若干半密封的空间,我不想强调它的循环的意象。仿佛是可以彼此观看的天体。遥远而切近。一如死亡和彼岸之于我们。下海,这是另一个词(写下它已令我厌烦)。对这个词的滥用可以用另一个词来形容:泛滥成灾。我不想谈它,我也不知道我有什么理由非要谈它,读者可自行将此段忽略不计。
维特根斯坦声言:……精神总是环绕着灰烬。但愿那不是纸币的灰烬。

失去还意味着迷惘。当人们渐入知命之年,当写作成为一种生存的策略,而不是纯粹的(从来就不曾是?)精神活动时,在一个残酷的、无序的、缺乏智性和真正欢娱的时代背景前,当金钱适时地成为一种困扰,这当然会令我们感到空虚。不是因个人的某种缺乏而空虚,而是因为其充斥世间的空虚而迷惘、而癫狂。有趣的是,按照福柯的观点,正是在理性主义时代,现代疾病分类为我们发现了忧郁与躁狂之间的内在联系。病症,如同每个人都有一份病历卡一般,它伴随着我们,是我们所有档案中最公开也最熟视无睹的一份。
这又令我想到低能的聒噪和圣洁的沉默。我并不试图将这两者截然分开,它们彼此暗含,一如艾略特的著名诗篇《稻草人》所提供的形象,诗人说它皮囊泄气一般归于寂静。作为我们所处时代的精神投影,大师的影响还将继续存在。这些词,这些形象,这一系列的隐喻,虽然来自一些最敏感的灵魂,但那些相对平庸的灵魂依然视他们为无效。这当然没有超出大师们的预设。“多好的酬劳啊!”瓦雷里这样感叹过,“经过了一番深思,终得以放眼远眺神明的宁静。”
接着我接触到了信仰和死亡。
“信仰就是愿意信仰。”乌纳穆诺如是说。而死亡,则每时每刻都在发生。青年诗人朱朱写道:“我一想到死亡就会死去。”伽达默尔认定,这正是人之为人的第一标志:对死亡和死后世界的恐惧。
时至今日,我们目睹的是一种速效的信仰和缓释的死亡。换言之,是一种兴奋剂和镇静剂交替使用之下的文化疗程,它试图重建免疫系统,但它的并发症和适应证使之很快变成了一种新的现实——一种麻木和垂死的实况,显然,这是巫术风行于实证思潮之后的一处佐证。
文化有时确实像钟摆一样来回摆动,催眠般将我们的目光导入迷梦。梦,梦境,当然是我的中心词汇之一。它死亡般的形式,对暗示和详梦的需求以及与睡眠同体式的亲密关系,使之稍稍具有庇护所的风格,不论紧张或者是松懈,灵与肉都向之逃逸,它的无可避免和频频破灭正是它存在的原因。没有比幻灭更强有力的释放了,尤其在苏醒后的追忆之中。

这种危机是普遍的,它囊括了每一个头脑。危机,也正是我所关心的,这是一个焦点,汇聚事物并且使之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坦然地面对它(这是多么困难)也许是唯一有效的手段。这是一个与危言耸听无关的词。它也没有多少商业效用,当它出现时,它就是真正出现了。通常,它是无法摆脱的,它的唯一出路是转化成另一种危机。
犹如人们诙谐地论及爱时,称之为危机或疾病,爱,当然它与对孤独的恐惧有关,即便我们是为了听听自己的声音,看看自己的影子才来到这个星球上,他者化现象以及我们使事物对象化的能力也使我们陷入广大无边的人群。在孤独中歌唱也就是在人群中歌唱,桑德堡曾经如此设问:“相爱者是否等于丧偶者?”这也恰是一切文化检索中惯常遭遇的情形。此与彼,内与外,正与反,不计其数。
我们确实不妨把时代看作是一个寓言,它视一个微观的世界为无穷无尽的宇宙的一份摘要。无论是潘多拉的盒子或是所罗门的瓶子,它都是一个内敛的故事(故事这个词并不为那些文学界的太监所独有),庞德的比喻在此是适用的,诗或曰寓言是方程式,而不是喷射器或掷弹筒一类的东西。我们要向那些严肃的批评家致敬,是他们使真诚的探寻得以确立。
我一度认为回归是一个虚妄之词,而今我才发现,我的态度使我误认了这个时代。每一瞬间都在发生的事情,因为它的无所不在而被忽视了。虽然它如潜流一般四处漫溢,但它的潜在仍然使它躲过了人们的视线。母系、传统、血缘和故乡,由这一切所支架的文化怎会倾覆于一夜之间?除非它在某处早已被倾覆。
一些词汇继续出现。(符号学,稍息!)柔情。它仿佛外在于缜密的思维,但因为狂喜和绝望,透过性史、娼妓史,我们逐渐在文明史中发现了一丝柔情的迹象。怎么,这不是我们时代的常备词汇?它为若干人士所精选,它当然不是杂志上的柔情,它要严酷得多,曲折得多,晦涩得多。当它为李清照和苏东坡所选中时,它也已被所有古代诗人所选中。当它在译文中出现时,通常是在对道德做一次逾越。也有完全循规蹈矩的柔情,只是在内心中它更为狂野,与任何时代都格格不入。它是所有动力的动力。前弗洛伊德式的。(开个玩笑。)
柔情的派生物首先是忧郁,这个老掉牙的词一点也不适合今日的文学。这是普希金反复吟唱的依据,在这个词的所有笔画之中你可看到大海、沙皇、俄罗斯的土地、少妇、军官和镣铐。聂鲁达发展了这种忧郁。如同他的著名诗篇,我们读到了绝望这个词。

绝望可能是一种面对永恒的声音,但它是一种加弱音器的声音,是一棵经过修枝的嚎叫之树,它不再生长,期待复活不是它的属性。它不是一种准备妥协的姿态,寂灭是它的必由之路,而迷狂和寂然都是它临终前的形态,自杀是它天然的伴侣,至于伴侣们的著名的名单还是省略吧!
上述问题虽然均由一些才智超群的人物提出,我依然不把它们视作是一些技术问题。虽然技术是我喜爱的作家、臭小子海明威爱唠叨的东西。也许有一天,这个世界将归结为一门技术,这也不是一个悲观的结局,但不是我的结局,我是说我唾弃这样一个世界。
我失去了我未曾有过的东西,也许那就是虚无。但即使我失去了一切,有的和没有的,我也不会失去这些语词。

【作者简介】
孙甘露,作家。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市作协副主席、浦东新区文联主席、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院长。
主要作品:长篇小说《呼吸》、中短篇小说集《我是少年酒坛子》、《忆秦娥》,随笔集《我又听到了郊区的声音》、《时光硬币的两面》、访谈录《被折叠的时间》等。作品有英语、法语、俄语、日语、韩语等译本。
主编:朱生坚
编辑:张晴柔
运维:任洁
制作:小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