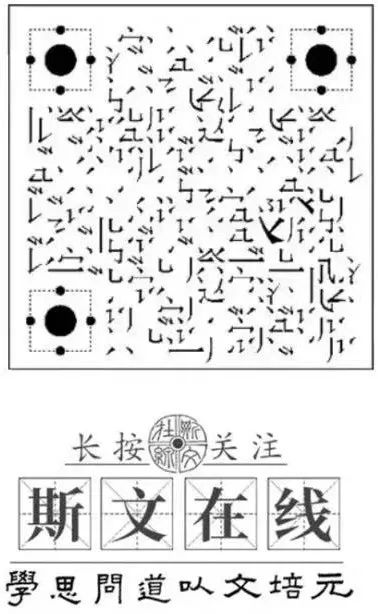一、引言
近现代时期,上海承接了江南地区大量人口和工商文教转移,江南人口纷纷将本地特征带至迁居地,借助在各自行业取得的社会地位,为新移民社会赋予了多元的主导元素,形塑了早期主流“上海文化”的参考准则。大量外来人口向上海的迁移与融合,“为近代上海文化的形成提供了底色”促使新型城市文化认同得以诞生。移民身份固然保留了同乡认同,这种身份也是在上海就业并获取圈层提升轨道的外力,同时,文化身份认同的范畴也在扩张:沿着同乡情感为轴心的认同实践,分别形成了早期城市身份认同和剔除了地方保护主义的家国认同。在这种意义上,同乡纽带可被理解为“‘文化’多变特性的一种证明”。
这种多重身份的复杂性既由当时的大众媒介所呈现,后者又参与到复杂身份的动态生产之中。“上海人”身份的建构离不开大众媒介对共同文化特征的整合,媒介将“上海人”的行为方式予以“规定化”并将其传播,对内完成移民群体在心理上由“双籍”到“单籍”的认同转变,对外逐渐形成一种“上海人”的整体形象:“活动在上海的人,也往往笼统地视为上海人。”大众媒介发挥了双向介入与差异统一的作用,实现了对差异性的“收编”,进而“集中体现了当时城市社会生活与人格类型的共同价值取向”以及一代上海人的共同特征。
身份建构总是离不开边缘群体对主流群体的折射,“上海人”身份建构的另一面是对“他者”的生产。后者极具冲突性的身份要素,承接了包括媒体在内的不同群体的观察、想象、刻画和区分,即“只有对照它界定自我时作为反衬的另类才能理解上海人身份”。而在“写上海”的过程中,乡村与其他城市曾经充当了城市形象的“他者”,以一种镜像反衬了上海独特的都市气质。“他者”视角中的上海,又往往被视为罪恶之都或城市传奇,由此在文学中成为一种互文性的表达定式,在两种表达路径上都形成了上海繁华且传奇的都市气质假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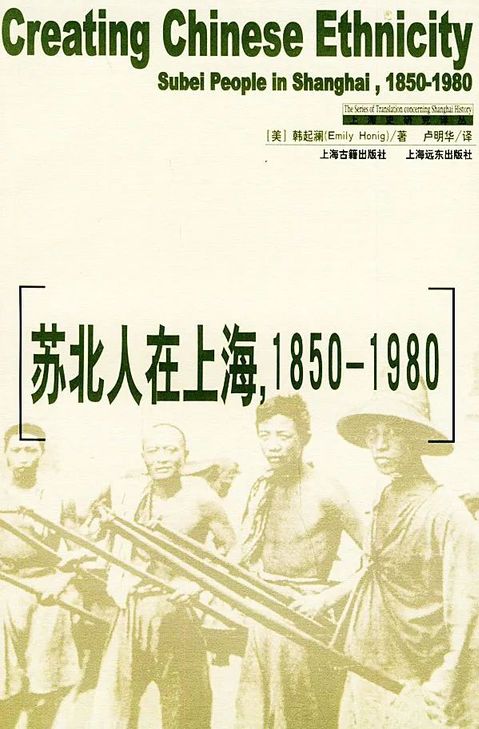
[美]韩起澜:《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上海城市内涵的多元性导致了“上海人”身份的文化概念既令人神往又模糊不清,与之相反,媒介描述中的负面“上海人”形象却相对清晰可辨。二者毋宁说是一种相依共存的关系:作为主体的“上海人”概念需要借助“他者”的投射来完成意义的生产,同样,作为“他者”的上海边缘群体的得名,同样依赖于模糊的“上海人”身份概念。在“上海人”文化身份的形成过程中,“外来客”与边缘人群充当了传递身份信息的中介。这种身份认知建构源于沉淀在包括报人群体在内的上海市民心理结构中的某种无意识原型。报刊激活了大众潜意识中关于城市身份的原型结构,在报刊中完成了对城市“他者”形象与“规定”城市身份之间的区分。
本文通过整理20世纪20至40年代相关报刊杂志等历史资料,考察当时大众媒介如何通过对“他者”形象的辨认与塑造,不断推动“上海人”理想主体的动态建构,比较不同圈层上海居民负面行为的媒介呈现与解读,进一步阐释在媒介的进步话语下,“上海人”身份意义生产中地域与圈层等多重因素的交叉作用。
二、天堂里的外乡人:上海底层旅居者的早期边缘呈现
旅居者(sojourner)概念源于芝加哥学派对移民研究的讨论,20世纪50年代华裔学者萧振鹏在描述旅居者时,形容他们是在一个国家生活了多年却未被同化的人。与萧振鹏所研究的海外华人洗衣工类似,20世纪的上海旅人在媒体和现实的共耕下,成为两个空间中的“他者”,这也让一部分迁居上海的底层外来人口具备了旅居者的内涵属性。报刊通过传递“内/外”的身份隐喻,将底层旅居者的行为与生活方式刻画为当代都市中的负面参照,形成了以他者的静态和停滞来反射上海的动态与发展的呈现逻辑。
(一)犯罪行为的圈层认定与籍贯归属
作为外来的他者,城市底层移民的边缘性首先体现在他们对城市居民的潜在威胁,远道而来的旅居者成为解释斗殴、抢劫、卖淫等事件的首要因素。报刊中大量犯罪者均被表现为年富力强的外来青壮年,“十分之八以上的犯罪者都是失业的游民”,这些人口在迁移之后,无法在城市依靠过去的技能为生,闲散、游荡的行为特征成为解释外来者与犯罪行为联系的首要原因。
以犯罪为特征的负面行为与旅居者的外来身份牢固地绑定在一起,在上海日常的讲述中,报刊渗透了一种“身份政治经济学”,将底层旅居者与“上海人”身份相隔离。除了底层身份与犯罪关联的不断重复,当事人与圈层和城市属性相关的身份特征,进而能影响媒体与大众对于他们的道德评判。在1920年的“阎瑞生杀妓案”中,受害者王莲英被称为“花国总理”,是旅居者道德败坏的集中体现;相比之下,凶手阎瑞生作为上海买办,却象征着由外国移植而来的现代性所带给中国的一切。他的英语能力、对电影等高端兴趣的执着以及当时在世界同龄人中少有的驾驶技巧,使他在报道中没有成为普通的歹徒,反倒有报刊在阎瑞生被处决后对他的境遇表达了同情。在这位看起来符合上海身份想象的年轻人的遭遇中,因为结束了这样一个“有才智”青年的性命,“社会”必须承担最大的过错。
福柯认为,传统社会对于犯罪的认识与断言往往与利益或情欲相关,在社会各阶层中都可能出现。而进入现代工业社会之后,人们却认为罪犯“几乎完全出自社会秩序的底层”。当时上海的报刊通过凸显移民的籍贯、圈层与犯罪活动的关联,将旅居者的身份特征限定在主流社会的对立面,从而将普遍的行为特征与特定的群体进行关联。
(二)城市日常生活的危险制造者
随着移民潮、难民潮进入上海,原本从事农业生产而缺少现代职业技能的旅居者往往只能从事一些底层劳动,黄包车夫、妓女、苦力、难民、流氓等身份成为他们在媒介中的日常标签。曾经江北旅居客的大量到来,被认为对“江南人群体自诩为上海精英文化代表的诉求构成了挑战”,由此形成了“江南—江北”和“沪内—沪外”的二元化身份格局。

嗷嗷待哺的难民:上海南市难民麕集法租界铁门外待发面包(《国闻周报》,1937)
一方面,城市中旅居者与其他市民之间的交往和互动被认为带来了相当大的麻烦。因为旅居者通过所从事的职业活动,使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来施展其“邪恶的天性”,而这本身源于旅居者物质条件匮乏的客观条件。为了生存,难民有时在街边乔装戏法、售卖“滑头东西”来赚取少量零钱的做法则又加剧了这种偏见。旧上海媒体一度将难民表述为上海社会头号问题,尤其在战争环境下,新闻报道更倾向于强化表达这类人群所导致的社会冲突。
另一方面,商业文化是近代上海最重要的城市特质之一,然而对于多数来自农村的旅居者而言,学习商业文化却被认为脱离了乡土特质,在此基础上试图进行文化或身份的跃迁,也被认为是一种危险的行为。这种尝试并未为旅居者增添上海身份的合法性,反而体现了城市负面道德行为在个体身上的扩散:“有了真实的学问,反不能谋到一个些微的职业,滑头事业,倒充斥了社会。”旅居者借助职业所进行的非常规行为,成为其边缘化身份及其对城市日常生活造成潜在威胁的识别特征。一种针对此类行为的常见媒体解释,是认为“农村带来的‘淳朴老实’的天性已被上海的繁荣销蚀殆尽了”。这些人通过职业进行的日常交往被定义为短暂地借用了城市身份的外衣,他们对职业内容的群体实践,又从另一个维度反映出外乡身份的难以改变。
在媒体看来,上海蕴藏着的商业精神对旅居者而言是极具复杂性的一种文化经验,当旅居者自身的乡土精神和上海的商业精神交汇时,无法被掌控的商业精神会导致旅居者意志品质的滑落,从而成为造成城市日常生活危险的潜在力量。
(三)城市经验匮乏的外乡客
在早期报刊的描述中,上海是与世界潮流无缝衔接的国际大都市,拥有各种眼花缭乱的现代设备。伴随现代物质产品出现的还有新的城市规则与生活经验,这种生活经验既是城市珍视的现代成果,同时也成为检验城市身份的标尺。报刊文人尽管相信本地所反映的现代精神应当引领当时的中国,却敏锐地观察到了上海的旅居者在学习“上海生活”时的“窘迫”。由此,旅居者囿于经济、视野和城市经验上的限制,经常成为城市生活反面典型的“出洋相者”与“被教育者”,继而媒体借助城市规则的镜像,进一步构建了外乡人不谙世事、缺少城市生活经验的形象。
上海作为时尚都市,城市中的女性以时髦而闻名全国,外地来沪的丝厂女工“每月所得的工钱,泰半花费在化妆打扮上,饮食粗陋”。不过媒体上不留情面的犀利评价,却反映出这种模仿与讲究,实则没有让旅居者踏入“城市身份俱乐部”。如果说对于时尚的感知暴露了生活品位上的差距,那么日常生活的“出洋相”则被视作缺乏城市经验的表现。
《晶报》在1927年刊载了描述外乡客来到上海的系列故事,利用漫画与文字讲述了一位名叫“阿木林”的“乡下人”因缺乏城市生活经验而遭遇的各种窘迫经历。由于缺少见识,旅居者在接触火车、电灯等现代化设备时出现了许多意外,屡次解救旅居者于知识困境的,都是在城市中占据较优结构化生存位置的居民。一方面是乡村经验与城市规则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是现代知识匮乏与城市发展之间的矛盾,二者都试图借助旅居者“出洋相”的行为,说明城市文明的某种门槛和距离。而在被拥有城市生活经验的居民“教育”的过程中,大众媒介不断强化了“乡下人”的身份隐喻,刺激着城市读者对外来人口的认知模式,形成了在地域、文化、生活经验上都区别于自己的“他者”印象。进而,战争期间大量赶赴上海的贫困移民,因缺乏城市经验而最终走向悲惨命运的叙事,也成为报刊有意择取并强调的一种结局。

《晶报》的《乡下人到上海》系列故事
报刊对外乡人在上海“出洋相”或受骗的事件刻画中,不论主动或是被动来沪,窘迫旅居者的结局不外于受苦或是逃离。在报纸一系列描述“出洋相”的场景中,外乡人对上海经验的尝试,被永远定格在体面的主流实践之外,而成为一项失败的文化体验。在这种“来—去”的经历对照中,旅居者的遭遇通过系列性文章串联为一套隐喻。他们逃离与被教育的故事,都在不断地反映这样一个事实:旅居者的城市生活经验即便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得到提升,但外乡人面对现代都市生活的窘迫却因媒介的夸诞描述而被持续标签化。
三、消费:中上圈层“上海人”的身份表征
如果说底层旅居者的“不体面”被定义为乡村的、落后的、非上海的身份标签,并被塑造为上海城市特征的对立面,从而为“什么不是上海人”做出了他者角度的注释;那么,对于体面且富裕的中产群体的报道,则围绕着以消费活动为主的日常实践。然而从消费角度建构上海身份的特质,在报刊文人眼中也始终是被批评、嘲讽和不可欲的对象。
上海作为现代都市,一度被认为能够承载普通人对于物质生活的所有想象。“听人说起上海是多么的繁华啊!差不多在路上到处可以拾到黄的金子、白的银子,但是一到上海,又异样了。”上海富裕群体主要由买办、民族资本家和高级职员组成,20世纪30年代这一群体的人数在10万左右,相比于当时数百万的上海居民,这群人的生活方式并不具有普遍性,“但是对上海人影响极大,有领先和示范作用”。
在报刊记录下,消费活动成为表征上海人身份特征和道德表现的一扇窗。报纸称赞了那些拥有进取精神与良好道德表现的富裕群体为社会带来的正面作用,与此同时,大量过度的消费活动却又被解读为应受指责的不当行为。“白天间若没有事做,睡到十二点以后才起身,夜间,便是他们活跃的时刻……去进餐,茶食,和跳舞……音乐会上的黑人乐团,吹奏着使人迷醉的爵士乐。”“夜阑人静,家家闭户睡觉,不料仍有许多绅士在楚馆秦楼挟妓雀战,声浪扰人。”对报刊文人而言,更值得关注的是令人羡慕的富裕生活与充满道德瑕疵的日常生活之间的矛盾。而当社会面临战争危机之际,一些过度消费行为也被认为溢出了上海城市身份中道德水准边界而受到指责,例如将这些“上海先生与小姐”称作“不事生产,只知道浪费的宝贝”。刊以城市或国族共同体叙事之下的身份道德作为准则,对上海部分市民在个人层面的物质乐进行批判,指出这类“上海人的人生观是不正当的,没有道德的”。
在富裕圈层受到报刊关注的同时,职工群体的生活也成为报刊话语审视的对象,他们是随工业化兴起而从事专业化程度较高职业的中产群体,即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笔下的“白领”。不同于更加富裕的圈层,中层职工群体遭受了来自地位和道德的双重质问。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处于职业群体的居民人数大约为20万至30万之间,位列全国第一。白领群体的诞生源于现代城市生活对于结构化职业人口的需求,以此为契机,大量上海的职业人群获得了在物质与文化上融入上海身份的可能。例如30年代的上海邮务员中拥有中小学学历的比例达到80%以上,成为当时一项远非贫民可以企及的工作。白领职业和拥有一定教育背景的新移居者,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同时接受了新的城市身份内涵。相比之下,一些中低层职员虽然因获得结构性的生存地位而被报刊纳入“上海人”的范畴,然而出于物质条件的限制,这类群体同样被当作不稳定的潜在“越轨者”而被加以警惕。《上海劳工统计(1930—1937)》刊载的十几项职业平均月工资多在十几元,这种物质条件的困难引来了报刊对中低层职员可靠性的怀疑。报刊话语仍旧基于物质生活的体面来奠定“上海人”身份的基础。
富裕圈层的消费行为对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产生了示范性的影响,职员群体在竭力模仿中试图维持其外表上脆弱的身份体面。“上海人无论贫富所穿的衣服都非常讲究”,“有了面子,然后可以生活,没有面子,就要受到压迫……虽然在背地里做猫做狗,而一到场面,硬碰硬,说一不二,都是大老官!”这反映出,上海中层劳动群体倾向于将城市身份的实质视作一种笼统的形象识别,其中消费活动被视为重要的一环,物质维度对于“上海性”的重要意义随着人们对消费的模仿而被不断加深。
在一些研究者看来,上海的现代化发展以及各类社会活动同样具有定义上海身份的功能,在消费文化席卷下,并不富有的普通上海居民试图通过消费来实现上海人的身份表征。所谓“贪夫殉财、烈士殉名,不料上海人却只知道殉衣”,不论财富如何,报刊舆论中的上海居民都在努力追求华美的服饰。在消费压力下,上海普通职员在理想生活与无奈之间,为了维持生活的体面不得不四处借钱,“排场要大,而实力毫无”。为维持体面生活的开支与现实财富能力的有限,构成了上海职员群体在身份建构实践中的主要矛盾,在“上海人”对这种物质生活分毫不让的同时,报刊通过对“实力毫无”的强调,不断重申在身份要素间的权力关系。媒体对此类生活方式的批判,渗透在上海人日常的各个瞬间,覆盖了普通人的消费、社交甚至死亡。
中层劳动者在报刊中的评价维度相较于富裕者更加丰富。不可忽略的是,报人亦不能摆脱自身的圈层归属,这使大众媒介对于“何为上海人”的认知预设,自然而然地带上了特定的视角,并使其为主流舆论所接受。同样是一些受到批评和嘲讽的行为,底层旅居者的实践被归为无法融入上海的外乡人的窘迫,而经济上优越圈层的过度消费,则仅被视为上海人普遍存在的一种生活缺点,甚至成为凸显市民身份的表征。
四、市民与国民:“上海人”身份内涵的拓展
在早期因政治运动来到上海的报人眼中,上海是启中国之变、开社会风气的起点,是开辟城市与国族共同体的根据地。康有为在《强学报》首刊的《上海强学会序》中谈到:“今为上海,乃群天下之图书器物,群天下之通人学士,相与讲焉。”这种对于文化领域的资源吸纳,源于上海率先出现的各种条件,例如商业稿费制度、出版物的行政追惩制、新式印刷设备等,为大量投身政治运动的报人提供了物质上的支撑。同时上海居民因这种文化和地理环境而成为大众媒介新文化审视下的政治启蒙对象。1896年梁启超提出“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报刊的一大天职就是成为国族层面启发民众的向导者。1904年,蔡元培等人在《警钟日报》社论中呼吁上海精神时,指出上海之“乳汁”应当哺育全国:“上海者,上海人之上海也,上海人得此天然地势,宜其组织特色文明,随上海潮流,灌注全国,使全国人饱饮吾上海文明乳汁。”这是“上海人”在文化概念上的首次出现。事实上,当时定居上海的精英群体绝大多数都不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但这并不影响他们以“上海人”的身份自居。地理维度的上海意涵已然随着政治话语发生改变,政治文化对于现代性的引导与追求,成为上海城市精神与上海人身份认同的核心要素之一。
20世纪20年代,报刊开始流行“新文化”“新上海”等表述,同时文明、青年、进步、城市这类术语也开始在报刊中频繁出现。内外交困的时代背景与现代民族国家话语的启蒙相结合,以“东—西”二元对立的方式传递出“新—旧”的发展观念。马克思指出,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东方必然要“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初识西方现代化样貌的上海工商业人士,同样开始在中国土地上尝试建立起一座不同于传统经验的现代城市。政治元素在建构城市身份中的讨论,自改良派政治家报人起就已出现。报刊对于“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的塑造,促进了上海人“公众”与“市民”身份的生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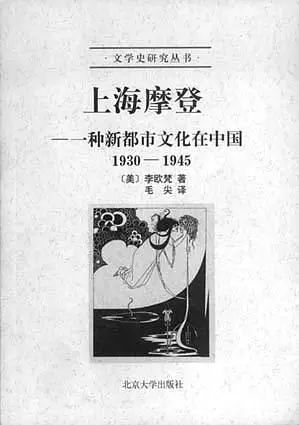
[美] 李欧梵 著, 毛尖 译:《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 , 2001
被报刊划入市民群体的中上圈层,最具备成为上海城市人口主体的可能,他们展现了获得完整城市身份内涵的潜能。在城市身份建构的过程中,发端于现代性与民族国家的身份概念,既是国族思想的起源,又支撑了城市身份的建立。在上海身份的形成与对他者的刻画过程中,大众媒介试图凝聚城市共同体和现代民族国家这两项意识,作为建构拥有完整“上海人”身份的精神内涵。对于中上层社会成员的启蒙落脚于精神上的规劝,以期在现代城市文明与民族国家的构建中发挥他们的力量。然而,报刊将缺少物质生活基础的底层移民视为城市的不稳定因素,便也主动忽略了对这群人在国家层面的精神启蒙,而仅寄希望于该群体在城市内部保持团结。
在面对外敌入侵的威胁时,知识分子意识到以城市为单位扩大具有现代精神和时局素养之国民的迫切性。《申报》在一篇社论中指出上海时局之问题“不在上海市民的不知醉生梦死为不当,却在没有一种强有力的组织来加以纠正”,缺少的是一种“督促与规劝的工作”。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战争阴影的笼罩下,为了激发市民在战争环境中的道德意识,除了家国民族议题,报人增添了在职业基础之上的社会意识、城市文明精神等方面的讨论,以期借助城市文明、现代发展、国家富强等议题,向个人层面传递蕴含在城市身份中的市民精神。媒体见证了孤岛时期上海人性格的转变,从“浮躁”“狂妄”到沉着隐忍,节衣缩食帮助他人。“改造人作为改造一切的基础”成为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的共识。在对市民的引导中,媒介所认可的身份形象淡化了地理性、职业性等条件,凸显了文化因素主导下行动的重要性:“需要的是常识充分、身体强健的国民,和有纪律有组织的社会。”报刊以市民身份为标准,提出市民素养对于城市乃至国家的重要作用,同时提出这种背景下报纸所背负的“醒世觉迷”之任务。
报刊文人眼中亟待启蒙的市民具有典型的圈层特征,是有一定的学识与财富的人,他们被寄希望于通过道德文化上的蜕变,来提升国家、城市在现代化危机中的竞争力。在这个意义上,曾经被公共话语质疑城市身份的市民,被重新赋予了城市主体的期待与可能性。另一方面,如前文所述,底层移民的形象一度被刻画为难以被规劝与同化的上海旅居者,他们仅被视作地理层面的上海居民,把不合时宜的静态乡土经验错置于都市生活中。对于这些旅居者而言,现代职业技能的缺乏限制了他们所能从事的工作,并进一步阻碍了其文化习惯等方面的都市化。对于底层人口转变的期待主要寄希望于国家与学人能起到开智于底层的角色,“故必使人人有普通之知识,乃能副其国民之资格”。这恰恰反映出报刊文人基于旅居者群体在物质与道德上的双重判断缺失,毕竟该群体在启蒙的范畴之外,也就不过希望他们可以通过学习现代规范而避免为城市带来更多的伤害。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报刊对于上海市民日常行为缺点的批评,连同对其不足之处的引导,将“上海人”身份建基于文化主体与城市主体二者的交点。此后,随着报刊对于上海市民国族身份与城市文明精神的唤起,原本不断遭受报刊批评的中上圈层上海人的身份特质,在城市和国族共同体遭受危难之际被重新缝合,又赋予了这些“不完美者”增益上海身份的可能。曾经的缺点成为完整“上海人”身份得以生长的新空间,使身份“连续不断地包容其他附加或补充的意义”。但在大众媒介普遍的“引导”中,上海居民基于阶层、职业与籍贯等因素所形成的偏见,则在能否习得“上海人”身份的背后,反而强化了“城市/乡村”“我们/他者”“进化潜能/顽固落后”等顽固的隐性逻辑。
五、结语
“上海人”的身份内涵建构是一个受多重因素影响且持续进行协商的动态历史过程。民国时期“上海人”身份建构的过程中,对此议题不断加以再现、引导和规训的大众媒介,其本身也是历史语境与脉络中的行动者之一,有时报刊是对社会主流观点的“再现”,有时文人又企图通过批评与引导,对其进行趋近于理想的构建。最终留下的丰富文字资料使我们能对当时的社会过程管中窥豹。
一个族群身份的历史建构往往首先表现为在现实与想象中对“他者”的建构。在“上海人”身份形成的案例中,某些群体“他者”地位的获得,并不只是由其社会圈层所决定的,籍贯及其背后所代表的移民数量、影响力和文化习惯等,也发挥着同等重要的作用。部分群体的边缘化与“他者化”,自然与其阶层地位脱不了干系,但另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是,边缘群体与持江南吴语的多数上海主流人口所形成的文化差异。在后者眼中,前者的生活习惯、口音、行为方式等都与理想中的市民身份格格不入。即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大众媒介中的公开歧视早已销声匿迹,但作为上海市民中的“他者”而存在的旅居移民,其相对的边缘身份甚至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才随着改革开放后新移民的涌入而被淡化。
“上海人”身份的形成总体而言是一种相似性和差异性的对话协商,充分吸纳了具备身份潜力的“上海人”,往往位于较为优越的圈层或来自相对富裕的江南地区,同时把旅居者建构为市民身份的“他者”,后者的城市边缘地位被定义为与现代城市文明格格不入,进而也很少被报刊寄予启蒙引导的可能性。不论是再现社会主流观点,还是力图进行理想化的引导,大众媒介关于什么是“上海人”的讨论,最终可能只是在文化层面再生产了旧上海基于阶层与籍贯的权力认知。真正实现了“上海人”内涵的媒介再生产,或许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变革。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在面对外来移民的快速涌入时,大众媒介在对市民精神的塑造方面显然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由此也折射出大众媒介在城市精神塑造问题上的多面性和复杂性。
本文刊于《上海文化》(文化研究版)2023年12月号。注释见原文。

【作者简介】
陆新蕾,1982年生。华东政法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媒介与社会文化。
郁升, 1996年生。华东政法大学传播学院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媒介与身份认同。
【新刊目录】
《上海文化》(文化研究版)
2023年第12期
新时代新视野
郭思恒 从城市到精神——上海城市现代化道路与理念
访 谈
王南溟 艺术社区:让社区成为作品
理 论
泓 峻 “第二个结合”视域中新的文学观及其学术意义
姚晓雷 陈玉璇 改革开放以来文学讲述中国式现代化故事的地域路径
文 学
何霜紫 “时光慢递”与“绿色废土”——评《我们生活在南京》兼论“中国网络科幻”
孙晓迪 再造昆仑:“丝绸朋克”小说的幻想尺度与现代性镜像
童博轩 人工智能“近未来”想象的创作探索——从《造神年代》看网络科幻的书写潜能
文 化
陆新蕾 郁 升 体面的市民与危险的“他者”:“上海人”身份的早期媒介生产
高晓倩 上海文化熔炉中的现代身份养成:基于犹太青少年难民自传的考察
彭 志 都会图景与画笔救国:《时代漫画》中的直言与隐义
文 艺
姜 岑 郭会坡 “游于艺”思想辨正及其对当代艺术的启示
潘晓斌 何小青 数字化对中国电影发展的价值意蕴研究
林梓豪 时间的“脱节”及其可见性:德勒兹与弗朗西斯·培根的影像共振
编后记
英文目录
封二 曹琼德《蓝色树林》
封三 好书经眼录
《上海文化》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扩展版)来源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引文数据库来源刊
社长:徐锦江
常务副社长:孙甘露
主编:吴亮
执行主编:王光东
副主编:杨斌华、张定浩
编辑部主任:朱生坚
编辑:木叶、黄德海、贾艳艳、王韧、金方廷、沈洁、孙页
《上海文化》(文学批评版)
主办单位:上海市作家协会
地址:上海市巨鹿路675号
邮编:200040
电话:021-54039116
电子邮箱:xinpiping@163.com
邮发代号:4-785
出版日期:单月20日
《上海文化》(文化研究版)
主办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地址:上海市中山西路1610号2号楼928室
邮编:200235
电话:021-54908148
电子邮箱:shwh@sass.org.cn
邮发代号:4-888
出版日期:双月20日
主编:朱生坚
编辑:张晴柔
运维:任洁
制作:小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