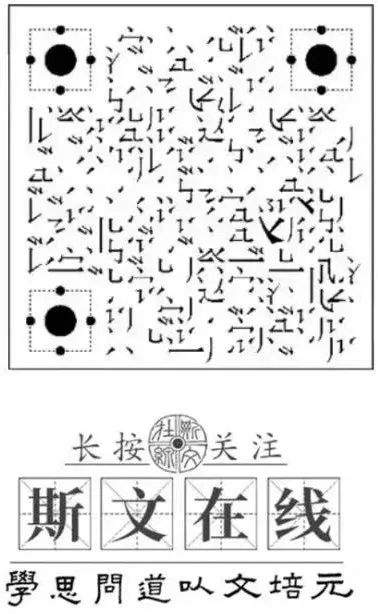一、绪论
现代词学的确立通常被认为在20世纪30年代,1934年龙榆生在《词学季刊》上发表《研究词学之商榷》一文,这篇具有开创意义的论文被视为“现代词学诞生的一篇宣言”,从此“词学”被纳入了一个与传统有别的崭新学术体系中,有了清晰的定义与明确的研究范畴。但现代词学的诞生并非经由《研究词学之商榷》一蹴而就,而是传统词学在近代以来的政局变化、社会思潮、教育制度、出版条件等多重因素的冲击下的必然走向。
在这个走向中,创作论作为词学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演变尤其值得被关注。传统词学中,理论建构与审美阐释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指导创作实践,即以民国之前的清代词坛为例,无论浙西派或是常州派,其词学主张都是为了在不同的政治背景与文化环境下,更全面地针对填词创作建立价值导向与审美范式,简而言之,是为了回答“为何填词”“怎样填词”“怎样填好词”等一系列创作论问题。而在近代社会与文化遭到了现代性的全面冲击之后,如学者所说:“五四运动以后,‘填词’的成分在淡化,而‘研究’的成分在逐步强化,进而形成了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词学’。”或者说,现代词学萌芽的过程,同时也是“填词”的理论比重逐渐减少的过程。
最能完整体现这个脱离过程的文本载体是民国词话,词话至民国已经是极其成熟的文学批评样式,词话作者沿袭传统词学的研究途径与方法,同时也承载了推动词学转型的重任。本文注意到,民国词话的内容与形式,在这个转型期中始终处于一种动态的变化过程中,尤其是“填词”的分离,使得民国中后期词学文本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而“填词”的退场同样经历了一个混乱复杂的过渡期,并不是“填词创作消亡了,现代词学就建立起来了”这样简单的因果逻辑。民国虽然时间不长,但囊括三代词人,每一代词人都有完全不同的教育背景和身份认知,新旧文化的冲突,更导致他们对于“应该怎样填词”“怎样看待填词的消亡”等等问题,有着迥然不同的观念与做法。本文将围绕以上问题在民国词话中的响应,以及词话如何跟随“填词淡化”这个因素产生变化,从而考察现代词学演进中的萌芽状态。
二、民国词话中填词功能与学词途径的改变
晚清词坛以临桂词人群体为首,这一词人群体在晚清词坛的一系列词学活动不能以简单的文学活动目之,其挟裹的政治目的与政治能量不容小觑。他们的词学主张与活动在清末那个特殊的社会环境中被激发,催生出了晚清词学创作的高潮,从中产生了不少填词名家,诸如朱强村、况周颐、郑文焯、夏敬观、易孺等人。民国初年由于南社的文学活动频繁,旧体诗词的创作也仍然活跃,如吴梅、王蕴章、庞树柏、陈匪石等人都是民初词坛的后起之秀。但随着1915年前后新文化运动兴起,1917年南社解散,旧体诗词的生存空间渐趋狭窄,加之填词创作门坎较高,词体逐渐退出主流文学的舞台。对这个问题最为敏感的,正是在清末民初词坛上活跃的这群词人,他们是词事鼎盛时期的过来人,同时又在民国有着为时不短的词学活动,更为敏锐地感知到了填词创作日渐式微的趋势,况周颐就说“乃至倚声小道,即亦将成绝学,良可慨夫。”最先被重新审视的,是填词一门的现实意义,也就是“为了什么而填词”。
(一)重新认定词体功能
晚清的临桂词人群体是一个特殊时代造就的特殊群体,吴熊和先生总结该派的聚合是“基于倾向维新与究心词学的相同兴趣”,是极为恰当的。以王鹏运为代表人物的临桂词人群体,将常州词派的经世主张与词学创作糅合于一体,强调填词创作所应承载的社会功能与政治意义,并藉由词学活动与政治活动的相辅相成,振起晚清词坛。但进入民国纪元后,无论是帝制还是维新都成为了过去式,这群词人无论出于主动还是被动,都已远离政治生活,甚至被排除在新时代之外,具体到填词上,他们信奉的那套经世致用的创作主张已与现实生活格格不入,因此对于填词创作在新时代新环境中还保留哪些价值功能的问题,与遗民词人最为切身,在他们的词话中被关注得最多。其中最有代表性也最能体现出词体价值认知转变的,是况周颐的《蕙风词话》。
况周颐作为临桂词人群体的代表人物之一,清醒地看到,在时代风气的转换下高论词的社会功能已显得多余了,和常州词派的前人不同,他在《蕙风词话》中并没有肆力抬高词的文学地位,而是直言“词于各体文字中,号称末技”,但末技也有末技的存在价值,《蕙风词话》重新界定填词创作之于个人的价值与意义曰:“吾性情为词所陶冶,与无情世事,日背道而驰。”填词不再是为了“托志帏房,眷怀君国”,而是为了“养成不入时之性情”,是摒弃无情世事、自我高蹈的精神追求,或许也是旧词人与时代洪流相对抗的唯一途径,也就是“夫词者,君子为己之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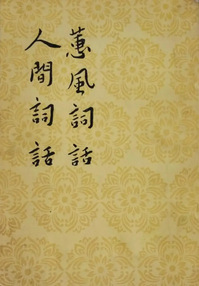
况周颐更进一步将填词回归为儒家士大夫个人的修身之道,《蕙风词话》的创作论中强调襟抱和性情,何为襟抱,他举了一个例子:
宋王沂公之言曰:“平生志不在温饱。”以梅诗谒吕文穆云:“雪中未问调羹事,先向百花头上开。”吴庄敏词《沁园春·咏梅》云:“虽虚林幽壑,数枝偏瘦,已存鼎鼐,一点微酸。松竹交盟,雪霜心事,断是平生不肯寒。”二公襟抱政复相同,一点微酸,即调羹心事。不志温饱,为有不肯寒者在耳。
他认可的“襟抱”是某种无法被艰苦生活所消磨掉的高远志向,也是不向残酷现实低头的倔强,所谓“贫贱不能移”者也。那么何为“性情”?《蕙风词话》在论程文简时,评其“性情厚”,评刘文靖词“以性情朴厚”胜,又引王半塘论《樵庵词》之言“朴厚深醇中有真趣洋溢,是性情语,无道学气”,可见所谓性情,是儒家所追求的温柔敦厚之品格,而这种品格不是假惺惺的道学气,是歌哭悲喜的人生状态,是真趣。襟抱与性情与其说是填词的先决条件,不如说是况周颐藉由填词打造的一个理想的儒士形象,因此况周颐将填词精进的过程视作儒家的修身之道,曰:
问:填词如何乃有风度?答:由养出;非由学出。问:如何乃为有养?答:自善葆吾本有之清气始。问:清气如何善葆?答:花中疏梅、文杏,亦复托根尘世,甚且断井颓垣,乃至摧残为红雨,犹香。
善葆清气,出自《孟子》“吾善养吾浩然之气”。《蕙风词话》中填词一事所承载的“言志”功能继承的是传统儒家诗教的另一面,从批判现实回归修身养性,其中固然有超然通脱,更多的还是遗世独立的孤寂与失意。这种填词功能论是传统士大夫“立德、立功、立言”三大理想都落空之后,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观点在词学上的观照。
况周颐《蕙风词话》是民国词坛的重量级词话,也可以说是常州词派理论构建的收官之作,主张弱化词的“言志”的社会功能,转而强调词对个人情志的抒发作用,可以推断晚清的词学创作论已经面临无法适应新的时代要求,亟需自我调整的困境。
(二)探索新的学词路径
事实上,民国时期除了少数遗民词人外,无论是词话也好词学论著也好,已经鲜少有作者关注填词的现实意义,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如何挽救这门末技上。如果说况周颐《蕙风词话》着意于改写填词在功能层面上的标准,那么更多词人则是留心填词技术上的门坎。20年代后晚清词人渐次离世,懂填词的人越来越少,老一辈词家感受到了词学逐渐被主流文学所放逐的寂寞,如蒋兆兰在《词说》自序中如此感慨道:
嘅自清命既讫,道丧文敝,二十年来,先民尽矣。独有强村、蕙风,喁于海上,乐则为天宝霓裳,忧则为殷遗麦秀,是可伤已。乃今岁初秋,蕙风奄逝,吾道亦孤。
因此重振词学的希望寄托在后学身上,他在自序中介绍《词说》的创作缘由时说:“诸生以老马识途,时时从问词法,兼求词话,奉为准则。”但是“又虑近世学者根砥不具,则枝叶不荣。”事实上,向蒋兆兰问学的吴梅、陈去病等人,都是旧学底蕴深厚的文人,这里的“近世学者”更多是指接受新式教育成长起来、对旧学较陌生的青年学子。
晚清词坛的审美风尚简略言之,是选涩调、讲四声、重故实、炼字面,推崇《梦窗词》,这种风气在民国初年演至顶峰,所谓“近世学梦窗者几半天下”,但这种创作审美对创作者的学力要求极高,绝大多数仅仅是东施效颦,作品也多生硬雕琢、晦涩饾饤。另一方面,白话文兴起,大众迅速接受了这种通俗明白的行文方式,同时随着文言文和旧体诗词逐渐离开日常生活,不要说填词,甚至知晓词调的基本格律、明白词中典故的人都越来越少,词逐渐变成一门远离现实的传统文学技艺,面对这样一种“曲高和寡”的困境,倚声家们开始考虑如何降低填词的门坎,为这门绝学保留一线生机。
首先是对清末民初的词坛风气进行反思,主要是反思“梦窗热”影响下过于强调技法和学问的创作倾向,尤其是针对“严守四声”和“堆砌典故”这两个症结。
早在20年代的词话中就已有清遗民词家试图对“梦窗热”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行补偏救弊,宣雨苍在《词谰》中明确反对同时代词人吹捧梦窗、以涩为尚的风气,并以朱强村的词为例谈堆砌雕琢的弊端:
近日词家争相祖述(吴文英),饾饤写来,几不成语。尝见今世奉为词伯者有传句云:“窣波钟动,归去连钱,蜻蛉催泛。”可谓涩矣,然“窣波”何不径用“佛楼”?“连钱”何不径用“花骢”?“蜻蛉”何不径用扁舟?使读者可以豁然意爽,仍未见其稍倍词旨,必欲强借名词,一一帖括,好为其难,毋论矣。乃并其强借之名词,不求甚解,是诚大可怪也。试为正之,如“窣堵波”为梵语,译即塔也。塔非藏钟之地,钟则别有钟楼。而“窣堵波”一句梵语,尤断不能截去“堵”字,但用“窣波”,致不成语。即彼或曾见前人有误者,以为是有所本,而不知为一盲引众盲,相牵入火坑也。彼执词坛牛耳者传作且如此,世之依草附木,自号倚声家,更可知矣。
“窣波钟动,归去连钱,蜻蛉催泛”三句出自朱强村《烛影摇红·月夜泛舟里湖,遍串六桥并丁家山而归,山椒一园,歌鼓彻曙》,作者直接将矛头指向“梦窗热”的“始作俑者”朱强村,认为词坛名家犹如此,何况学力普通的一版词人呢。夏敬观也说:“今之学梦窗者,但能学其涩,而不能知其活。”遗老尚且如此,稍微的词家则更普遍地意识到到了其中的弊端,吴梅在《词学通论》中教授如何填词,就提醒曰:“近人喜学梦窗,往往不得其精,而语意反觉晦涩。此病甚多,学者宜留意。”很明显,有经验的词家都意识到了学梦窗之“质实”与“涩”是需要学力门坎的,并不适合当下的学词者作为心慕手追的目标。
“守四声”也是同样的情况,《柯亭词论》认为“守四声”是填词的进阶课程,曰:
词守四声,乃进一步作法,亦最后一步作法。填词须不感拘束之苦,方能得心应手。故初学填词,实无守四声之必要。否则辞意不能畅达,律虽叶而文不工,似此填词,又何足贵。
龙榆生也认为选涩调、守四声会影响词中情志的抒发,他曰:“以此言守律,以此言尊吴,则词学将益沉埋。”蔡嵩云与龙榆生均是词学教育家,执教于高校,因而更加能体会到严守四声给初学词者带来的障碍。
其次是探索更适合初学者的学词路径。周济提出的“问涂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一直是常州词派创作论中教科书级别的学词路径,其立足点在于南宋词的立意、笔法、结构都是有径可取的,其艺术技巧可以靠揣摩、模仿进行学习,但在词学面临中绝时,词学家开始反思这条路径是否还适合当下的学词者。
夏敬观在《〈蕙风词话〉诠评》中明确批评这种路径是颠倒因果说:“止庵谓问涂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乃倒果为因之说,无是理也。”《诠评》更进一步反对初学者从南宋入手,先以常州词派两位代表人物张惠言与周济为例,一针见血指出常州词派理论强势而创作弱势的症结所在,借此说明为何不可学南宋词,曰:“张皋文、周止庵辈尊体之说出,词体乃大。其所自作,仍不能如其所说者,则先从南宋词入手之故也。”不可不谓大胆。
周济的“四家逆溯之法”长期以来被认可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大部分词人认为小令最难填,应该从长调开始学习如何铺叙、构架、声律等基本技巧,而南宋词以长调为主,北宋词以小令为主。但是由长调入门,所需要学习的格律知识、笔法技巧、典故史实等颇费功夫,需要较为扎实的文史基础。
因此《词说》主张学词之前要先学作诗,曰:
初学作词当从诗入手,盖未有五七言不能成句,而能作长短句者也。词中小令,收处贵含蓄,贵神速,于诗之七绝最近。慢词贵铺叙,贵敷衍,贵波澜动荡,贵曲折离合,尤与歌行为近。其他四五七言偶句,则近于律诗。是故能诗者,学词必事半功倍。
因为诗中五言、七言律句,都是词中常见的,先熟悉律诗的声律格式,遣词造句,了解旧体诗词的创作规律。第二步才是填词,“初学作词,如才力不允,或先从小令入手”,因为有学诗的基础在前,如果天分高的话,易得名隽之句,接着才学填慢词中格律较宽、束缚较少的词调,最后才是精研词律声韵,尝试孤调、僻调。这样的学词法显然是针对没有旧学根砥的新学人而发,从作诗开始补旧学的基础课。

三、新式词学教育影响下词话的功能分化
无论是重新考察填词的功能,还是探索“逆溯之法”以外的学词途径,大多仍属于常州词派内部的创作论修正,对于这种修正最为积极的大多是清遗民词人,他们虽然能感知到填词创作的式微,但并不直接面对新式教育和青年学生。而生于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主要人生经历和活动在民国的这一辈词人,譬如刘永济、吴梅、陈匪石等人,他们与晚清名家多有师生之谊,旧学根底深厚,兼擅倚声,在20年代后进入高校,成为身体力行教育新模式的一代学者,他们率先创立的讲稿式词话,大力促进了民国词话的“填词”离场。
为了适应新式教育下的施教需求,“低门坎学词法”开始代替从前以技法风骨笔力为中心的创作论,这种替代与转变体现在形式上,则是条目清晰的知识结构代替了随性零散的片段式文本。传统词话创作的体例多半是漫谈随笔式的即兴抒发,其内容包罗万象,创作论范畴论鉴赏论统统包含在内,全凭作者喜好自由发挥,不仅缺少系统性框架,理论陈述也比较抽象。但是随着词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走入课堂,传统词学家著述的目标群体变了,面向的是不了解词的学生群体,同时西方学术体系的引进带来了高等教育中的学科细分,具体到词学一门,“词学”这个概念也细分为多种课程,以1928至1929学年的国立暨南大学为例,共有四门涉及词学的课程,分别是“词学”“词曲通论”“中国词史”“专家词”,在以具体的教学目标为主导的课程体系中,传统词话自然无法匹配新出现的词学教育需求。
因此,进入了一个词话体例的转型期。以身在高校的几位词学家的词学讲稿为例,体例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偏重词学教材与讲义,主要以传授词学知识为目标,另一种仍是传统词话,充满兴会所至,信笔拈来的个人感悟,不过二者之间并非泾渭分明,词学教育尚在起步阶段,讲稿没有现成的范式标准,加上大部分授课教授都深得旧学熏陶,因此难免将词话的笔调带入讲稿的撰写之中,使得这些讲稿类词话大多介于由词话向论著过渡的一个模糊的形式中。但在这个略显混乱的转型期里,有一个特征是非常明显的,就是“填词基础”与“词学研究”被区分开了,这里所说的区分,不仅包含某独立文本中两种内容的区分,也包含不同著述层面上的区分。
(一)讲稿词话中“填词”与“词学”的区分
先来看同一文本下的“填词”与“词学”的区别,这主要体现在作为课程讲稿使用的词话之中。词学教育家在20年代已经注意到了随着学科愈来愈细,如何填词与词学研究也逐渐兵分两路的现实。寿鑈在授课所用的《词学大意》中曰:“词人未必工于论词,工于论词者,其词又未必工。”在高校教学的需求下,很多教材已经在“学词”和“词学”上做了区分。譬如《海绡说词》是陈洵在中山大学任教时的讲稿,主要内容分为通论和名家词作赏析两部分,通论主要谈及填词的一些基本素养,譬如“师周吴”“志学”“严律”等,赏析部分包含《梦窗词》《片玉词》《稼轩词》三家词的详解。可见虽然纯用传统词话的体例,但将创作与鉴赏稍作了区分。

吴梅的《词学通论》又更进一层。《词学通论》是吴梅于1922年秋至1927年春在东南大学任教时的授课讲义,全书分为“绪论”“论平仄四声”“论韵”“论音律”“作法”“概论”六部分,其中“概论”又分为“唐五代”“两宋”“金元”“明清”四章。“绪论”共10则,体例全依照传统词话而来,开篇首则即曰:“词之为学,意内言外。”然后谈词的源头与词体的特征,接着依次论词与诗、曲在创作中的区别,小令、中调、长调之划分的误区,词中调同名异者,填词的协律与用字发意,咏物词,是否需要严守四声,词之用韵,词之择题等,这个顺序,其实就是学习填词由浅入深的一个路径。是一个关于“如何填词”的基本内容。绪论部分,精炼简要,深入浅出,与旧体词话无异。而后面绪论的逻辑上细分为几个章节,是偏重词学研究的内容,凸显条理,又添加表格与小目录,便于学生理解,兼顾授课的需要。
又例如刘永济的《诵帚堪词论》上卷为“通论”,分为“名谊第一”“缘起第二”“宫调第三”“声韵第四”“风会第五”五个部分,下卷为“作法”,分成“总术第一”“取径第二”“赋情第三”“体物第四”“结构第五”“声采第六”“余论第七”。不难看出,与吴梅的《词学通论》相似,《诵帚堪词论》上卷主要是词学知识传授的部分,下卷紧扣词旨与词法的,属于创作理论叙述。
因为是用词话形式写成的讲稿,又常作为词话发表,姑且可称为“讲稿词话”,这种新兴词话首先改变了词学创作论的内涵,使“离场”更为直接,使批评论析更为具体深入。当然,在过渡期里,这些讲稿并非一刀切式的泾渭分明,部分论述并不能完全割裂“填词”和“词学”两者。只能说大部分作者意识到了传统词话本身的无序杂乱也与高校教育的专科化、学术化的趋向背道而驰,并有意识地在讲稿中将二者进行了区分。
(二)作为一门独立技艺的“填词”
“填词”与“词学”的分离并不仅仅发生在高校词学课程之中,既然讲稿已经在区分二者,“填词”进而从讲稿独立出去,出现了围绕“如何零基础填词”的一系列学词工具书。这类工具书的体例介于词话和讲稿之间,同样可视为民国词话朦胧转型状态的某个横截面。“填词法”著作兴起的首要原因自然还是出于词学教育的需求,很多词学课程都包含创作的考察,如刘毓盘的考试办法就是“只要你填一首词就是。”冒广生也说:“庠序之子非学词无以卒业”,可见会写词也是当时课堂上的一种刚性需求。另一层原因则是出版业的发展带来了更激烈的商业化竞争,诸如大东书局、世界书局、崇新书局等以民营资本为主的中小出版机构,在商业运作方面都非常积极灵活,图书策划与推广都以读者的需求为中心,其中也迎合了词学教育的需求。各种“零基础填词法”应运而生,成为民国词坛一道独特的风景,例如吴莽汉《词学初桄》、傅汝楫《最浅学词法》、顾宪融《无师自通填词百法》、刘坡公《学词百法》等。这批工具书的出现,代表填词成为了一门传统技艺,完全告别“经世致用”和“词史”这些创作论概念,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是普及性强,面向普罗大众,从富有吸引力的书名就能看出,这些书是供初学填词者使用的,而且有诸如“无师自通”“最浅”这一类略显夸张的宣传标题,旨在吸引完全不曾接触填词的新手。《无师自通填词百法》的《自序》中道:“兹编之辑,即为初学诸君作向导,故陈义不尚高深,遣词务求浅显”,一语道出这类启蒙词话的卖点。
其次这类填词法体例新颖,首先通过安排目录章节,使得全文条理清晰,具备系统学习的便利。为了初学者考虑,各书一般都会涉及词的起源、词体与其他诗歌体裁的区别、宫调与四声五音的基础知识、词律与词韵的工具书与检索方法、历代词人词派点评、词调范式(或词谱)这些内容。而且在结构安排上,不仅分了章节,在大标题下还有细分的小标题,不可谓不细致,而且检索方便,初学填词可能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作者都提前想到了,令读者可以将其视作词学的百科全书,有问题只要对照相关条目,就可以寻得解答。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这些填词法在体例上有所创新,但内涵并未脱离传统词话的范畴,文本中词话与词学论著之间的界限十分模糊,以《词学初桄》为例,全书的主体部分其实是模仿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的词谱,可以不论,前面绪言分16个部分,如果拿掉题名,也就是普通的16则词话而已。再如《无师自通学词百法》,上卷论词旨词法,下卷品评历代词人,虽然都单独附上“xx法”的标题,内容与传统词话别无二致。在这一点上,“填词法”与诸如《词学ABC》《词学常识》这种词学论著形式的通识读物有着显著区别,后者是以论文体例或教材形式章节构成的著述。
(三)剥离“填词”后的词话
既然“填词”一门已经另立门户,那么抛开创作论的传统词话,自然在内容上也发生了重心的转移,一方面是减少抽象零散的理论建构,另一方面是将重心转向如何阐释、赏析作品,这一点在作为教学讲稿的词话中尤其明显。
以《海绡说词》为例,虽然通论部分是阐述填词基础,但主体部分是“说词”,试举说《霜叶飞》(断烟离绪)一例:
海绡翁曰:起七字,已将“纵玉勒”以下摄起在句前。“斜阳”六字,依稀风景。“半壶”至“风雨”十四字,情随事迁。以下五句,上二句突出悲凉,下三句平放和婉。“彩扇”属“蛮素”,“倦梦”属“寒蝉”。徒闻寒蝉,不见蛮素,但仿佛其歌扇耳,今则更成倦梦,故曰“不知”。两句神理,结成一片,所谓“关心事”者如此。换头于无聊中寻出消遣,“断阕慵赋”,则仍是消遣不得。“残蛩”对上“寒蝉”,又换一境。盖蛮素既去,则事事都嫌矣。收句与“聊对旧节”一样意思,见在如此,未来可知。极感怆,却极闲冷,想见觉翁胸次。
《海绡说词》的主体部分均如此例,即将一首词拆开,细究字句与其中布局关联,梦窗与清真词层次丰富,前后勾连,对于初学者来说的确难解,陈洵自己也说:“吴词之奇幻,真是急索解人不得。”这就给不熟悉旧体诗词的学生带了不小的审美障碍,但《海绡说词》不仅在章法结构上说得非常细致,而且关于用字下语也评点得深到,首尾照应,勾连阕,有种作品串讲的意思,大不同于传统词话涉及作品的三言两语而不易得要领,也可说是兼顾词学教育的一种创新,这番细致解读之下,整首词的词意、笔法、结构、艺术特色都清晰无疑。

除了内容方面向鉴赏倾斜,体例上也为方便读者进行了改良,如陈匪石的《宋词举》,此书集词选、词话于一身,先录作者小传与词集版本源流,再集前代名家评述,再录词作,词作中标出韵位,每首词后有“校记”、“考律”、“论词”三科,“校记”主要记录各个版本中的异文。“考律”一栏,一般先溯词调起源、词牌别名,再根据此调字数析其数种体式,细析每一体的平仄、句法区别。“论词”是词作赏析,极为详细透彻,短则四、五百字,长至一、二千字,逐字逐句分析句法、字面、结构之要领,另掺杂词本事的记述与对词境的体悟,偶尔还会与其他词人或词作相比较,优劣互见。此三科是传统词话批评中常见的论词主题,但这些主题散见于旧体词话中时,经常是支离破碎,让初学者摸不着门路,往往“知句而不知遍,知遍而不知篇”,陈匪石评价前人词话,也委婉指出张炎、沈义父、周济、陈廷焯、况周颐等人的词话“咸有伦脊”。
《宋词举》中别出心裁地将这几个主题以词作为中心贯穿起来,几乎囊括了解一首词所需要的全部因素,其详尽程度,民国再无词选能出其右,唐圭璋评价此书:“自来选词者,无举词详析之例,有之自匪石先生始。”可见其首创之功。

教育者的对面是学生,如果说老一辈词学家通过多方改良传统词话使其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并为后人打开了词学鉴赏文体的先河。那么作为接受者的晚辈后学,在词话中则更多地体现出现代词学研究的端倪。
例如唐圭璋先生的《梦桐室词话》,这部词话是他整理辑校《全宋词》的副产品,绝大部分内容为词学文献勘考,且多属于宋词的文献范畴,大致可分为作品辑佚、作者考辨、版本溯源、订误辨伪等几大类,其中发明最多的是辨伪条目,如“明人伪作陆放翁妻词”“《学海类编》中所收之伪词话”,又多有对宋词作者的考辨订误,如订正误署杨妹子而实为张抡之作的《题马远松院鸣琴图》,考辨鲁仲逸即孔方平,一首词作,一位词家,皆辨析有据,发覆无疑。有时往往是作品辨伪与作者考定并行,在指出周邦彦的《水调歌头》“中秋寄李伯纪观文”一阕是伪作后,又找出此词真实作者为何大圭,所谓“既明其伪,复补其缺,是亦快事也”。在辨析《词林纪事》所载的文天祥《南楼令》时,唐圭璋感叹道:“乃知后人引用前书,往往不足据,非复校原书不可。”这真是个中人甘苦之言,会心之得,可引以为校勘学不刊之经验谈。因为词话所固有的体例特点,《梦桐室词话》没有展示繁琐的考辨过程和数据罗列,但同样利用词话简明扼要的笔法,三言两语论析清晰,使读者有线索可寻,有依据可凭。
《梦桐室词话》的文献学主旨纯粹,内容集中而丰富,这在词话发展过程中是值得关注的一个内容与形式的突破,本可以用文献著作形式来讨论的问题,却采取了更为轻便简捷的词话形式来表达,一来是将平日校勘点滴所得作一番随录式笔札,二来是大型总集不便揽入的文献稽考内容自当整理,另行刊出,对于现代词学研究的辑佚之学有重要意义。
同样富有代表性的是萧涤非先生的《读词星语》,该词话发表于1929年的《清华周刊》,是萧先生在清华就读期间的学词心得。全文连“小引”共66则,每则前以词人姓名为标题,对词人评价不着意于褒贬,而是着眼与词中佳句的出处与注解,“颇有为前人所未发,亦间有与旧说相补证者。”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不谈词旨,不涉词史,也无关声律与风格,单从文本字面锲入,探求词句来源,专心于名句的出处,这是《读词星语》的一大特点。尤其深细妥帖的是论周清真《六丑》名句:
美成《六丑》蔷薇谢后作词,时而说花,时而说人,时而人花并说,极变化浑成之妙。其“钗钿堕处遗香泽,乱点桃溪,轻翻柳陌”,则仍是说花,非说人。《片玉词集注》引杜诗“神女落花钿”,失其旨矣。唐徐汇《蔷薇诗》云:“朝露洒时如濯锦,晚风飘处似遗钿。”词盖本此。全词“似牵衣待话,别情无极”,陈注缺,余按储光羲《蔷薇歌》云:“高处红须欲就手,低边绿刺已牵衣。”
其中体现了诗话的某种传统因素,即论者专注于文本的祖述与溯源。中国文学的语汇、字句、典故等等,历代流传,袭用变化,形成既有祖述又有创新的文学动态。“诸引文证,皆举先以明后,以示作者必有所祖述也。”所谓“文证”,即把原文出处揭示出来,“举先明后”本是诗文评注的重要概念,也是传统诗话文论普遍使用的方法,宋代以来,诗话流行,其中引诗摘句,溯其由来,更是不胜枚举。只不过词话晚出,专论亦少,尤其晚近以来,在崇论寄托、杂谈佚事、标举风格的词话中,像《读词星语》这种避免零碎,单纯专一于文句祖述的词话未曾经见,因此显得独特而可贵。除此之外,《读词星语》擅长以诗证词解词,这需要论者的诗学功底,不仅是文献考据校勘之方法,也是词体研究的一大入手处。《读词星语》突破前人的词话范式与内容,注重词与诗的渊源关系, 既是古老诗学传统的研究途径,也是崭新的词学方法。
师生同样沿用传统词话的体例,又各有侧重点与创新之处,也透露出词话这种传统文体在现代词学替代传统词学时所保留的另一种可能性。
四、余论
传统词话同时承载词旨、词法、词律、文献版本、填词技巧、创作风格、审美鉴赏等多种词学项目,是一种大杂烩式的文体。随着倚声创作在民国文坛的日渐没落,词话也开始发生变化。先是从理论修正的角度重新审视“填词”的功能与价值,并反思晚清以来过分强调技巧学力的创作导向,这种变化还只是发生在词话的内容层面,但随着词学教育成为高校教育课程的一部分,“填词”与“词学”分道扬镳,创作论从词话的内容中逐渐剥离开来,独立成为一门传统国学手艺,这种分割体现在了词话体例的层面,词学讲稿与填词工具书是最能体现这种形式上的变化的,剜去“填词”后,偏重科学系统的研究论证主要由现代词学专著或论文承担,词话内容开始向批评鉴赏的方向倾斜了。
以上是本文试图考察的民国词话中“填词”的离场过程,但历史的发展是充满复杂性与多样性的,“填词”的退场不能简单代表传统词学的末日,现代词学的肇兴也并非仅仅从新思潮而来,单一的脉络叙述虽然适合梳理历史发展的重要线索,但也难以全面观照其间的细枝末节。
胡云翼在《词学ABC》中论其书主旨时说:“我绝不像那些遗老们,抱着‘恢复中国固有文学之宏愿’,来‘发挥词学’的。”又说:“我这本书是‘词学’,不是‘学词’……我不但不会告诉他一些填词的方法,而且极端反对现在的我们,还去填词。”这当然是一种未免极端的观点,但也从中看出新派词学家“重解不重作”的一种集体态度,民国时期有很多类似态度的词话,作者主要是新青年学子,以鉴赏品评以及追溯词的历史为主要内容,但由于缺少旧学根基,因此评价范围大多很狭窄,作者上主要关注唐五代与北宋词人,体裁上以短小但有余韵的小令为主,而且解词的手段比较单一,无非是强调情感真挚,自然隽永。其背后的原因,在于新文学帽子下的词学核心概念非常贫瘠,无法从“境界说”或是“白话说”上演绎出更完整的理论学说,所以只能不断重复车轱辘话,所以很多新派学子的词话照搬王国维、胡适二人的理论,甚至直接大段抄写,质量非常粗糙。
而围绕创作展开的传统词论则不一样,其中充满感性体悟与各种抽象概念,适合进行阐发和二次解读,更能根据现实创作的需求不断进行调整,生发出新的理论主张,这种“活的”词论的基础,在于不同时代不同作者不同文学思潮下创作实践的千变万化,所以即便“填词”退场,词学批评仍需要吸取传统词学中的见解,尤其是艺术形式上的一些表达,譬如俞平伯《读词偶得》中大量借鉴常州词派的概念,呈现出更丰富深邃的词学批评风格。而老一辈词人一方面尽量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在传统词话的范式体例上进行了调整与创新,这些新变成为现代词学形成道路上的基石,但是从词学立场而言,他们并没有听任“填词”的退场,而是希望引导后学藉由学习和鉴赏重新回归填词创作,如陈匪石在《宋词举·叙》中说:“盖欲学者触类旁通,由是而能读、能解,驯至于能作,悉衷大雅,毋入歧途。”《最浅学词法》虽然是工具书,其撰述目的也是出于“恐阅数十年,难免如高筑嵇琴,绝响人间矣,心窃忧之。”在词学中绝之时所保持的这份守先而待后的态度,为现代词学研究注入了愿景的光彩。
(原载《词学》第49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6月版,注释从略)

【作者简介】
戴伊璇,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词学、近代文学。在《词学》、《齐鲁学刊》等刊物发表论文数篇。
主编:朱生坚
编辑:曹晓华
运维:任洁
制作:小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