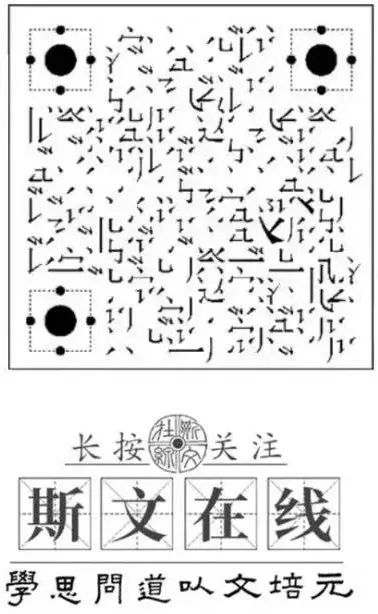一、从卡佛说起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内对卡佛的译介与研究开始起步。1992年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的《雷蒙德·卡弗短篇小说集》,成为90年代最早且流传范围最广的卡佛作品集。一些介绍卡佛生平与创作经历的传记类文章被翻译、刊载,卡佛的底层生活经历、作品中的“温情”与对年轻一辈美国作家产生的影响为人们熟知。他“完全舍弃了浪漫的自我主义”,强调“文学可以从严格观察真实生活中得到形成”,“在学院派超小说模式占优势的时刻……使现实主义短篇小说的形式重新得到了活跃”。与此同时,“手艺人”卡佛也为中国青年作家注目,或批评或推崇,成为90年代以来青年作家身份意识的镜像。
卡佛进入中国的时间正是新写实主义兴起的时间,时间与风格的暗合成为作家们评说卡佛创作的前结构。在先锋成为“传统”之后,青年作家们实际从未放弃过对方法论与世界观关系问题的思考。新写实呼啸而来,其零度叙事的态度与日常生活摹写,使得叙事者的位置乃至作家的人格构型成为评论家们关注的重点。在激进的形式实验“消弭”后,什么样的写作才能贴合世纪末情境,对光怪陆离的“现代”“后现代”景象做最传神的刻画?作家应秉持何种精神立场、叙事立场来应对先锋退潮后的芜杂?卡佛的极简风格的流行与作家故事的流传,既是一种影响焦虑下的叙事新变,也是作家们在先锋退潮后小心翼翼寻找个人身份位置的表征。手艺人还是殉道者?观察者还是参与者?赓续形式试验还是转向宏大叙事?青年们对卡佛小说技艺的评说,不止关涉当下创作现实,还关涉技与道的辩证法这一文学的永恒议题。
从20世纪50至70年代的“文艺工作者”“灵魂工程师”到先锋作家、“手艺人”,纯文学的“诞生”不仅改变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轨迹,也改变了社会与作家个人对身份、角色的认知。21世纪卡佛短篇小说一度风行,旧闻者与新知者奔走相告这一“所罗门宝藏”。“70后”作家徐则臣则说“卡佛没那么好”,短篇小说需要精致的留白和粗糙的毛边,卡佛“只是在方法论上做得比别人更极端一些”,因此“短篇小说在卡佛这里变成了别致和另类的模样”,这是个形式,也即方法论问题。成为大师需要技术与世界观并重,当然也有仅凭世界观傲视群雄的大师。“而卡佛,在他小说的背后,我看到的是他无限地接近于我们看待世界的眼光。他缺少我理想中的大师当有的世界观。”2019在《中华文学选刊》发起的“当代青年作家问卷调查”中,许多作家在“有哪些作家对你的写作产生过深刻影响”的提问下给出了卡佛的名字:“在写作的初级阶段,从他那里学了不少写作的技巧。”“卡佛教会了我收敛。”“卡佛:他影响了我的语感。”“雷蒙德·卡佛——极简语义学以及小说的阴阳双面法则。”“不知道小说该怎么开头就翻一翻卡佛。”由此可见,在一切文学资源都成为传统的当下,作为小说“手艺人”的卡佛为青年作家青睐,徐则臣对卡佛没有提供独特世界观的“指责”,似乎也反向证实了卡佛短篇小说方法论在受众心中的地位。卡佛在中国的出场与成为文学传统后对他的“再解读”,昭示了先锋落潮后写作主体想象的更迭。卡佛在《论创作》中强调的,作家应创造属于自己的世界观,反而在对他的阐释、想象中逐渐剥落,其方法论而非世界观为人们注目。青年作家们对自己所接受的来自卡佛的影响的追认,也是从写作技术而非写作伦理方面进行的。或许可以这么说,在当代要想成为一个青年作家,首先要成为卡佛式的“手艺人”,寻觅到短篇小说的流行“风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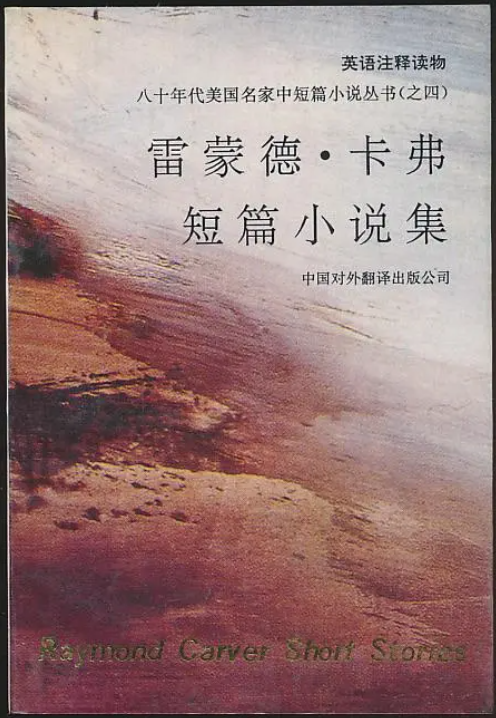
从对卡佛接受史与作家形象变迁史的简要梳理中,我们或许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手艺人”叙事深刻影响了90年代以来的青年创作,纯文学仍旧是这个时代的“宏大叙事”。陈思和曾借用“中年写作”的诗歌术语,指称90年代以来当代文坛呈现出的创作风貌:激情褪去了,活力凝滞了,“中年危机”悄然出现。陈思和认为90年代末韩东等人的“断裂”行动、卫慧棉棉的小说创作等实则延续了五四的“青春”主题,但文学已进入中年阶段,秩序而非反叛更为主流话语所需要、所接受。80后一代则完全脱离了传统秩序,与媒体、网络共生。“中年危机”由此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某种元叙事,或表征为“自我的神话”,或表征为“内卷”与“倦怠”,“青年性”与“共同体”的召唤亦同步出现。卡佛为何流行?或许是因为其极简小说技巧与“手艺人”形象,恰恰暗合了中国当代文坛的“中年写作”趋势。青年们仔细挑选着模仿对象,言说态度与写作姿态日趋保守,“先锋”成为遥遥的手势。是什么让青年们过早步入了“中年”?当代青年作家如何进行“自我”言说与“自我”保存,有着怎样的身份意识与身份困境?所有的一切,或许需要从景观社会中麦克风的数量讲起。
二、青年作家的“自我”言说
樊尚·考夫曼在《景观“文学”》中勾勒了作者成为“景观”的过程:文学史建立在“稀缺性经济”的基础上,在“注意力经济体制”,也即“丰饶经济体制”下,作者要面对来自其他媒介,如影像、音乐等争夺受众注意力的压力。当下的消费是一种“即时消费”,在这种消费模式下,注意力是一种稀缺的资源,作者也“泯然众人”,与电台DJ与脱口秀主持人一样,失去了“风格”和“权威”。罗兰·巴特笔下的“作者之死”象征着作者的荣光,“死亡”是对平凡化、标准化的文学生产的“抵抗”,是“先锋”的“绝唱”,“而这一文化正在渐渐失去重心,一开始它被视听领域征服,如今则屈从于数码技术”。相较于罗兰·巴特笔下的“作者之死”,网络时代青年作家面临着更复杂的身份困境,或因“公务化”而死:“公务化”“不仅涉及一种生活方式,比如作者必须出现在电视屏幕前,必须履行交流沟通的义务;同时也意味着我们都受到了新兴技术的影响,其中也包括作者:“我们是为技术而服务,让机器运转的公务员。”
而今是麦克风遍地的时代,作者不仅借助他人的麦克风宣讲,也创造自己的麦克风用以交流、发声。站在麦克风前不仅是作者的权利,也是作者的义务。由此创作谈成为文学生产的必要环节抑或说衍生物,或与作品绑定,如《青年文学》以作品搭配“问答录”的形式推出“90后”青年作家,《收获》刊发“青年作家小说专辑”的同时在微信公众号刊发创作谈以及批评文章为其造势;或与更具青年作家个人标识的传播渠道绑定,如在豆瓣上发表创作感想与评论,在个人公众号刊发创作谈文章,在微博等社交平台与读者互动,都是媒介更迭过程中涌现的新“微型”创作谈形式。
言说写作与“自我”言说,对尚在成长中的青年作家来说都不是简单的“工作”。李壮就曾言明:“我们在宣传自己的同时也在暴露自己、限囿自己,而当我们真正面对四面八方投来的关注目光之时,却又常常意识到完成自我辩解或者至少把自己说清,其实并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当个人借由媒介成为当下文学景观的碎片,创作谈中的“我”愈发暧昧。在文学生产愈加流水线化、产品化的当下,青年作家的个人形象建构也成了文学生产的重要环节,作家故事的流传与作家形象的建构将原本作家与读者的关系改造为明星与粉丝、崇拜者与追随者间的关系。不止是青年作家需要参与到这场大众狂欢中,余华、莫言等老一辈作家也从作品背后走出,走到了微博热搜、综艺节目中。“90后”“00后”的青年作家作为随网络成长的一代,在写作初期便借助网络发表创作,“评论区”这一产品设计,拉近了作家与读者间的距离,也让创作成为在互动中不断垦殖、拓展边界的数字文本,文本与作家个人的形象都是流动的,为大众凝视,也为吸引大众目光而持续存在。在何平、金理发起的“上海—南京双城文学工作坊”会议上,与会者多次谈到创作谈与青年作者“打包”的问题。方铁谈到要把创作谈与作品打包成整体来看,“打包起来之后才是一个完整的作品”,作者介入营销之中也是创作才能的体现,现在的写作外延宽广,“而这正是青年写作者更为如鱼得水、更为擅长的部分”。作为编辑,方铁从营销角度肯定了作家创作谈的创作,何同彬则从文学传统与创作现状的关系上揭出创作谈的某种虚构性抑或说表演性:“(很多年轻人)主要的才华都体现在给作品起篇名和写创作谈上了,张口闭口都是‘世界文学’的各种‘高级’经验”,作品却“跟他所娴熟讨论的‘世界文学’没有关系。”何平提及《中华文学选刊》“当代青年作家问卷调查”中“谁对自己写作影响最深”问题下村上春树的落寞,猜测“青年作家也许有各自不可告人的隐秘之书”。

2023年10月14日,“花城关注”栏目主持人、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平与复旦大学教授金理、《十月》执行主编季亚娅、作家张怡微做客南京先锋书店五台山总店,与读者们分享《花城关注:六年三十六篇》背后的故事。
作家个体对同时代人的认知,也是我们窥见外部世界对作家的建构与“修改”的重要窗口。在《中华文学选刊》“当代青年作家问卷调查”中有这样一个问题:“你关注同代人的写作吗?是否可以从中发现不同于前几代作家的群体性特征或倾向?”答卷中许多作家都提到了同时代人的精神困境与时代“诱惑”:“我们面对的信息前所未有地丰富,也承受着不同程度的裹挟。市场也好,舆论也好,三观审查也好,都太容易抵到面前,由此产生的保守和拘谨对创作来说不是好事。”“他们身上会不经意间散发出一种‘心口不一’的文学野心……知道如何隐藏自己,注重自我,言行举止精致、得体、圆滑,表面的敞开和内在的封闭丝毫察觉不出表演的痕迹。”“最怕的是一代人精神上的矮化和自我规训,或者被名利迷了眼,或者陷入极端化。”“失败青年”的叙事所表征的,青年作家的精神困境,与“市场”“舆论”“三观审查”等外部环境有关,环境变化的同时,青年作家的创作也向内收紧,外在的“自我”与自我认知间的裂痕增大,青年作家们不知不觉扮演起市场与体制期待的“角色”。与此同时,“80后”“90后”的代际差别在比较中浮现:“‘90后’整体来说还是乖一点”,“80后”“可以走期刊也可以走市场”,“‘90后’基本是走期刊,而期刊相对来说严格一点,所以大家也会把自己往里边收”。此外,游离于宏大叙事之外的个人写作,技术的精益求精与传统的内化,共同体的松散与“无名状态”也是青年作家们言说同时代人的关键词。
目下许多青年作家所进行的是一种精细、内向的个人写作,写作是个人生活方式的内化。与此同时,这一内向的写作出于各种原因不得不暴露在外界的闪光灯下,获奖后的频繁曝光、新书出版时的宣传活动、日常生活中与读者的互动,都让青年作家陷入“自我”言说的漩涡。作家个体与创作谈叙事者、小说人物间的关系暧昧不清,何谓“真实”,何谓“虚构”?青年作家在真实的创作谈中搭建“虚构”的叙事者,也在虚构的创作中还原“真实”的自我,真实与虚构、私人言说与大众阅读的界限被打破的同时,“自我”得以保存。
三、青年作家的“自我”保存
在物质愈发丰富、信息愈发纷杂的时代,青年作家的成长路径却呈现出某种相似性。麦克风的多样化与经历的“同质化”催生了青年作家的身份认同危机。“80后”作家张悦然就曾多次就个人创作乃至代际创作的特质发表看法。在《对70一代的嫉妒》一文中,张悦然将“70后”与“80后”的区别归结为“理想”与“友谊”,“70后”们为了“理想”与“友谊”聚集到一处,“80后”却失去了“凝聚力”与“根系”,“营养也无法互相补给”。在与霍艳的对话中,张悦然坦白“80后”一直受到“个人”“自我”的前认知结构与粗暴标签划分的困扰,这使得“80后”作家个体似乎永远无法离开“80后”作家群体独立存在。但与此同时,“把‘个人’从集体中分离出来”是“80后”作家的时代使命。不同于上一辈作家的全局观点,“80后”作家的创作是由特写展开的:“我们这一代人,仅就我个人来说,我似乎并没有这样的全局观。至少在一开始,不会首先想到这个人的阶级和社会身份。我首先想到的是这个人非常具体的处境和所面临的困难。”“到了我们这里,我们的集体概念瓦解了。”因此张悦然能直面《茧》缺乏历史感的批评,认为《茧》是一部以自己的方式去“记得”的小说。“匮乏”反而成为小说叙事的动力与可能的出口。

许多青年作家从“匮乏”出发,重构了关于“个人”“经验”“历史”的叙事装置。“自我”并非匮乏的同义词,相反,它是轰轰烈烈的历史事件远去后,个人重新抵达时代的重要方式。重要的不是经验,而是对经验的认知与表达,青年作家们据此发明了从“自我”出发,以虚构介入现实的创作模式。李唐将写作视作“理解世界与自身的过程”,沉迷于寻找答案是对艺术的损坏,寻找途中变化的风景才是写作的迷人之处,以“我”的感受经历为原点,不断深化对世界的理解,写作也将随之不断展开。王占黑曾说对自己而言,始终是经验在前,知识在后的,“想象(回忆)的世界,真实的世界,文学创作的世界”之间是畅通的,“文学的真实和虚构可以暂时(或永久)地模糊界限”。青年一辈对自己所成长的年代的艺术呈现,便是对父辈的最高献礼。虚构与现实的关系或许并不生发于写作之前,而是写作之后,故事会在存在于作品中后,与现实生活产生神秘的连结。王占黑想在大润发收银处扯一根线,将小说串起来供排队的人们阅读,空响炮的声音,也是在《空响炮》出版后才第一次听到。通过后续的“发生”与行动,作品有了回声,这是王占黑心中更喜欢的,“虚构影响现实”的方式。对大多数青年作家来说,“自我”是撬动世界的起点,它并不意味着情绪的沉溺,而是指向了生活的社区、从事的职业等具体的事物,城市漫游由此在许多创作谈中发生,作家们从寄身之所出发,用脚步丈量并拓展生活的边界。散步因而有了一种虚构意味,打通了“自我”与世界之壁,将其从“同质化”中拯救出来,细微反而成为一种力量。
与此同时,内向的写作催生出小说中的小说家,进一步模糊了真实与虚构、小说家与人物之间的界限。在《消失以后》中,鬼鱼为小说家剡扬设置了镜像人物——李懿。剡扬和女友田阡陌来到孤岛般的边境小镇,剡扬是个小说家,却被镇上的居民视作无业游民,李懿是两人的房东。在李懿眼中剡扬是个不折不扣的怪人,最终他意识到“不能将一切与剡扬有关的事物脱离小说而像对待普通事物那样对待”,对方显然不理解现实生活中的情感而活在虚构中;李懿描述的田阡陌的现实失踪场景,在剡扬看来是比三流小说家的作品更为蹩脚的虚构,甚至李懿本人,也像是虚构出来的人。田阡陌是二人的连接点,使世界的真实与虚构有了颠倒的可能,她向李懿解释剡扬创作中的癖好,她的失踪让彼此指认对方是虚构物的李懿与剡扬在现实世界中分工合作。李懿是生活中的小说家,他意识到世界在倒退,剡扬的创作也是倒退的表征,剡扬在自己是小说家的世界里生活,并在经历了田阡陌的失踪事件后意识到现实世界的荒诞与摇摇欲坠。而跳出文本,李懿和剡扬都是小说家的虚构。在林培源《一个青年小说家的肖像》中,“他”的朋友方晖在虚构与现实间来回穿梭,最终打破了主人公“他”关于写作、关于文学的“幻象”。“他”和方晖在酒吧结识,对方从他的小说中品出了贝克特的味道,但认为还缺少一些“蛮荒之力”。“他”跟方晖谈影响的焦虑,谈自己的创作“瓶颈”,在方晖出国后帮其照看房子,并在房中收获写作灵感,“他”终于明白,“原来他一直艳羡的不是方晖为艺术而奔忙的魄力,而是方晖原本拥有的优渥生活”。“他”为“招魂”而写作,却迷失在写作之路上,在写作中不断痛苦地自我审问:
他试着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是读的书太多且杂,撑坏了写作的胃口,以致思维的链条断裂?还是因为经验匮乏,消磨了讲故事的热忱?
“认识你自己。”他自问道,你认识你自己吗?知道自己是谁吗?一个小说家?不,你不是小说家,你只是普通人,你的人生没经历过大起大落,你没被命运踩在脚下,没吃过苦受过罪,凭什么称自己是小说家?
“他”在乡下出生,在影响的焦虑中不断摸索写作道路,惆怅自己经历的单薄与技术的未完善,所标榜与所遵循的却还是贝克特、弗洛伊德。小说中隐现的阶层主题,使得小说与更广阔的现实相联系:“他”是小说家,亦是“失败青年”的一员,“失败”后唯有返乡。在小说中,林培源详细摹写了“他”为自己画像的举动:“他想把自己住在方晖家的这段经历写成新小说,题目叫《一个青年小说家的肖像》。”“他无意间打破了‘你无法为自己画像’的规矩,想把自己塞进虚构中。”方晖归来,“他”在搬离前更改了故事结局,让故事里的“他”作为中学老师跳楼自杀,口袋里的稿纸既像遗书又像未完成的小说。“他”在虚构与现实间徘徊,并尝试为自己画像的举动,透露出青年作家在小说创作背后的身份焦虑。“一张未成熟便已脱落的脸”要如何勾画,如何言说?一切的虚构没入小说,又升腾于现实的海面上。

四、余论
樊尚·考夫曼曾这样摹写过去与现在作者“心灵回音室”的区别:
曾几何时,作者在心灵回音室可以用所有的时间去倾听自己的想法,将自身孤寂地抛入想象的空间,在那里塑造闻所未闻、意想不到的主人公,即便最终让房间变成一个“喧叫之地”也在所不惜。而今天,有许许多多“实时”跟踪作者的爱心朋友,他们在作者听到心灵深处的回音之前,便已经随时准备参与、讨论和修改了:马塞尔,删掉点吧,这里不用逗号,该用句号,你真让我晕!
吵嚷的“心灵回音室”还听得见作者的声音吗?或许在这个嘈杂的时代,我们才更需要借助作品而非作者这一媒介。这既意味着要对作品进行风格化、类型化的区分,在面对不同风格的作品时启用不同的批评装置,也意味着将作者从商业制作的流水线上“抢救”下来,给予他们表达或不表达“自我”的权力。鬼鱼、林培源等青年小说家笔下的青年小说家“你”“我”“他”,既作为“失败青年”序列中的一员存在,也因具有了小说家的身份而被赋予模糊虚构与真实,乃至从作品中破壁而出的势能。青年作家们在一切传统都已被转化为资源的当下,更重视内在“自我”,也因此不断对作为小说家的“自我”进行“审视”,历史的远去与现实的破碎,都使当下的青年作家有了不同于前辈的“焦虑”与“隐忧”。但与此同时,“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世界与传统均向青年作家敞开,“自我”的待生成,也是“转机”的待生成。
本文原刊《上海文化》2024年第4期,注释从略

【作者简介】
牛菡,女,1994年生,南京大学博士,中国矿业大学人文与艺术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制度、青年写作、十七年文学。
【新刊目录】
《上海文化》(文化研究版)
2024年第4期
专 题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上海实践
郑崇选 “第二个结合”与当代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巩固
黄力之 中国文化主体性与文化自信的历史逻辑
访 谈
李庆西 齐晓鸽 文学现场四十年——李庆西访谈录
理 论
章文颖 超越理性的“实存”——谢林美学中的存在主义萌芽
文 学
牛 菡 “自我”的言说与保存——90年代以来青年作家身份意识辨析
董外平 小资青年的前生今世:一份精神史的考察——论张柠的长篇小说“青春三部曲”
文 化
肖 剑 章心仪 算法时代的音乐品味:网易云平台的歌单策展研究
林 凌 曹浥霖 人人都能搞音乐吗?——透视新技术条件下“抖音神曲”的生产与流通
文 艺
朱恬骅 “另类”与“日常”:城市更新中的艺术空间
张苏卉 谭 然 微更新视域下社区公共艺术的生态性研究
张 磊 滨水工业遗存的艺术化更新策略——以上海“一江一河”为例
笔 记
张 生 “诗人与思想家的民族”——谈宗白华对德国思想的认识与接受
书 评
夏 天 西方学者对中国近代文物流失的历史还原与当代思考——评《掠夺的补偿:中国如何失去其宝藏》
编后记
英文目录
封二 周卫平《古镇夕阳》
封三 好书经眼录
《上海文化》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扩展版)来源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引文数据库来源刊
社长:徐锦江
常务副社长:孙甘露
主编:吴亮
执行主编:王光东
副主编:杨斌华、张定浩
编辑部主任:朱生坚
编辑:木叶、黄德海、 贾艳艳、王韧、金方廷、孙页
《上海文化》(文化研究版)
主办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地址:上海市中山西路1610号2号楼928室
邮编:200235
电话:021-64280382
电子邮箱:shwh@sass.org.cn
邮发代号:4-888
出版日期:双月20日
主编:朱生坚
编辑:曹晓华
运维:任洁
制作:小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