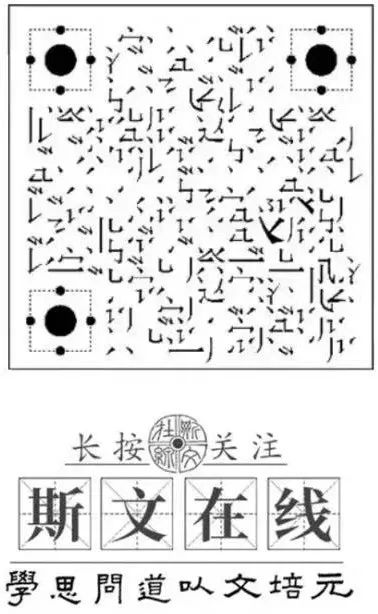在儒家思想中,“安贫乐道”是极为重要的精神旨归,大多学者从哲学史、思想史等角度对经典文本进行阐释。然而,由“安贫”的态度何以“乐道”,这种转化的内在逻辑是什么,可以追溯到何处? 从文化传播和思想生成的视角,在比较神话学的视阈中,借助“神话-仪式”的研究方法,可以构成窥探儒家思想来源的一条重要路径。文章以“儒,柔也”作为问题的切入口,将儒家原型与上古时期火焚帝王的神话和甲骨卜辞中“烄”的火焚祈雨仪式关联起来,发现上古时期的神话仪式孑遗与儒家的人生信仰之间的源流关系。
一、“安贫乐道”与儒的社会职能
先秦时期,儒家建构的“圣人”,总是以“安贫”为重要的人格特征,且“圣人”始终与“乐道”密不可分, “安贫”成为通达“乐道”的前提与考验条件。在儒家的经典文本中,反复出现圣人对“安贫乐道”的表述,如“圣人安贫乐道,不以欲伤生,不以利累己”“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刘宝楠《论语正义》释:“闻道而不遽死,则循习讽诵,将为德性之助。若不幸而朝闻夕死,是虽中道而废,其贤于无闻也远甚,故曰‘可矣’。”“子贡问:‘贫而无谄,富而无骄, 何如?’孔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论语·学而》)此外,孔子还提出,“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之议也”。他赞颂“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孔子提倡且大力推崇弟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 回也”。他要求“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在这句话中,“无饱”和“无安”正是“安贫”在身体上的具体表现,它们都指向了一个理念,即通过否定外在物质条件的恶劣,以此来成就和达到超越物质之上的精神性满足。

刘宝楠撰,高流水点校:《论语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然而,我们要追问的是:为何儒家君子在面对困厄和窘境时,依然保持对“道”的坚守。从发生学上看,“安贫乐道”的精神旨归可以追溯到何处,“道”为何会成为君子人格塑造的基本要求?在这个问题上,陈来指出:“儒家思想是接续着三代文化的传统及其所养育的精神气质的,儒家思想的一些要素在三代的发展中已经逐渐形成,并在西周成型地发展为整个文化的有规范意义的取向。”据此,他强调,对儒家思想之源流的考辨“要从三代文化(这里的文化指观念、信仰、伦理、意识形态、精神气质)的发展过程来寻绎。忽略了这样的立场和眼光,就可能止于局部而不自觉”。这一观点极具有启示性。
从上古到西周,古代儒家关于礼乐天道文化的真正形成,以及这种从非自觉到内在自觉的演变,实质上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通过神话传说、文字记载、考古资料等多维证据进行论证,发现在儒家思想体系中,仍保留了“巫”时代所特有的人神沟通以致“天人合一”的神圣观念。如此,对“安贫乐道”思想的来源就可以追溯到中国早期礼乐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初期。从上古时期的巫觋文化和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祭祀文化,到西周时期的礼乐文化,皆是早期儒家思想的重要来源,它们直接影响了儒家文化心理的形成。因此,对“安贫乐道”思想来源的追溯,也需要回到儒的社会职能上来。对“儒”的理解,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讨论的核心,但始终没有定论。许慎在《说文》中指出:“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许慎之所以运用“术士”和“柔”的说法来阐释儒家的源流,说明在儒家思想中,“柔”的理念与祭祀仪式有着密切的关联。20世纪以来,古文字学的兴盛推进了人文学科的发展,产生了许多“说儒”的论著。
20世纪30年代,胡适将“柔”诠释为儒家的一种主要精神特征,他从比较宗教学的角度,援引古希腊知识分子的演变规律,来论证“儒”是殷民族的亡国术士,因迫于生存需要而建立了“柔逊的人生观”。针对胡适的说法,郭沫若在文献史料的基础上,用甲骨文作为论证材料,认为 “儒”之本义的“柔”,不是指习于服从的柔,而是文绉绉、酸溜溜的柔。1954年,钱穆在《驳胡适之说儒》一文中强调,胡适所谓“亡国遗风之柔逊则不可”,“考之古说,殷尚鬼,周尚文”,殷之遗民“长艺术”与“重现实”,自有古之遗风,“儒道尚柔,亦未必与亡国遗民相涉”。到了20世纪70年代,徐中舒则认为,儒者事神前,必斋戒沐浴,“致其诚敬”,这种因“诚于中”而“形于外”的诚敬方式,赋予儒者一种柔逊的气质,也构成儒家的一种精神旨归。同一时期,日本学者白川静将中国古老文明与巫祝文化联系起来,认为儒的宗教背景可以溯源到巫祝为牺牲而求雨的仪式活动,从商汤到周的历史过程,同时也是由巫到儒的演进过程,此一观点十分中肯。
近几十年来,相关学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继续推进。杨向奎认为,所谓的“柔”是指“他们宽衣博带,他们的解果其冠,给人们的印象是迟滞缓慢,而且相礼职业的本身要求也是如此,如果从字义本身说儒,应从此下手”。叶舒宪则根据《诗经》中“温柔敦厚”的诗教理论,反推“儒”与尹寺之间的同源关系,提出从人格特征和生理特征的方面,去仔细探求“柔”的本义。总体而言,上述援引的诸多论点,主要还是因循经典国学的考辨之法。陈来在反思这种方法的局限性时指出:“用字源学的方法讨论上周甲金文是否有‘儒’字及其在古文字早期的意义,无疑是有学术价值的。但是,这种对‘儒’字的考释在理解儒家思想的根源方面却有很大局限性。”然而,值得肯定的是,比如白川静从神话学的视角,叶舒宪从人类学和人格特征的视角,来阐释“儒”与“柔”之间的关系,实际上都为释“儒”提供了字源学和考据学在文本之外的补充性和有说服力的论证路径。
在上述各家观点的启发之下,本文认为,对“儒”的理解,应该在语义学、史料的研究基础之上,在动态的文化传承关系中,返回到思想生成的历史脉络中,尤其是中国上古时期特殊的民间宗教信仰与神话体系之中去重新寻求答案。
二、神话-仪式视阈中的“儒”与“柔”
在上古神话中,有一类独特的古宗教仪式:火焚帝王。如在《淮南子》中,记载了一则关于帝王祈雨的传说:
汤时大旱七年,卜用人祀天。汤曰:“我本卜祭为民,岂乎自当之。”乃使人积薪,剪发及爪,自洁,居柴上,将自焚以祭天。火将燃,即降大雨。

商汤祈雨
在这则神话中,最高统治者作为牺牲主体,亲自主持祭天祈雨的仪式,可见,祈雨一事在上古时期是极为重要的仪式活动。类似帝王直接参与祭祀的神话,也出现在文献史料中,如《史记·殷本纪》云:“周武王于是遂率诸侯伐纣。纣亦发兵距之牧野。甲子日,纣兵败。纣走,入登鹿台,衣其宝玉衣,赴火而死。”《说文》载,“灵”被释读为“巫以玉事神”,“玉”在上古时期是巫师的通灵法器,通神的重要物质媒介。因此,在纣王“赴火而死”时,用“衣其宝玉衣”的行为,暗示他在完成某种“事神”的仪式。对比两则材料可知,火焚的祭祀仪式在殷商时期是一种重要的宗教现象,且都由君主来充当祭祀活动中的人牲。然而,为何君主会亲自参与火焚仪式呢?
自新世纪以来,由于甲骨文的不断出土和随之带来的新发现,为早期中国文明的研究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史证材料。火焚的祭祀仪式也被认为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甲骨卜辞时代。我们发现,一种可以称为“烄”的火焚仪式,可能是探寻帝王参与牺牲祭祀活动缘由的突破口。“烄”在甲骨文中写为“

”,上下结构,上部似为双腿交叉的舞者,下部则是燃烧的火丛。根据卜辞的内容可推知,烄祭的目的在于祈雨。如“勿烄[女才],亡其雨。”“贞[女才]亡其从雨”等。根据考证,这些卜辞共有128种,都明确地将“烄”和祈雨活动联系起来。作为烄祭牺牲者的“女才”,虽然在仪式过程(火焚)和仪式目的(祈雨)两个方面,与《淮南子》中对商汤作为帝王祈雨所描述的情节基本一致,但是,它们之间却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差异。为了搞清楚这种差异背后的缘由,我们援引另一则火焚的神话:
南方赤帝女学道得仙,居南阳愕山桑树上。正月一日衔柴作巢,至十五日成,或作白鹊,或女人。赤帝见之悲恸,诱之不得,以火焚之,女即升天。因名帝女桑。
在这段引文中,“帝女桑”与烄祭中的“女才”性别一致,仪式的场景基本类似。如果“帝女桑”被焚的目的也是祈雨,我们就能根据以上三个方面推测,这则神话实际上曲折地反映了火焚祈雨仪式的过程。而在神话叙事中,“衔柴作巢”“或作白鹊”的细节描述,恰好证明了这个推断。在殷商时期,“鸟”或“白鹊”的意象,正是预示和启示雨水将要降临的象征。所以,在卜辞中出现了大量有关祭鸟的陈述,比如:“贞:方帝。七月。”“贞:帝鸟一羊、一豕、一犬。”“贞:帝鸟 三羊、三豕、三犬。”“丁 巳 卜,贞:帝 鸟。” “丁 巳 (卜),贞:… 福 … 鸟。”
章太炎在《国故论衡》中提到:“鸟知天将雨者曰鹬(《说文》),舞旱暵者以为衣冠。”章氏的论点和祭鸟卜辞的内容,合起来正好可以说明,“鸟”和“雨”二者间有某种隐秘的关联。进而,在烄祭卜辞中所能显示的祭祀主体的性别特点(女)、仪式经历(火焚)和仪式目的(祈雨),都与上古神话中“帝女桑”的形象相吻合。所以,我们可做出如下推断:“帝女桑” 的原型,很可能对应于卜辞中记载的“女才”形象。由于“帝女桑”具有极高的社会地位,她是炎帝之女,因此“女才”等被烄者很可能是“炎帝”“商汤”这类帝王的直系亲属。那么,在这类祈雨仪式中,火焚帝王与火焚帝女之间,又存在何种关联呢?
从比较神话学的视角来看,首先,在祭祀的仪式活动中,帝王与帝女拥有相同的“神性”,后者被认为可以在仪式中代替前者。人类学的材料表明,在世界性范围内都出现过类似的传统。在《金枝》中,弗雷泽记载了多例相似的祭祀活动,基本的模式是:当一个国家处在危亡的时刻,最高统治者会把自己的孩子献祭给魔鬼或神灵,以此祭祀活动来为百姓赎罪谋福。其中一个案例是:当国王穆阿布被以色列人包围,攻打紧迫时,他只好献出本应继承王位的长子,把他“在城墙上火祭了”。国王的长子遭遇了与“帝女桑”“女才”类似的“火祭”。为何在祭祀中要选择处死与国王本人具有直接血亲关系的家庭成员呢? 弗雷泽提出如下推论:“国王在得到别人的生命代替他的生命而成为牺牲的时候,他一定要表明别人的死完全和他本人的死能够同样地达到目的。既然国王是作为神或半神而死去的,那么,代他而死的替身至少当时要赋有国王的神性。”这段话正好说明,在这种仪式活动中,国王的牺牲被赋予了等同于“神”或“半神”的神圣性地位,能够替代国王而成为祭祀牺牲的角色,需要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和国王相匹配/对称的“神性”。同理,诸如“帝女桑”“女才”等王室成员皆因具有“炎帝”“商汤”等帝王的血脉,实际上被视为是帝王之神性的最佳“分有”者,因此最适合扮演牺牲替代者的角色,从而取代帝王来完成献祭仪式。
其次,在祈雨仪式中,“女”与“雨”之间,遵循阴性同构的巫术法则。在《金枝》的案例中,“大难临头”之际,君主以“火焚”儿子的方式来实现拯救民众的目的。然而,在中国神话和文献记载中,替代者是帝王的女儿。这种牺牲替代者在性别方面的差异,究竟包含着怎样的宗教义理呢? 我们依然可以从甲骨文中找到相关的线索:
贞:舞,有雨?
庚寅卜,甲午奏舞,雨?
辛巳卜,宾贞:乎舞,有从雨?
在这些卜辞中,通过舞蹈(“舞”)仪式来祈求降雨的活动,多数为女性。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说:“凡求雨之大体,丈夫欲藏匿,女子欲和而乐。”在祈雨仪式中,为何男性和女性的表现会有如此大的差异? 《春秋繁露》进一步指出:“天地之阴阳当男女,人之男女当阴阳。”在天-地、男-女、阴-阳等二分的认知基础上,根据神话学和人类学的巫术法则,“‘女’的阴性特点和‘天地’之‘雨’的阴性特点可以达成同构的巫术机理,才会出现以女求雨的祭祀标准”。所以,帝女由于“分有”帝王的神性而成为火焚祭祀仪式的牺牲者,而她的性别特征,则是其充当祈雨人牲的关键所在。有学者概括这是史前三代时期一个重要的宗教现象,即女巫的专门化。
造成这一现象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祈雨。《说文》中对“巫”的另一个解释是“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由此可以看到,“降神”这一神圣的仪式化行为,已经产生了某种职业化的倾向,而女 性因为与阴性同构,成为重要的参与者。在同一时期,有文字记载的关于帝王本人祈雨的故事,逐渐不再常见。这说明,在此类仪式活动中,帝王作为牺牲者的模式,开始逐渐隐退。因此,将女、舞、降神、祈雨,这几个关键词串联起来,构成我们理解女性参与祈雨仪式和从帝王火焚祈雨到帝女火焚祈雨转变的宗教性缘由。
然而,到了商周交替之际,天命鼎革,周人为稳固王权,进行了一次重大的宗教改革。在这次改革中,包括帝女祈雨仪式在内的诸多商代宗教仪式,也随之失传。此即“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胡适对此加以阐述,“殷周两民族的逐渐同化,其中自然有自觉的方式,也有不自觉的方式。不自觉的同化是两种民族文化长期接触的自然结果”,而“自觉的同化”则“与‘儒’的一个阶级或职业有很重大的关系”。与此观点类似,牟复礼在讨论先秦儒的传统和起源时指出,到了商晚期,儒者主要是扮演“神灵世界的和个人仪式行为的顾问”,他们在仪式活动中效法神灵,为世俗社会谋求生存的权益,而这种行为又承继于更原始的民间信仰。到了周代,王权合法性更加仰仗复杂的礼仪制度来维系,“衍生于早期商代神灵世界的事迹,构造成了虚拟的历史”,被周王朝的君主改造利用。也即是说,在周承袭殷礼的过程中,为达到政治、文化上的合法化,对殷礼进行了吸收、转译与改造,而“儒”者在周代建构的礼仪文化方面,承担了关键性的社会角色。
综上,可以梳理出一条相对明晰的线索:帝王祈雨逐步转化为帝女祈雨,而帝女祈雨的仪式职能,后来在殷周同化的过程中,又逐渐被儒者所承袭。以女祈雨的原因,主要在于女性的阴柔特点,能够与雨水达成象征性的同构。换言之,帝女祈雨的本质,是以“柔”之道祈雨。儒家由于承袭了帝女祈雨的宗教文化职能,在这个过程中,“柔”的特征,逐渐构成儒者思想气质认同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并非儒家这群“术士”本身具有“柔”的性格或体貌,“柔”的实质,乃是巫(女)在祭祀祈雨仪式活动中所呈现出来的阴性特征。由于“儒”成为“帝女”牺牲的替代者,因而“柔”的特征也融入了早期儒者的社会文化的性格构成。由此,“儒,柔也”的表述,在祈雨的神话仪式中找到了关联性的答案。
三、“安贫乐道”与祈雨仪式的孑遗
在上古神话中,诸如火焚帝王/帝女的烄祭仪式,内蕴着大量的原始宗教信息,它们是人类最为丰富的对自我的认知与对世界的想象。英国学者赫利生(Jane Ellen Harrison)强调:“尽管巫术也许是一种包含大量谬误的学问,但它被认为主要起源于一种再生仪式,这种仪式强调唤起人类的一种集体愿望,即渴望与外界的力量合而为一,或者支配这些力量。”在上述关于帝王和帝女的祈雨仪式活动中,他们通过特定的方式和特定的媒介物,与神明沟通,并借助其神圣的力量,达到为集体谋生的最终目的。然而,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诸如此类的神话样貌发生了重大改变,它们被记录在后世小传统的文字材料里,并被高度理性化。如在“火焚”仪式的活动中,能否经受住用火来焚烧的痛苦演变为一种“考验”,它成为儒家思想体系里能否成为“君子”的前提条件,而巫者为谋求集体利益和追求天道的献身精神,则成为儒家对人格理想的至高追求。由此,我们可以推知,儒家“安贫乐道”的人格美理想,与“乐道”的神圣审美体验,依然保留着上古神话祭祀活动中所特有的神圣特质,即与天地沟通、与神灵交往,从而主宰万物。
上文提到,在周代初期,诸如祈雨仪式这类关乎人民基本生活的宗教活动,均由儒者承担。随着历史的发展,上古神话记载中的帝女、女巫的神性和宗教职能,也同时转嫁到新的社会阶层,即儒者身上,而这样的演变对早期儒家的思想和审美心理产生了何种具体的影响呢? 神话学和人类学的研究表明,在上古时期,人们通过“巫术-仪式”的方式,来彰显他们信奉的神圣力量。从功能主义的视角看,神话仪式的基本特征表现为,巫师通过“有形”的实体(身体),借助特定的渠道(物质媒介),达成和“无形”的神明进行沟通,进而获取有助于人类自身发展的超能力。仪式作为一个动态的概念,其基本内涵直接呈现在仪式化的实践过程之中。因而,我们在探讨仪式与人类道德伦理规范关系时,也必须返回到具体的仪式实践中。
在祈雨仪式里,我们尝试从“体与礼”的视角,重新思考烄祭的深层含义,它涉及三个关键质素——身体、火焚、祈雨,“火焚”的仪式象征活动,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一是仪式功能,在出现干旱这类自然灾害时,人与自然之间处于对立的状态。在祈雨仪式活动中,帝王或帝女通过“火焚”使身体受难,以超越日常生活的经验,进入某种神圣的状态,达到与“天”的沟通,实现与“不可见”的神明进行交流,以此来改变事物的发展轨迹,最终达到降雨的目的。这种介于对抗与和谐之间的“天人合一”的状态,是上古先民自我生存的基本追求,也是此类仪式活动发生的原初动力;二是仪式心理,通过火焚的仪式行为,牺牲者可以达到“人-神”对话的境界,而这样的 精神状态,是上古巫者在人与神的“对抗-和谐”的交流交融时产生的特殊情感和欲望表达。涂尔干将这种巫术-仪式状态描述为:“也就是这个时期,人们感觉到有某种外在于他们的东西在此获得了新生,有某种力量又被赋予了生机,有某种生命又被重新唤醒了。这种振奋不是想象,所有的个体都从中获益。”涂尔干在此强调,仪式活动强化个体对生命的感知能力,达到超然物外的精神境界,并在此过程中,借助神的力量来提升集体的凝聚力;三是仪式手段,在上古时期,巫者诉诸火焚的仪式行为,类似于人类学视野中的肢解、性交、净身、纹身、裸身等象征性的行为,它们均可被理解为一种“考验”的仪式。也就是说,只有通过使人的身体遭受某种磨难的方式牺牲者才能跨越庸常的经验,有资格与神进行沟通,进而获得神明的认可或允诺,以此来实现集体的或个人的特定诉求。虽然这些磨难的形式各有不同,但它们最终都会转化为祛灾、祈福和治疗的手段。
在甲骨文中,“烄”字的下半双腿部分显示的是一位交叉站在烈火之上(“火”)的舞女形象,这种扭曲的动作并不是一个舒适的姿势,甚至可以说会带来一定的身体痛苦。那为什么烄祭的对象会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呢? 我们可以从甲骨文的字形结构来推测,在这个字里,商人非常生动且形象地描绘出了巫者(舞者)在仪式活动中“痛”与“乐”并存的精神状态,双腿交叉的体态,既显示出牺牲者狰狞扭曲的肢 体动作的“痛”,也反映出在烈火之上,舞者通过仪式舞蹈(双腿交叉)所恪守的神圣心灵原则的“乐”。而这种“痛”与“乐”的对立交融,正好和上文描述的祭祀者在人-神沟通时,与天“对立-和谐”的模式相互印证,两者都是上古时期巫者在仪式过程中产生的独特心理。
如果进一步对比类似的神话和文字材料,可以发现在祈雨的仪式活动中,作为仪式牺牲者的帝王及牺牲者的替代者,往往具有一个共性的特征:他们都是通过外在可见的“体”的受难和痛苦,以达到内在不可见的“精神”的神圣与愉悦。也就是说,外在物质环境的恶劣和内在心灵世界的神圣之间具有逻辑上的关联。因此,内外二者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和对立。这种反差和对立,又逐步积淀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心理取向——以外在物质环境的恶劣和肉体的痛苦来表达和反衬内心的神圣。
这种以身体的痛苦来成就道义的神圣体验,最终演化为一种独特的宗教心理和人格典范,这一套巫史传统的模式,李泽厚将其解释为“演德”,即“原具有神秘力量测吉凶卜祸福的巫术占卜,日渐演变为对卜者(‘君子’亦‘圣王’)虽仍具有神秘力量却又已经是非常理性化了的道德品格的要求”。据此,李泽厚给出了中国巫史传统里这条一脉相承的线索,并诠释了从上古的巫术占卜发展到儒家礼制的逻辑关系。然而,在后世小传统的经典文本里,关于儒家的礼乐制度和道德规范的始源性信息,早已遗失。
上古的祈雨祭祀活动,原本是巫者为谋求公共利益而牺牲自我的仪式行为。在先秦时期,这一神圣的宗教孑遗呈现出新的面貌,孔子将此宗教性的仪式心理推而广之,并在儒家的经典文本中留下了相关的记载。如《周礼·天官》载:儒以道得名。《周礼·地官》:联师儒。由此可知,儒家思想的来源与上古时期的巫祝传统息息相关。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文明祛魅的理性化发展,绝大多数的宗教话语和礼仪实践相继隐退,其中包蕴的有关神话的内在机理也逐渐转化为某种规则和道德人格的典范。
孔子再三强调“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安贫乐道”的儒家教义意在协调一种普遍意义上的“德”与位的关系,若德不配位,则无法达成“乐道”。“安贫”不是一种外在的强制性规定,而是一种内在自觉的心性追求,这是儒家思想体系中“君子”的典范,也是孔子以实际行动诠释和想要达成的最高人格理想。“乐道”不仅是儒家在心志上的追求,也是一种内在的审美体验。孔子把原本属于宗教仪式活动的质素和要求归结为不屈服于外在环境的个体自觉。意在强调,我们虽无超凡的神力,但却同样可以通过自我牺牲的献身精神,达到对“天道”的体悟。也就是说,凡是能够经受住外在贫乏物质条件的考验,并一以贯之地把求“道”作为终极追求的人,才能称为儒家的“君子”。此时,“安贫乐道”的审美追求,也就转译为儒家君子之德的伦理追求,即不以外在的物质为价值尺度,而是致力于从道德上唤起人们在精神和人格上的完满。这些由帝王祈雨仪式活动而生发出来的对“天人合一”的道学追求,透露出上古神话与后世儒家思想观念之间的关联。
孔子认为,对“天道”的追求是个体成员也可以承担的任务,这就极大地突出了儒家对人本理性和个体人格的重视。这种经由个体人格的完成以通达天道的传统,也正好成为儒家“道在伦常日用之中”的典型注脚。圣人以身作则地践行了对这种伟大人格的自觉追求。

《孔子圣迹图》
结 语
通过对“儒,柔也”的重新释读,推知儒家“安贫乐道”的思想与上古时期火焚帝王神话之间的关系。儒家不仅掌握了从帝王到帝女以来主持仪式的特定技能,同时也承续着他们的仪式心理,即以外在物质环境的恶劣与肉体的痛苦(火焚)来反衬内心的神圣。这种神圣的仪式心理,在后世逐步积淀为儒家“安贫乐道”的人生信仰和心灵境界。儒家对史前的宗教仪式和信仰观念进行了有机整合,使其朝着更理性化的方向发展,“安贫乐道”也被记载于小传统的文字材料里,其原始宗教的内在精神被遮蔽。借助神话-仪式的研究方法,可以突破局限在古典文学文本内部的思维束缚,运用跨文化的综合性研究,在中国文化传统之整体性的原生“语境”中,重现阐释儒家“安贫乐道”思想与神话-仪式之间的文化传承关系。
原刊于《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注释请见原文

【作者简介】
张盼盼,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文化人类学、民俗与艺术考古。在《民族艺术》、《河南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论文数篇。
主编:朱生坚
编辑:张晴柔
运维:任洁
制作:小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