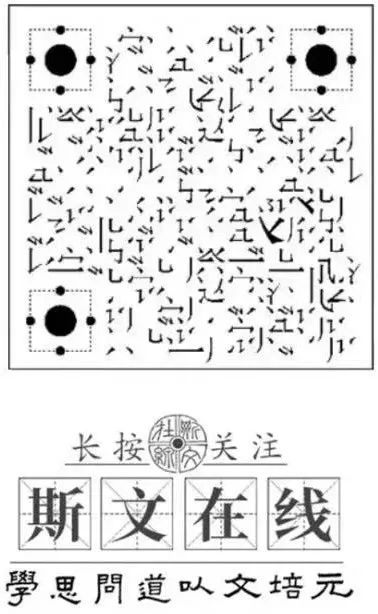绪言:为“德国式的歧形思想”辩护
1935年,宗白华在介绍席勒的人文主义和美育论时,曾引述英国作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Carlyle)的话,称赞“德国民族是‘诗人与思想家的民族’”。不过,他对卡莱尔的这个看法的赞同并非人云亦云,而是有着自己对德国民族思想和文化的深入的理解在内。因为早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宗白华就因对叔本华、康德等人的哲学的介绍而知名,并被人视为深受德国思想影响的青年学人,为此他还与当时如日中天的新文化的倡导者陈独秀产生了思想的冲突。1920年初,宗白华致信《少年中国》编辑部,建议《少年中国》以“打破中国人的文学脑筋,改造个科学脑筋”为办刊的目的。而陈独秀认为宗白华相当于点名批评的“文学脑筋”的“著名的新杂志”就是自己主编的《新青年》,立撰《告上海新文化运动的诸同志》予以强烈回击,并怒斥宗之所以有这样的看法就是因其所受到的“德国式的歧形思想”的影响。
像那德国式的歧形思想,一部分人极端的盲目崇拜自然科学万能,造成一种唯物派底机械的人生观;一部分人极端的盲目崇拜非科学的超实际的形而上的哲学,造成一种离开人生实用的幻想;这都是思想界过去的流弊,我们应该加以补救才是;若是把这两种歧形思想合在一处,便可算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底新注脚了。

宗白华著:《宗白华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
但宗白华出于对德国思想的了解却对陈独秀的批评“有恃无恐”,虽觉自己被陈“痛骂了一顿”,他依然不卑不亢,立即以《答陈独秀先生》一文回应,对其所指责的“德国式的歧形思想”进行辩护和“正形”,并且毫不客气地指出,“陈先生对于德国现代哲学,丝毫没有研究”,甚至,“陈先生对于德国现代哲学,简直没有研究”。而对宗的不留情面的讥诮,陈独秀只能作罢,因为对德国现代哲学,他确实没有研究,或者说确实没有宗的研究深广。但这次学术的激烈交锋,并未影响两人的友谊,宗不仅在后来陈独秀被羁押于南京狱中时与中大同事兼好友胡小石同往探视,在其于抗战时期寓居江津时,还在主编的《学灯》上发表其《〈小学识字教本〉自序》。
因此,作为对德国思想有着深入研究的留德学人,宗白华对德国思想的看法也具相当的代表性,从中不仅可以看出德国思想对其美学思想的影响,也可以看出那个时代中国的学人对德国思想的认识。本文从他对德国思想的认识和接受入手,以探讨他对德国思想特点的看法,然后再考察他对德国思想的缺陷的认识,从而还原他的德国思想观的生成与生发的过程,同时探讨他的德国思想观对其研究和批评中国艺术与美学及文化的影响。

宗白华(1897-1986)
一、德国思想的认识:“灰色”的“理论”与“常青”的“人生的金树”
宗白华对德国思想的认识最初来自1914年起在国内所受到的系统的德式教育,尤其是就读同济期间所接受的训练,在这个过程中,他逐渐对德国思想产生了兴趣,并决定弃医从文,从事哲学与文学的研究。其次,来自他于1920夏到1925年夏留德期间的学习,在此期间,他不仅更为深入地学习德国思想,而且还真切地接触并沉浸于德国的生活中,这使得他对德国思想的了解逐渐加深,并因此确定了日后努力的学术方向,从哲学研究转为文化批评与美学和艺术的研究。
1914年春,17岁的宗白华自南京赴青岛德华大学(Deutsch-Chinesische Hochschule)中文科读书。德华是1909年中德两国联合设立的大学,奉行德式教育,他主要在此学习德文。当年秋天,宗白华转入1907年建立的上海同济德文医工学堂德文科继续学习。而其时,他的伯父宗嘉谟在校教授国文,可能是他转学同济的助力。自此他开始就学同济德文科,1916年夏又升入医预科,至1918年毕业。在同济这所师资主要由德国学者构成,并且主要使用德语为教学语言的学校,宗白华受到了严格的德式教育的训练。而他在德文科及医预科的学习,不仅使他对德国的思想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还让他对科学有了很深的认识。这也是他始终对“科学精神”或“科学脑筋”念念不忘的原因。
他自言对哲学的兴趣就是在同济听到同宿舍朋友念诵《楞严经》开始的,而这其中,他感兴趣的主要是德国的哲学家和文学家,“庄子、康德、叔本华、歌德相继地在我的心灵的天空出现,每一个都在我的精神人格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痕”,所以,“拿叔本华的眼睛看世界,拿歌德的精神做人,是我那时的口号。”不过,也因此,宗白华对医学不再感兴趣,并决定弃医从文。“在五四运动的前夕,我在上海同济大学学习德文后,因法租界封闭了同济,同济迁吴淞,我无意学医,自己在家阅读德国古典文学,歌德、席勒、赫尔德林等诗人的名著,同时也读了一些哲学书,如康德、叔本华、尼采的著作。”
1920年5月底,23岁的宗白华赴德国留学。他先入法兰克福大学学习哲学心理学等,1921年春,又转至柏林大学,继续学习哲学、心理学、美学等。他在此期间,不仅对德国哲学及美学等学科有了系统的了解,还真切地感受和体验了德国的生活,使得他对德国思想与现实的关系有了深入的理解。他喜欢的歌德曾在《浮士德》中借靡菲斯特之口谈及理论与生活的关系,即“灰色是一切的理论,只有人生的金树常青”。而他在德国既深入地学习“理论”又热情地投入生活,尽力把“灰色”的“理论”和“常青”的“人生的金树”联系到一起。正是在法兰克福的学习,让他确定了后来的学术目标,从哲学转到了文化批评以及美学与艺术学的研究。他在入学两个月后,于《自德寄见书》中致信国内友人称其“在此进学已两月,听讲读书,非常快乐”。但他更“快乐”的是找到了自己的研究方向:“因为研究的兴趣方面太多,所以现在以‘文化’(包括学术伦理宗教)为研究的总对象,将来的结果,想做一个小小的‘文化批评家’,这也是现在德国哲学中一个很盛的趋向。所谓‘文化哲学’颇为发达。”其目的,就是想“借外人的镜子照自己面孔”,“以寻出新文化建设的真道路来”。当然,他眼中的“镜子”就是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德国人的思想。同时宗白华也深深融入了德国的生活,他在致国内朋友柯一岑(即郭一岑)的信中说:“我这两年在德的生活,差不多是实际生活与学术并重,或者可以说是把二者熔于一炉了的。我听音乐,看歌剧,游图画院,浏览山水的时间,占了三分之一。”这使得他对德国思想产生的背景与土壤也有了真切踏实的感受,因而对其理解也更深。正如他本人在《我和诗》中谈到这一时期的生活所言:“民国九年(1920年)五月我到德国去求学,广大世界底接触和多方面人生的体验使我的精神非常兴奋,从静默的沉思转到生活的飞跃。”反过来,“生活的飞跃”也让他开阔了眼界,从而也更好地与“静默的沉思”互为表里,让他把之前对德国思想的纸上的遐思变成生动的存在。

1920年代的柏林
二、德国民族的复兴:“乐观的”文学与“民族自信力”
宗白华在德国留学之际,正是德国一战战败谋求重新崛起之时,这也使得他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和观察德国人的生活与工作,并且对德国民族的国民性有了具体的认识,而他也因此发现在其复兴的过程中,文学艺术的弘扬对其民族“自信力”的激发所起到的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因为真切地置身于德国的诗与思相互激励的生活中间,也使得他诗兴大发,创作了将近五十首“流云”小诗,成为了一个新诗诗人。所以,他在德国生活期间,虽然对“德国民族的粗鲁”和“社会的冷酷”、“党派的争执”很不喜欢,但是,他对其国民性却非常欣赏:“他们那种冷静的意志,积极的工作,创造的魄力,确使我惊叹羡慕;也因为我们中国民族正缺乏这种优性,正需要这种东西。”而他对德国民族的工作的勤奋、努力与坚忍不拔的精神的发现,正与他欣赏的费希特对德国民族的国民性的概括相似:“前一种民族(德意志人)做一切事情,都很诚实,勤奋与认真,而且不辞辛苦。”
而宗白华认为,德国民族的这种国民性的养成,除了哲学的影响之外,更与诗相关,也即与文学艺术的影响有关。当然,宗白华的这个看法并不新鲜,除了卡莱尔所说的德国民族是诗人和思想家的民族,斯太尔夫人(Madame de Staël)也很早就谈过德国民族的这个特点:“德国人既具备了想象力,又能凝神静观——这是难能可贵的——所以他们比大多数其他民族更善于做抒情诗。”这里的“想象力”就是诗的能力,“凝神静观”则是哲学的思考能力,而德国人正是因拥有这种“难能可贵”的以形象表现思想的能力,使其变成一个诗的民族。宗白华到德国学习后,更是深刻意识到了德国民族的这个特点,他从德国民族对诗的热爱中,看出诗或文学对德国民族的振兴所起到的积极的作用,也即诗或文学可以改变人的人生观,从而激励和改变民族的精神。所以,他指出“文学底责任不只是做时代的表现者,尤重在做时代的‘指导者’”。他坦承自己的人生观也与文学的影响密不可分,称自己因读《浮士德》而“人生观一大变”,读莎士比亚则人生观变得“深刻”。也因此,他认为一个民族的精神状况与文学的状况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向来一个民族将兴时代和建设时代的文学,大半是乐观的,向前的”。因此,他称赞惠特曼的那些充满“伟大乐观”的豪情的诗歌,也是对美洲少年的勇猛奋进的精神的激励,而罗曼·罗兰的充满昂扬斗志的“乐观的文学”也对未来的法国和欧洲有着“好影响”,反之,法国颓废派的文学是不可能鼓励法国的“民气”的。
这当然也与宗白华对现实中德国民族的表现的认真观察有关。他发现,德国民族其时所处的处境虽然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困苦,最可悲了”,甚至比中国差十倍都不止,可是他“搜遍”德国出版的“文集诗歌”里,“不看见一首关于时代的悲调。他们国民人人自信德国必定复兴。这种盲目的乐观,就是德国复兴唯一的基础”。其实,这种“盲目的乐观”有着乐观的文学的激励。因此宗白华呼吁应以德国为镜鉴:“所以我极私心祈祷中国有许多乐观雄丽的诗歌出来,引我们泥涂中可怜的民族入于一种愉快舒畅的精神界。从这种愉快乐观的精神界里,才能养成向前的勇气和建设的能力呢!”而他对诗歌的这种看法,其实在出国前就已经形成,出国后看到的事实只是让他更加确信自己的判断而已。因此,他赞同歌德对诗歌的看法,“应该拿现实提举到和诗一般地高”,因为只有这样诗才能起到引导和鼓励人们的作用。宗白华通过与德国人的交往,也坚定了这个看法。1923年,他曾参加德国作家浩朴德曼(Gerhart Hauptmann)60岁生日的庆祝聚会,而老作家不仅精神健旺,还鼓励国人要相互“了解”和“亲爱”,“他相信德国必定复兴,只要国民不要失去了这个复兴的信仰”。正是有了这样的看法,宗白华一直主张用文学和艺术来鼓励人,以提高和坚强民族的自信力。1935年,他在《唐人诗歌中所表现的民族精神》一文的“文学与民族的关系”一节中,强调民族“自信力”的重要,而又特别举例德国以说明,对文学艺术予以格外的重视:“然而这种民族‘自信力’——民族精神——的表现与发扬,却端赖于文学的熏陶,我国古时即有闻歌咏以觇国风的故事。因为文学是民族的表征,是一切社会活动留在纸上的影子。”抗战爆发后,宗白华更是坚持自己的看法,他依然认为文学等对民族自信力的培养,对民族的复兴有着重要的作用,他不仅以德国一战后的复兴为例,而且也把130年前德国民族抵御外侮并统一强盛的境遇与抗战时的中国类比,强调其统一与复兴均有赖于文艺的助力,“而文化学术光芒百丈,也是民族复兴的原因”。
所以,宗白华认为,正是对文学的热爱,对思想的重视,才成就了德国民族的独特性,也使得他们在面对苦厄时,既有文学的鼓励,又有思想的指引,可以一次次从危难的境遇中复兴。

德国的“黄金二十年代”(Goldene Zwanziger Jahre)
Tea dance in the garden of the Esplanade hotel, Berlin, 1926
三、德国学者的治学:“哲学的精神”与“精细周密”
宗白华不仅赞赏德国民族的富有诗意,热爱文学,同时也对德国人的善于思想欣赏有加。而他之所以对席勒赞赏不已,就在于席勒在诗与思两个方面都才华横溢,“尤以席勒的好学深思,哲学论著精深严密,简直可以列入德国哲学家之林。他的人文主义是德国古典时代人文思想的精髓,他的美育论是美学上不朽的大作”。也因此,他对德国思想的产生的前提条件,也即德国学者的学术研究的态度推崇有加,这就是“哲学的精神”与“精细周密”。而这也影响到了他在从事中国美学及艺术研究时的态度,使得他的文化批评也具有了“哲学的精神”和“精细周密”的特点。
当然,对于德国是思想家的民族的说法,宗白华所征引的卡莱尔的话比较简略,卡莱尔对德国民族的这个特征还有较为详细的描述:“他们的民族性格中有一种严肃认真的东西,是一个善于思辨的民族......(他们的全部神话)都隶属于一个思想深邃的民族。”而在其之前,斯太尔夫人对德国民族的思辨能力也青睐有加:“没有任何别的民族比德国人更适合于从事哲学研究的了。”此外,宗白华所欣赏的德国诗人海涅不仅赞同斯太尔夫人的这个观点,更是以德国人的身份,对德国人的哲学热予以文学化的描述:“德国被康德引入了哲学的道路,因此哲学变成了一件民族的事业。一群出色的大思想家突然出现在德国的国土上,就像用魔法呼唤出来的一样。”宗白华对康德早已烂熟于心,自然对海涅所说的由康德所引起的德国人对哲学的热衷别有会心。但他更关心的是德国哲学滋生的土壤,这也是他赴德留学后非常关注的问题。
宗白华认为思想或者哲学的思辨之所以成为德国的民族特征,与德国学术气氛的浓烈紧密相关。他到德国后,发现德国的青年虽然“生活困苦”之至,可是他们之中到大学读书的人却比战前增加了一倍。正是这么多青年热衷追求学术的进步,才使得德国思想的发生与哲学的发展成为可能。不过,德国思想的繁荣,宗白华认为最为关键的还是德国学者治学时所秉持的“哲学精神”和“精细周密”的态度。他对此的看法主要表现在对李长之翻译德国学者玛尔霍兹(Werner Mahrholz)的《文艺史学与文艺科学》(Lierargeschichte und literaturwissenschaft)的“跋”中。他对这本书很赞赏,并且鼓励当时同在重庆中大任教的李长之完成了这部书的翻译,所以,他特地为这本书写了跋语,对德国学者的治学精神进行了概括:“德国学者治学的精神有它的特点:一方面他们都富于哲学的精神,治任何一门学问都钻研到最后的形而上学的问题,眼光阔大而深远,不怕堕于晦涩艰奥;另一方面却极端精细周密,不放松细微末节。”
在宗白华看来,所谓的“哲学的精神”,就是要将自己研究的问题逐步深化直至推到形而上学方面,因此,德国学者“不怕堕于晦涩艰奥”;而“极端惊喜周密”,就是对所探讨问题的研究充分全面,这就是一种科学精神。因此,宗白华对李长之在书中所作的对话体的序言为德国学者的“晦涩”进行“辩护”表示赞赏,并为之“感动”。李长之认为一般人只看到德国人的著作“沉闷而冗长”的“坏处”,但却没有看到其“好处”:“简单说至少是周密和精确,又非常深入,对一问题,往往直捣核心,有形而上学意味。幽默,轻松,明快,本不是德人所长,我们也不求之于德人著作呢。”因此,李长之更进一步指出,“周密和精确”实际上是一种“科学”研究的态度:“研究却不同,研究就要周密,精确和深入。中国人一向不知道研究文学也是一种‘学’,也是一种专门之学,也是一种科学。关于数学的论文,一般人看了不懂,不以为怪;为什么看了关于文学的论文,不懂,就奇怪呢?”
李长之对于“周密和精确”的解释和宗白华对于德国学者的研究问题的“精细周密”的意思是一样的,不过他说得更清楚,那就是凡是“科学”的研究必须要认真,周密,精确。正是对德国学者的治学精神有此认识,宗白华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也努力向德国学者学习,虽然他没有讲自己是否像尼采那样把生命燃烧在思想的探索中,但是他的研究却颇具德国学者的特色,那就是如其所言,他的研究大都富于“哲学的精神”,喜欢把问题深入到“最后的形而上学问题”,显现出“眼光的阔大深远”。他在探讨中国绘画所表现的“中国心灵”时,就直接将其从画家个人的艺术表现追溯到中国人的整体的“宇宙观”,可谓“深远”之至。而宗白华这样的由艺术现象深入到宇宙观或者“最后的形而上学问题”的研究方法,也是其学术研究的特色,从中既可以看到他所受到的德国治学精神的影响,也可以看到他对学术研究的“哲学精神”的追求,同时也体现出他的研究的“精细周密”的特点。
四、德国的精神文化:“可以说是音乐化了的”
宗白华留德期间除了对德国民族的诗性和对思想与学术的热衷之外,对于德国的精神文化的本质也有了更为具体和深刻的认识,那就是德国精神文化所具有的“音乐化”的特质。这个认识既来自他对于德国音乐的直接的接触和接受,也来自他之前对叔本华等人的音乐理论的理解,也因此他对德国文化精神的理解更为深透。而从音乐出发对中国的文化艺术进行批评,也成为他从事文化批评及美学与艺术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
不过,宗白华对音乐或者对德国文化的音乐性的认识还是至德国留学之后,出国前,他在文章里很少谈论音乐。当然,在理论上,他对德国人对音乐的喜爱并非一无所知,他喜欢的叔本华就非常推崇音乐,这对他应不无影响。叔本华认为,在艺术中,音乐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因为音乐既不像绘画一样依赖“现象世界”,也不依靠“理念”,而是对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本源的“意志”的“直接客体化和写照”,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即令这世界全不存在,音乐却还是存在”。叔本华对音乐的形而上的推崇对宗白华的音乐认识不无影响,但他对音乐的喜爱和真正的理解主要还来自于他留德后生活经验的直接的养成。在德国学习期间,宗白华狂热地喜欢上了德国的古典音乐,他不仅经常去听音乐会,还购买大量唱片在家里随时聆听。而他对此也不无感慨,在给朋友的信《致柯一岑书》中说:“我在德国两年来印象最深的,不是学术,不是政治,不是战后经济状况,而是德国的音乐。音乐直接表现了人生底内容,一切人生境界,命运界(即对世界的种种关系)各种繁复问题,都在音乐中得到了超然的解脱和具体的表现。”所以,他不仅从对音乐的理论认识中、更从自己的亲身体验中得出结论:“德国全部的精神文化差不多可以说是音乐化了的。”而宗白华说德国的精神文化是“音乐化”的,或者是“音乐式”的,是因为他发现德国的精神文化都富有音乐性或者表现出了音乐的特质,或者说音乐就是德国精神文化的灵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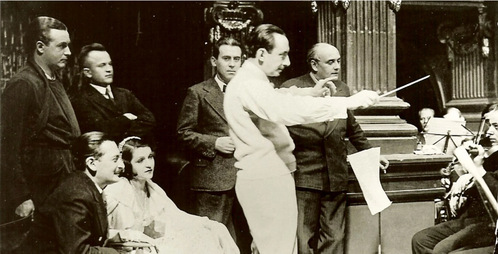
德国音乐家Werner R. Heymann在指挥乐队演出他的电影配乐,1931
正是因为宗白华在德国所受到的音乐的影响,使得他不仅把德国音乐视作世界艺术的高峰,还将其作为衡量伟大艺术的标准,在对中国的绘画进行批评时,为了凸显其价值,他除了将其与希腊的雕刻并列之外,还与德国的音乐相提并论:“中国的绘画,与希腊的雕刻和德国的音乐鼎足而三。”他也因此很赞成英国文艺批评家派脱(Pater)的音乐与艺术关系的观点,即“一切的艺术都趋向音乐的状态”。而从音乐性入手对中国的艺术的考察也成为宗白华的非常重要的艺术研究方法。除此之外,他还从音乐出发对国人的生活及文化精神进行批判,他认为中国的音乐自从唐以后就衰落了,而这使得中国的生活变得枯燥,人性变得粗粝。正是如此,使得宗白华非常重视音乐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在抗战期间他主持《时事新报》“学灯”时,就始终不忘向国人提倡音乐,“现代中国人需要悲壮热烈牺牲的生活,但也需要伟大深沉的生活,音乐对于人生的深沉化有关系,我预备发表几篇音乐家的故事”。不过,宗白华认为中国的音乐虽然缺失,还好“写字的艺术”即书法却起到了音乐的作用,多少调节了一下国人因缺乏真正的音乐而枯燥的生活。而他在向西人介绍自己的好友徐悲鸿的画作时谈到中国的书法,同样强调了其音乐性的特征或美感的音乐性:“故中国书法为中国特有之高级艺术:以抽象之笔墨表现极具体之人格风度及个性情感,而其美有如音乐。”
当然,宗白华不仅以音乐来批评中国的生活与艺术,还以其来考察中国文化的精神。他在《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往哪里去》中就借泰戈尔所赞赏的“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来强调中国文化中的音乐性:“中国人本能地找到了事物的旋律的秘密。”宗白华在此不仅把中国的艺术“音乐化”,也把中国的文化精神“音乐化”了。这其中虽然有中国艺术及文化精神固有的音乐性的一面,但更不能忽视的是宗白华因受到德国精神文化“音乐化”的影响,有意无意戴着德国音乐的“有声眼镜”来审视中国的艺术与文化,才有意无意地将中国的艺术与文化也“音乐化”了。
五、结语:“这就是德国人精神!”
宗白华因特殊的教育及生活经历,既对德国思想了解颇深,也深受其影响,因此他由衷赞赏这个“诗人与思想家的民族”的融合诗与思的才能与力量。他不仅对文艺在其民族的“自信力”的养成中起到的作用予以肯定,对德国学者在治学中体现出的哲学精神和精细周密的科学态度欣赏不已,同时,他也对德国精神文化的音乐化产生共鸣。而正因为他对德国思想的深刻的理解,他才得以将其思想转化为自己研究中国艺术与文化的方法,独出机杼,建立了自己独特的美学体系。而德国思想对宗白华来说,它永远是自己的思想深处和情感深处的不朽的诗篇:
对于近代各问题我都感到兴趣,我不那样悲观,我期待着一个更有力的更光明的人类到来。然而莱茵河上的故垒寒流,残灯古梦,仍然萦系在心坎深处,使我常时做做古典的浪漫的美梦。
也许,用李长之的话来说,“这就是德国人精神”!

【作者简介】
张生,作家,学者。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法国理论、中国现代美学,文化批评等。专著有《时代的万华镜》(同济大学出版社,2008),《通向巴塔耶》(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等。有短篇小说集《乘灰狗旅行》(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长篇《白云千里万里》(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年),《忽快忽慢的旅程》(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年)等。译有黄哲伦《蝴蝶君》(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布罗茨基《水印》(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等。
【新刊目录】
《上海文化》(文化研究版)
2024年第4期
专 题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上海实践
郑崇选 “第二个结合”与当代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巩固
黄力之 中国文化主体性与文化自信的历史逻辑
访 谈
李庆西 齐晓鸽 文学现场四十年——李庆西访谈录
理 论
章文颖 超越理性的“实存”——谢林美学中的存在主义萌芽
文 学
牛 菡 “自我”的言说与保存——90年代以来青年作家身份意识辨析
董外平 小资青年的前生今世:一份精神史的考察——论张柠的长篇小说“青春三部曲”
文 化
肖 剑 章心仪 算法时代的音乐品味:网易云平台的歌单策展研究
林 凌 曹浥霖 人人都能搞音乐吗?——透视新技术条件下“抖音神曲”的生产与流通
文 艺
朱恬骅 “另类”与“日常”:城市更新中的艺术空间
张苏卉 谭 然 微更新视域下社区公共艺术的生态性研究
张 磊 滨水工业遗存的艺术化更新策略——以上海“一江一河”为例
笔 记
张 生 “诗人与思想家的民族”——谈宗白华对德国思想的认识与接受
书 评
夏 天 西方学者对中国近代文物流失的历史还原与当代思考——评《掠夺的补偿:中国如何失去其宝藏》
编后记
英文目录
封二 周卫平《古镇夕阳》
封三 好书经眼录
《上海文化》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扩展版)来源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引文数据库来源刊
社长:徐锦江
常务副社长:孙甘露
主编:吴亮
执行主编:王光东
副主编:杨斌华、张定浩
编辑部主任:朱生坚
编辑:木叶、黄德海、 贾艳艳、王韧、金方廷、孙页
《上海文化》(文化研究版)
主办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地址:上海市中山西路1610号2号楼928室
邮编:200235
电话:021-64280382
电子邮箱:shwh@sass.org.cn
邮发代号:4-888
出版日期:双月20日
主编:朱生坚
编辑:张晴柔
运维:任洁
制作:小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