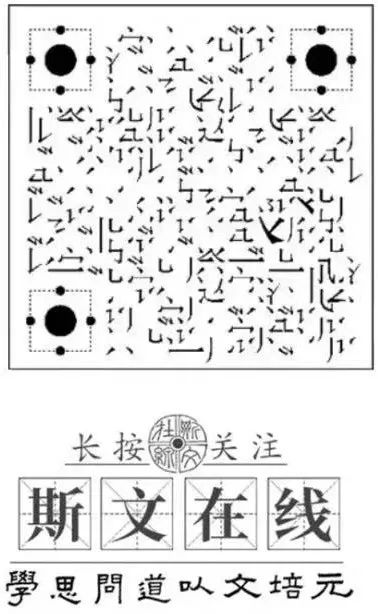与国内同辈大多数导演不同,万玛才旦的艺术世界由文字和影像两部分组成。他是作家,也是导演。文学方面,迄今出版了《乌金的牙齿》《城市生活》《诱惑》《撞死一只羊》《气球》《故事只讲了一半》等多部短篇小说集,合著长篇小说《大师在西藏》,以及《西藏:说不完的故事》《人生歌谣》等汉译藏民间故事集。曾获“林斤澜短篇小说奖”、“青海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等多个文学奖项;电影方面,自北京电影学院求学期间拍摄的习作《草原》始,万玛才旦导演了《静静的玛尼石》《寻找智美更登》《老狗》《五彩神箭》《塔洛》《撞死了一只羊》《气球》等七部剧情长片和两部短片,获得“中国电影金鸡奖”、“釜山国际电影节”、“上海国际电影节”、“美国布鲁克林国际电影节”等多项国内外电影奖项,被誉为中国电影“藏地新浪潮”的开拓者和领军人物。从具体作品出发,理解万玛才旦,既要有汉/藏文化的双重视角,也要有小说/电影的双重维度。这不仅意味着万玛才旦可以被单独理解为作家或导演,同时意味着他的小说与电影彼此交织,他对汉/藏文化的理解亦可作如是观。

万玛才旦(1969-2023)
一、汉藏文化交融:创作底色及主题
作为藏族艺术家,万玛才旦成长于青海安多,受过系统的汉文化教育,可以娴熟使用汉、藏两种语言进行文学创作。他的藏语短篇小说多发表于《章恰尔》《岗尖梅朵》《西藏文艺》《青海藏文报》等藏文报刊,已出版《诱惑》《城市生活》《岗》等藏文短篇小说集。虽然有藏族评论家认为这些藏语作品由其创作的汉语作品直接翻译而来,但两种语言的小说究竟哪种是翻译、哪种是原作,或者作者创作过程中是否使用两种语言间或写作,实在难以确定。
这里探究万玛才旦汉藏双语创作的缘由,在于他的汉语文学作品从题材、意象到结构、视角,甚至词语的选择都带有明显的藏文化印记,他所编剧、导演的藏语电影同样具有汉藏文化交融的复杂面貌。与以往表现西藏生活的文艺作品相比,万玛才旦既没有在“异域文化”框架中将藏区风俗“景观化”,也没有在“小资文化”语境中将之“符号化”——他的艺术眼光,是根植其中的“向内”审视,用质朴的情感和不加滤镜的“此岸”,描述深具人文内涵的“彼岸”。
由于地域、历史、政治等诸多因素,藏传佛教“在一定范围内同藏族传统文化水乳交融,在其中占有一定的核心地位,并构成了藏族人民生活和文化的精华……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人生态度等精神文化领域产生了极其深厚的影响”。万玛才旦成长于藏传佛教氛围浓厚的藏区,以藏传佛教为重要组成的西藏传统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万玛才旦的创作。对此他有着明确的认知,自言“宗教肯定对创作有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并非那么表面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在藏区普通民众日常生活中的相互交织渗透,构成了万玛才旦创作的主题,两者间的博弈正是他艺术世界的底色。

万玛才旦 《撞死了一只羊》
花城出版社,2018
藏区的传统文化首先深刻影响了万玛才旦艺术人物的世界观。就世界架构而言,藏传佛教认为世间万物都处于“成住坏空”的流变中,生灭迁流刹那不住,人的生命并不终结于肉体的死亡,灵魂受到业力牵引,会进入六道不断轮回,而轮回所经历的世事并不是世界的本质,如同虚幻的梦境,超世俗意义的真实是空性的。刘大先指认为万玛才旦的小说,“吸收了民间故事及其所蕴含的民间智慧与思维的营养。这些小说虽然并没有直接书写佛教和苯教式的思维观念,但是它们那种潜在的文化记忆和精神框架却隐约地弥漫在文本之中”。短篇小说《玛尼石,静静地敲》中,醉酒的人可以听到死去的老玛尼石匠仍在凿石,还能在梦中与他对话。《诱惑》中的嘉洋丹增,前世、今生、死后都对同一卷经文怀有执念。《气球》里的大儿子,被全家认为是死去奶奶的转世;尚未出生的最小孩子,也被活佛认定会是离世爷爷的转世。这里的轮回赋予了万玛才旦艺术人物超越此生的生命格局。当生命并不限于已知的长度,并且可以穿越不同的物质世界,人的主体意识也会随之改变,彼岸和来生构成了一种别样的异托邦。
与之相应,万玛才旦的创作还常常呈现出一种深刻的荒诞感。如《乌金的牙齿》中我的同学突然成为受人敬仰的活佛,而我的乳牙和他的乳牙混在一起被信徒朝拜,《流浪歌手的梦》里梦境与现实产生奇妙的呼应等等。就世界本质而言,万玛才旦认为与其说他作品中的“荒诞”是受到现代主义的影响,不如说其根基“更多来自现实的真实”——“世界对我们在场,它的面貌不可能完全清晰……人们对于一些未知的东西,或者信仰层面的东西,都是混沌的”。这里的“未知和混沌”并非反理性,而是前理性的,与宗教信仰混杂在一起;在人们对于生死、悲喜、现实和幻境(梦境、神迹)超越二元对立的认知中,世界的本质是超验的。例如,“影片《静静的嘛呢石》中的猴王面具与《寻找智美更登》中女歌手的面纱,为的并非是遮盖或显露藏文化那隐藏的真实文化身份,而是要显示在再现之中并无任何终极的 ‘真实’”。
此外,西藏民间文学也从人物塑造和叙述等多方面,影响了万玛才旦的创作。就人物选取而言,西藏民间文学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多取材自历史或宗教人物传说、神话故事、佛教经变故事等,万玛才旦小说和电影中的活佛、度母、喇嘛、格萨尔王等带鲜明西藏文化色彩的人物,其角色形象、精神主旨都可以在民间文学找到原型。如《陌生人》异乡人要找的第二十一位卓玛,就是观音菩萨的化身即藏传佛教中的度母,《大师在西藏》的主角就是藏传佛教大师莲花生。人物塑造之外,万玛才旦还借鉴了西藏民间文学常见的叙事结构和节奏,通过某些语词、段落的重复,增加语言回环往复的音韵美,进而以重复和重复中的差异突显主题,并且通过不断累积的叙述本身的力量,“动员读者深层意识中的原型叙述,把读者的注意力聚焦到人物的精神状态之上”。如《第九个男人》中卓玛讲述过往爱情经历时第九个男人的数次回应,又如《尸说新语·枪》的故事框架就来自他翻译的藏语民间故事集《西藏:说不完的故事》。
总体而言,万玛才旦的艺术创作巧妙攫取了身在其中的西藏文化精髓,同时又会拉开距离从外部对此做出反思。他深切感受到“虽然信仰的力量是强大的,但面对多元文化的夹击和挑战,信仰也很脆弱”。当藏区的传统文化日益改变,万玛才旦虽在《岗》《我是一只种羊》《静静的玛尼石》《寻找智美更登》《老狗》《五彩神箭》等作品中留恋过往,但并未将视角停留在“雪域圣地”的固态化的藏区。他认为自己“不是刻意要呈现传统文明与现代文化的冲突,而只是去呈现生活”,因此作品中的人物对于现代文明,是一种既震惊、排斥又新奇、欢迎的矛盾态度。对此,万玛才旦的处理饶有意味。其一,对现实做理想化加工。如《塔洛》照相馆里的牧民夫妇选择以北京、纽约市景作为合影拍摄背景,投射出其对现代化大都市的向往,又如《静静的嘛呢石》中小喇嘛、小活佛对“唐僧喇嘛故事”(1986电视连续剧版《西游记》)的热衷,都体现出人们 “对那些对你原有的文化可能带来冲击的东西,甚至是带着一种迎接的心情的”;其二,隐藏作者态度,采取“中性的,可能只有佛教才会用的解决方法”。如《老狗》最后老人自己杀死了被卖掉又追回的老狗,“对老人、对老狗都是一种解脱”。又如《寻找智美更登》中的老人把妻子送给瞎子单身汉,他像传统藏戏中的“智美更登”王子一样具有慈悲心,毫无保留地帮助他人,但也明白妻子是独立的个体,做决定前主动征求妻子意见。万玛才旦采取了一种受到藏区宗教文化影响的独特处理方式,以坦然、宽容和慈悲化解后现代语境中类似题材常见的文明末路和自我认知障碍。
怀着对复杂现状的敏锐感知,万玛才旦试图通过文艺创作与社会历史形成对话,进而引导读者和观众的深入思考。纵观万玛才旦的创作,其关注的主题或可归纳为三个方面:其一是“寻找”。如在《寻找智美更登》《寻访阿卡图巴》《陌生人》《流浪歌手的梦》《站着打瞌睡的女孩》等作品中,人物都被某种行为目的所驱使,而寻找的对象则带有某种精神寓意。例如,作品中所寻找的“智美更登”表面是扮演藏戏角色的演员,实际是日渐衰落的藏戏传统。《流浪歌手的梦》里歌手苦苦追寻的“梦中情人”,显然意味着未受任何世俗干扰的灵魂飞地;其二是“慈悲”。慈悲是对他人痛苦感同身受的同情,是愿意为了他人付出乃至牺牲自身利益的博爱,某种程度上,也是万玛才旦艺术世界的人物共性。如前所述,万玛才旦的创作受到藏传佛教影响,而慈悲则是他所认为的“藏传佛教基本精神”,慈悲也“被认为是西藏文化的最高价值观,部分学者更将之定位为西藏身份的重要特质”。在万玛才旦的作品中很难找到带有道德污点的坏人,人们也许迷茫(如《塔洛》中的塔洛、杨措),也许一时糊涂(如《草原》中偷了“放生牛”的村长儿子),但归根结底不会对他者报有恶意,即便如《老狗》中的老牧人最终亲手结束了老狗的生命,也是希望带给老狗远离世间痛苦的真正解脱。万玛才旦对他的人物是慈悲的,而作品中的人物对于天地万物也报有同样的尊重和慈悲;其三是“身份认同”。无论是“寻找”还是“慈悲”,都意味着在一个失衡的世界里,在新旧生活混杂、多元文化冲击中,重新锚定自己的文化身份。在这个意义上,万玛才旦“作品的最终目的,是破除西藏作为边缘及‘永恒不变’的神话,把西藏经验重新放置于中国及全球社会显现的框架中……邀请观众将社群视作一个未来的概念,观察他们的过度与转变的型态。”
二、从小说到电影:影像改编与创新
从文学到电影,万玛才旦的文艺作品表现出某些共同的特点,又呈现出一些饶有意味的差异。正如万玛才旦能够跨文化地融会汉藏两种语言进行文学创作,他的小说和电影同样在相互影响中滋生出一种别样的力量。就创作过程而言,万玛才担任导演的影片,多为他的小说改编或本人亲自编剧,他坦言自己“写剧本也跟写小说差不多,跟职业编剧写剧本的套路方法是不一样的……有的小说写的介于小说与剧本之间”。
万玛才旦的小说,通篇呈现出电影剧本般的极简叙述风格。随机摘录几段,如《我是一只种羊》的结尾,老村长说:“今天开始你被放生了,这个草原上谁也不会那你怎么样了。”我还是用不解的眼神看着他。老村长指了指远处白皑皑的雪山,说:“去吧”。又如,《流浪歌手》的开篇,为了寻找那梦,流浪歌手次仁行进在路上。次仁在他十四岁那年春天的晚上做了一个梦。出现在他梦中的是一个小女孩。那时候他已经是一名小歌手了。那时候他已经学会了读书写字。那时候他已能简单地记述一些事情了。
万玛才旦的小说中充斥着类似的叙述,寥寥数笔,交待清楚时间、地点和人物经历,叙述主要指向人物的行为与语言。对此,万玛才旦有着清醒的自知,克制、冷静白描似的叙述策略,是他深思熟虑后的选择,“我觉得心理描写不太必要……‘她想……’这种方法可能是太过于直接和粗暴,进入人物的心理,甚至干涉她的语言。还是观察的方法、带距离的描写更舒服、更可信”。
浓郁的影像化表达是万玛才旦小说的另一特征。如《塔洛》的开篇,塔洛平常都扎着小辫子,那根小辫子总是在他的后脑勺上晃来晃去的,很扎眼。此处对于“小辫子”的描写,就采用了类似电影特写镜头的方式,突显人物外貌特点以及其后隐喻的人物精神特质。又如小说《气球》的开头,达杰翻遍了抽屉,翻遍了枕头底下,翻遍了所有能翻的地方,最后也没有翻到那个玩意儿。他问他的老婆卓嘎,她说她也没有看到。完事之后,他就骑着他那辆破摩托车上路了。这里一连串的“翻遍”和随后的夫妻间问答,像极了一组展示人物动作的剪辑镜头,“完事之后”则是转场镜头,开启了下一场景的故事。
通篇可见的画面感给万玛才旦的小说带来一种令读者身临其境的效果,并营造出一种类似纪录电影的纪实感。如前所述,万玛才旦的小说人物主要依靠行为、语言展露内心情感,而对于人物的深层精神世界,万玛才旦同样采取“做实”的方法。他为人物设置了诸如梦境、幻境、死后的灵魂世界、醉酒后的迷醉世界等异质世界,在尊重现实生活逻辑的前提下,还是通过行为、语言来展示他们彼时的所思所感。这种创作方法或曰美学风格,与电影的人物塑造方式较为接近。和那些采用大段人物内心活动描写的文学作品相比,电影显然更擅长用音(语言)画(动作)表现人物。在这个意义上,万玛才旦的小说具有电影的表达特点。另一方面,就电影受到的小说影响而言,他的电影呈现出对人物的心理、情感甚至潜意识的着重描述。万玛才旦会在影片中特意为人物设置梦境、回忆、幻觉等异质空间,通过视觉变形、色调差异、情节闪回,而运用非大段独白或者对白为人物的精神世界赋形。
虽然万玛才旦的艺术创作兼顾了文字和影像两种媒介的表现要点,但要实现二者的顺畅转换仍需做出诸多调整。从小说到电影,改编涉及的首要问题就是对文学作品的解读。即便是改编自己的小说,小说文本与电影的关系也并不是情节、场景、人物、对白的简单视觉转化。尼尔.辛亚德认为文学作品的改编类似文学评论,“电影改编选取小说的某些部分,对其中的细节扩展或压缩,进而创造性地改写人物形象。由此,电影改编如同文学评论一样对原作做出新的阐释。”很多电影理论家也认为,从文学到电影的转换(通常被称为改编)既非表演又非文学的图解,而是要翻译为电影语言。对于自己作品的改编,万玛才旦基本遵从了上述要点,他认为相对文学而言,电影改编的关键,就是要通过一些比较外化的手段,为电影找到了一种适合故事的讲述方法。
电影的本质是通过视觉幻想强烈地吸引观众,因而在电影向观众传递信息的“电影叙事交流”中,鲜明的视觉特性十分重要。从短片《草原》起,万玛才旦的电影作品就很注重视觉特性。《静静的玛尼石》和《寻找智美更登》对长镜头的运用,《塔洛》的黑白影像和“镜像”隐喻,《撞死了一只羊》中的对称构图以及对墨镜、后视镜等镜面反射颇具先锋性的探索,都形成了十分符合剧作精神的美学风格。万玛才旦生前上映的最后一部院线作品《气球》,其对影像视觉风格化探索和现实主义追求,可谓对多部前作做出了总体性回顾。例如,万玛才旦一直偏爱的对比与平行,他认为“对比与镜像式的表达是比较直接的,让你一下子看到两者之间的区别”。这种方法在《一块红布》《八只羊》《午后》等小说就频繁使用,电影《塔洛》中的塔洛与杨措、塔洛的辫子和光头,《撞死了一只羊》中同名“金巴”的司机和杀手,被撞死的羊和肉摊买的羊等等,都构成微妙了的对比。电影《气球》中,全片的冷色调为影片带来一种深入人物精神世界的冷郁,烟囱、门框、水沟、电线等作为中线形成了对位分割构图,更暗合了剧中多重的对比关系。万玛才旦除了设置女主角卓嘎与卫生站女大夫周措、白色的避孕套与红色的气球、爷爷的马背和达杰的摩托车等精妙对位,还特意增加了小说中所没有的姐妹对比。卓嘎与妹妹卓玛同样重情,但她们守护婚姻、出家断情的不同选择,构成了相互的补充和对比,为叙事增加了人性的深度,也突显了卓嘎的意图打胎是藏区普通牧民妇女,宗教之外影响生育选择的别样因素。对位之外,万玛才旦还以梦境、回忆等场景多次出现的方式,为《气球》设置了多处主叙述场景之外的心理空间。如两个小儿子梦中揭下了哥哥江洋身上象征奶奶转世的黑痣,既隐含了对轮回观的略微怀疑,又带有想让自己成为家人转世者获得更多关爱的复杂心绪。丈夫达杰在种羊主人家醉酒后产生的幻觉,预示了家庭即将到来的变故。江洋梦中去世爷爷的倒影徘徊在水天一色、天光粼粼的湖边,江洋无法追逐也不能对话,表达了江洋对爷爷的依恋和对轮回观的笃信,为结尾部分父子闯进手术室埋下伏笔,这一开放性的结尾,也为影片留出更宽阔的思考空间。

《塔洛》(2015)

《撞死了一只羊》(2018)

《气球》(2020)
电影《气球》始于“白气球”终于“红气球”,鲜明的视觉意象代替了剧情片常见的结局,一众角色身处各地抬头仰望,这一刻希望与惆怅并存。这种印象式的“一瞥”蕴含了万玛才旦对身处时代的理解。“在他那里,试图完整地描摹世界、解释生活,或者对未来和未知做出承诺和预测是一种渎神行为——他能做的是讲述‘因缘’”。克拉考尔认为,“作为通俗艺术的电影为人民洞察一个民族的无意识动机和幻想提供了可能”,在这个意义上,万玛才旦的多部电影,以复杂又混沌的“此刻”,无限接近了他所理解的“现实”。
(原刊于《当代文坛》2023年第4期。作者略有修改,注释见原文)

【作者简介】刘春,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理事,上海电影评论学会理事,上海国际文化学会秘书长,《上海电影产业发展蓝皮书》执行主编。研究方向为电影批评、电影产业、影视创意写作。
主编:朱生坚
编辑:张晴柔
运维:任洁
制作:小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