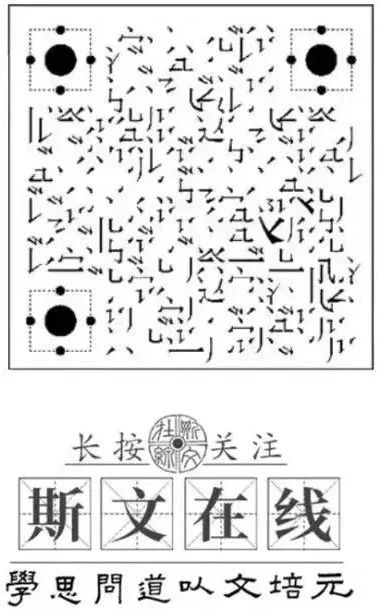2022 年 8 月,在国际博物馆协会布拉格大会上通过了博物馆的新定义,强调了博物馆“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具体执行维度,涉及“可及性” “包容性”“多样性”“可持续性” “社区” “参与” “反思”等关键点,回应了时代变革的新需求。由于博物馆具备实物性、科学性、体验性、系统性和自主性等资源优势,其社会服务所能达到的一个重要价值目标就是培养公众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既具有文化层面的意义,也具有政治层面的意义。在博物馆中,无论是对包含国家制度体系、公民身份和权利等政治共同体的认同,还是对所处的物质、知识和精神等整体生活方式的认同,都不同于“国家结构体系的质量及其对民众塑造”的实际体验,而是通过“文化”——这一贯穿在不同社会实践中的整合性要素予以呈现的。在探讨国家民族议题时,博物馆积极尝试对共通话语的创设,依托有力的物化证据和空间体验,为观众提供了理解历史、社会和个人的新方式,从而形成了“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的特殊融合。对认同价值,尤其是民族国家认同的追求在我国博物馆中更显突出。吕烈丹(Tracy L-D LU)在《中国博物馆:权力、政治与认同》(Museums in China: Power, Politics and Identities)一书中认为博物馆是国家推行意识形态和公民教育的重要场所,我国使用博物馆收藏所策划的展览、物件的阐释、经由博物馆呈现的历史均是国家话语的物化显现。但过多使用国家话语建构认同的方式反映在当下观众的认知偏好中未必始终奏效,邓腾克(Kirk Denton)认为还应当关注其他影响博物馆的社会力量,以展现博物馆协商性的叙事话语。博物馆应当为公众创造联结历史与当下、群体与整体、艺术与现实、自然与人类、专业与跨界等互动关系的诠释框架,站在多重社会身份的视角转译社会发展经验,强化认知理解、情感疏导,鼓励分享与学习,最终实现认同理性的回归。
一、博物馆“国家认同建构”角色的历史演进
早在 17 世纪末走进公众生活之前,博物馆就已经在定义国族和国族身份方面扮演了特殊的角色。在储藏室、画廊等博物馆雏形中,大量具有权力、阶级、宗教和文化象征意义的物品被收藏和展示。18世纪后期,欧洲各国进行殖民扩张时,艺术被认为“是开启往昔的一把钥匙,这一信仰激起一股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欧洲各国都想把自己的历史放在艺术繁荣的中心地位”。博物馆成为欧洲各国展示本国历史文化和从他国掠夺而来的艺术珍品的场所,也是宗主国强化“帝国知识体系”的手段之一,用以征服和控制殖民地民众。此外,法国大革命使天赋人权、三权分立的民主思想取代了贵族政治秩序。1793 年卢浮宫(the Louvre)向公众开放。但真正率先将博物馆作为社会教育工具的实践发生在美国。18 世纪后期公共博物馆在南卡罗来纳州出现。19 世纪中期,波士顿自然博物馆、史密森尼博物学院和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逐一建成开放。到了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殖民体系进一步影响了全球文化走向,“种族优越论”“同化论”等观点强调了博物馆维系民族国家共同体的纽带功能。
但此后,文化“同化论”遭到批判,焦万尼·巴蒂斯达·维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和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 Johann Gottfried Herder) 认为:“每个人类社会、每个民族等都具有它自己独特的理想、标准、生活、思想和行为方式。”提出了“多元文化主义”理论,博物馆被认为应当在存续不同文化和文明发展轨迹方面展现不可替代的作用。20 世纪中后期,随着后殖民主义的兴起,博物馆成为了殖民地或附庸国保护自身历史文化的重要象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后进国家的文化成熟度,也为文物归还做出了积极贡献。例如,19 世纪,在对柬埔寨的殖民统治期间,法国人以自己的认知框架赋予了吴哥窟遗址新的内容和形象,并利用博物馆和影像资料等手段予以强化,成为日后柬埔寨人视吴哥窟为自己国家、民族象征的基础。此外,20 世纪中叶,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影响,各国亟待修复民族国家认同、重构经济文化秩序、反思人类共同命运。 因此,纪念类博物馆在全球快速发展,如苏联建立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全景纪念馆( thePanoramic Museum of the battle of Stalingrad)、布列斯特要塞英雄纪念馆( Memorial Complex Brest HeroFortress)等,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为重要的集体记忆激发公民的认同感,帮助塑造公众的道德、心理和行为特征。 到了 20 世纪 60—80 年代,对民族国家认同的内涵、外延和建构方式的认知出现了更多分野。 其一,苏联剧变、东欧解体引发的民族主义浪潮,引起了政治学和文化领域对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之间关系和区别的再审视。两者互为前提,要强化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文化是重要的实现方式。文化以民族为载体依附于具体的国家,成为民族成员深层的历史记忆和民族国家的精神积累。其二,社会认同理论提出,要关注社会中的“自我”,认为认同的形成需要在社会结构和个体行为中间建立“自我”的动力结构,强调个体与社会的互动。认同具有群体性,团体的传统价值对个人成长具有特殊意义。其三,人本主义地理学家提出“地方感”概念。 在与环境的交换过程中人会产生地方依恋,这被认为是影响地方认同的主要因素。除居住环境外,人对一些特殊地点,如游憩目的地等也会产生相应的情感依附。 他们强调建构地方的独特性,在不同的空间尺度和时间维度上增强地方感。其四,全球陆续兴起了以特定群体身份为主体的“身份政治”运动,其目的在于破除种族、性别及不同形式的歧视,从而强化不同对象的群体认同、社会认同和民族国家认同。同时,全球身份流动加剧,传统的认同建构方式面临挑战,需要平衡不同文化和语境间的关联性,新方式的转变承认和接受了在身份创造过程中的文化偶然性,以及认同的不稳定性。认同建构要着力在社会不同群体间的对话、理解和包容上,既涉及特定群体身份的界定,也涉及打破群际间的对立价值。这一时期公众对“过去”和“当下”的区别意识得到增强,也影响到了“文化遗产学”和“博物馆学” 的发展,人们开始溯源民族国家的历史文化脉络及相关原始凭证,以形成、强化和维持现代人所需的归属感和稳定感。 在上述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诞生于 20 世纪70—80 年代的“新博物馆学”积极探索着“社会系统与物理的三维环境之间的关系的本质,也始终意识到代表的人类学”。博物馆领域出现了一系列批判性分析,揭示了物件、知识体系和意识形态说服过程之间关系的结构和程序。这些分析包括对博物馆在定义历史和文化身份等方面权威地位的再审视、对旧有一些僵化的和过于物化的博物馆展陈理念进行批评等。在新的理论架构中,博物馆建构国家认同的功能除了体现在对国家发展成就、制度路线、文化特征和英雄人物的展示外,产生了一些新的呈现路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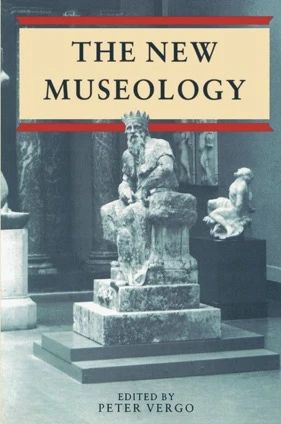
Peter Vergo, The New Museology, Reaktion Books, 1989
首先体现在继续促进文物归还和对源出社群的赋权上,使他们在文物阐释的竞逐中更具话语地位,用以展现文物所能支撑的民族和国家身份。2022 年,英国格拉斯哥市议会“跨党派的掠夺与归还工作组”( Cross-party Working Group for Repatriation andSpoliation)收到了数个来自他国的文物归还请求,陆续会将相关文物归还给尼日利亚、贝宁共和国和印度等国。博物馆践行“去殖民化”行动,意在履行博物馆维护文化正义的使命,让文物原籍国或原属民族成为自己文化的管理者。认同实质是确立人的归属,文物归还有助于在原籍国的国民中强化文化意识的情感黏合,形成文物所载历史维度和归还行为现实维度的结合。 其次体现在探索自身与在地社区建立联系的可能性,重新审视与社区的对话和权力关系。博物馆尝试着把自身的知识权威下放给公众,在联结社区的过程中,吸收不同个体或群体的故事、物件和表达。美国布鲁克林博物馆(Brooklyn Museum)在 2008 年举办了“咔哒:一个由民众共同策划的展览”,试图探讨大众对艺术的评判是否比专家更“智慧”。又如,美国亚利桑那历史协会的常设展览“让我们创造历史”积极地向社区居民征集藏品,与他们共同商议展览主题和内容策划,在观点碰撞中找到更合适的叙事方式。哈贝马斯认为,认同的一种意义是建立在沟通能力、理性和容忍之上的。博物馆希望通过不同的自下而上的方式促进社群发展,强化博物馆的民主化程度,从而提炼公众的文化共识,再借力博物馆的综合优势在社群中将文化维持和传承。基于对文化共识的具体诠释,逐步增强文化认同,由此展现国家共同体的利益诉求和价值导向。 再次体现在对不同身份群体的关注、尊重和理解。传统的博物馆以认同建构为目的的叙事表达往往因循着增强部分群体归属感和另一部分群体区分感的模式。斯图尔特·霍尔( Stuart Hall)认为,经典的身份创造模式是基于对他者的排斥,即只有在求助于不在场的、否定的身份时,才能想象一个在场的、肯定的身份。这种叙事方式会清晰地说明身份建立的主导权和认同建构的依据,但往往只指向目标群体。在博物馆的传统角色中,会选择与正在建构的认同主题相符的资料出现在具体叙事中,将过去视为一段线性的、总体化的历史,致力于创造和利用赋予过去连贯性和目的性的官方表达。而由新博物馆学理念推动,博物馆展览逐渐将目光投射到了体现群体身份和差异的主题上,这类展览需要把“政治、认识论和美学交织在一起”,打破以身份区分为认同建构逻辑起点的叙事,而转变至以包容融合为出发点的归属感的营造。1989年,法国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 the Centre Pompidou)和格兰德哈雷文化中心(the Grande Halle de La Villene)分别举办了由让-于贝尔·马尔丹 ( Jean-Hubert Martin )策展的“大地魔术师” (Magiciens de la terre)展览,展品来自于50位西方艺术家和50位非西方艺术家。展览以文化多样性和艺术平等性的概念打破了艺术领域内欧洲中心主义与“边缘”地域的传统分界。当置于一个多元文化共同作用的社会语境中,尊重不同身份群体的历史文化背景和价值观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以文化包容的方式增强文化共同体的凝聚力,从而反映在他们对所处社区、城市、地区和国家更深层次的融入感。

“大地魔术师”展览现场,1989年
二、 我国博物馆建构国家认同的特征分析
与西方认同建构的发展路径不同,在传统中国的时空观中,认同是天下、国家、文化“三位一体”的。天下是文化意义上的概念,是一种四海公认的价值尺度。中国人普遍认同自己文化的优越性,自然地将自身置于世界的中心。张汝伦认为“传统中国没有认同问题,或者说认同不是一个问题”。但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一系列的战争和政治动荡使固有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遭到了巨大冲击。当时出现了“中体西用”说,主张在基本维持传统纲常的前提下,学习西方的先进事物和技术文化。一些西方传教士和知识分子,以及游历官绅和留学生逐步将西方博物馆理念带到中国。他们敏锐地观察到西方博物馆的公共教育与传播属性,以转变古物私藏的旧有观念,积极探索如何在救亡图存的社会危局中以新型博物馆的形式兴贤育才、改造国民性。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张謇、李济等纷纷呼吁古物公有化、博物馆公共化的新发展路径。此时,博物馆更多地是推动古物向公众展示,让公众在参观中了解民族国家的历史文化,提升知识素养。古物收藏由私转公实际上已将国家认同建构排在了博物馆的潜在功能之列。但是,依照西方模式创办的博物馆样态并不能完全适用于中国本土化的发展和需求环境,尤其在对文化认同的塑造和强化、对民族特性的解读和呈现、对成为一个独立民族国家合法性根据的挖掘和提供等方面难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思考博物馆如何进行国家认同建构时,应该秉持陈寅恪所提出的“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的态度。1925 年故宫博物院建成开放和 1930 年中国博物馆协会成立可以说是博物馆本土化探索的标志性节点。
到了 20 世纪中期,博物馆的政治表达随着革命文化的出现而被进一步强化。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博物馆对国家认同建构的实现更多的是附着在对革命文化的展示与传播以及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上的。1961 年,中国革命博物馆正式开放。这一时期,遵义会议纪念馆、广州起义纪念馆、古田会议纪念馆、瑞金革命纪念馆等中国共产党革命纪念馆也相继建成。这些场馆多采用宏观的、进步式、英雄式叙事方式呈现内容,将政治认同的建构目标强烈地置于叙事的外显架构中。同时,如何阐释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的关系也是博物馆所要处理的重要议题之一。现代国家既强调不同民族的特质性,又趋于在认同层面将其整合成一个“国族”概念,使得“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成为相互依存的统一体。但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产生与侧重是有所差异的。民族认同偏向文化心理上的归属感和亲缘关系,涉及民族历史、地域、风俗、艺术、语言等,国家认同更偏重对个体所归属的政治共同体的辨识、区分和认可,涉及国家制度、政治观念、法律体系、公民权利与义务等。两者之间,民族认同更具先赋性,与个体与生俱来的生活环境和文化浸润息息相关。相较而言,国家认同的自发性稍弱,需要国家与个体间不断进行双向互动以达到增强和维持认同感的目的。在我国语境中,费孝通将中华民族结构概括为“多元一体格局”,这种结构具有较强的民族整合统摄性、包容性和持续性。个体在处理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的关系时,费孝通认为,作为国家认同的中华民族相对于社会成员的民族认同而言,是高一个层次的民族认同意识,其关键在于确认认同层级中的优先级序。国家认同与中华民族认同的建构又应当具备统一的路径,这也反映在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是高度互补的,政治认同的共同利益诉求和核心价值取向与文化认同的民族诠释相辅相成。国家认同建构需要兼顾对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关照,兼具思想与情感关联的国民意识必须依靠历史和现实的文化联系与价值表达。因此,博物馆需要保存、记录和展示不同民族独特的历史文化记忆。自 1998 年起,贵州、内蒙古、云南等地先后建立生态博物馆,依靠当地居民积极保护自己民族的文化遗产,并注入产业要素产生经济收益,提升当地居民对本民族文化、对现实生活状态的归属感。博物馆也需要在“中华民族”文化框架中提炼不同民族的共性伦理。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和地方政府层面就开展了广泛的少数民族文化、社会和历史资料的征集保护工作,一些地方和院校纷纷建设了民族博物馆和民族文化宫,在展示民族特色文化的同时传播各民族平等团结的价值取向。从而以民族文化认同为支点推动国家政治认同建构的思想凝聚、实践创新和政治资源的利益调适及共享。
近年来,社会的转型促使我国博物馆持续深入地走向公共领域,博物馆对国家认同的建构越来越下沉到与公众建立有效对话和互动之中。博物馆开展普遍性公民教育的必要性不断提高,也衍生出更复杂的博物馆认同建构内涵。我国博物馆在话语表述中持续向官方与民间观点结合、历史传统与现实社会互动、全人群与分众化对象化叙事区分、政治规训与休闲社交功能叠加、物理空间与虚拟空间相融等方向转变。一方面,博物馆对边界模糊的个体社会角色予以更大程度的包容,呈现对话性叙事策略,在不同地域、文化和时代之间创造联系。这种对传统认同内涵的挑战与拓展首先表现在如何在广泛的社会背景下产生对他人经历的同理心。其次,表现在如何在官方话语中纳入民间和个人叙事。博物馆使具有不同种族和社会经济背景的观众都能够参与公共记忆的谈判,为差异性观点提供安全空间。再次,表现在如何发挥记忆交流功能,赋予故事超越纯粹私人或单一群体的意义,在更广范围内产生归属感。如深圳(宝安)劳务工博物馆以职业角色建构认同,通过劳务工群体记忆的共享,与其他社会群体建立共同的价值观、态度和兴趣感。一般而言,个体会持续不断地进行自我的重新判断。博物馆对于个体社会身份认同的留意与关怀为公众提供了更多关于他们想要成为什么样的自我以及想要建立什么样的社会关系的选择。最后,表现在博物馆从观众研究的视角,开始剖析不同观众群体的心理、行为和知识结构与博物馆参观体验实效的关联。相较于以传统思想政治传播方式建构国家认同,时下观众更期望在博物馆等非正式教育环境中,以生活化叙事和“休闲学习”的方式完成参观体验,而建构国家认同所需的价值观塑造是自然融合在其中“日用而不觉”的。
另一方面,在全球化背景下,博物馆也转向了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共同价值追求的关注,再由此反馈到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认同建构上。近年来,中国博物馆积极组织筹办各类国际历史文化展,如 2018 年,中国美术馆举办了“‘美美与共’ 国际艺术作品展”,关涉了当前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恐怖主义、难民危机、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因素挑战。通过通识话题引导和文化遗产信息共享,博物馆推动观众接受不同的文化规范和价值观,将他们与全球集体身份相联,形成一种后现代的认同建构,即强调不同国家、民族和文化主体之间的交流和共存,并由此转向对流动的、复合的、混杂的社会身份的关注,尝试以自身优势阐述国家民族或不同文化与其所处语境间的关联性,化解认同危机。除利用既有珍贵藏品外,博物馆也充分发挥“公民文化”( civic culture) 的认同建构能力,许多由公众或专业人士提供的日常用品、记忆资料和创意表达形式被纳入博物馆的叙事载体序列。南京国际和平海报双年展每年向全球征集设计作品,通过海报这种世界性的视觉语言,跨越国家、民族、语言和文化的障碍,共述“和平”主题。“公民文化”调和了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公民互动,能有效解决多元文化主义的问题,具有差异性、参与性、平等性等特征。博物馆利用“公民文化”使其所用的故事能够支持身份重叠,有利于“世界社会”的建立,打造共同的或彼此理解的价值观,促使不同观点在积累的过程中达到有效的平衡和融合。
此外,网络已成为社会交往的重要载体,为认同建构提供了更多元的发生渠道。 不过,虚拟空间的出现也使得认同建构的基础、结构和主导因素出现变迁。博物馆利用数字平台搭建虚拟空间中的传播圈层,也利用元宇宙、人工智能等技术突破展览时空限制,探索在非传统文化空间中破解认同碎片化困境的路径。技术推动认同建构既有潜在的有利面,也有不利面。技术促使大量个人和集体记忆能够被更快更便捷地存储、编辑和呈现。但随着技术记忆自主权的增强,部分图像会自动承接记忆而脱离原始语境,这可能会导致对细节和复杂性关注的流失。未来,博物馆建构认同的关键就在于如何组织普遍性和共同性与特殊性和差异性之间的双螺旋结构,在空间、时间及价值等维度上创建更具普遍意义和时代意义的认同表征系统和符号话语体系。

南京国际和平海报双年展
三、博物馆环境中认同建构的路径与方法
从文化传播的视角审视,博物馆建构认同的路径在一定程度上与霍尔提出的“文化循环”模型相似,即从文化符码的创设与共享为起点,到文化符码表征实践的创造性和现代性实施,再到文化符码“再建构意义”的稳定和社会认可,逐渐孵化出当代认同模式。 具体而言,这种路径就是以实物资料的收集与整理为基本核心,利用艺术化、情节化、关联化等处理方式,阐释多维信息、提炼概念符号、塑造空间场域,将对大众文化的理解嵌入到关于“共同经验”的社会实践与文化过程的经验性考察之中,为认同创设语境化的“意义结构”,建立认同话语。博物馆既展现了政治认同所需的集体记忆立场与裁决,也融合了感性的生活化教育。从而增强了公众的审美体验,以及情感层面的认同驱动、选择和矫正。博物馆提供的各认同要素间的组合关系创造、强化和维系了“能够带来具体真实社会影响的主体身份”,最终促使受众能够回归认知理性和实践理性,达到持续性认同维护的目标。
(一) 实物资料的收集与整理
认同建构是社会化的结果,需要个体不断接触集体文化元素。公共博物馆的主要目的是收集、保存和展示具有制度价值和教育意义的物件。珍妮特·马斯汀(Janet Marstine)认为:“在博物馆内,物件不再仅仅是物件,博物馆叙事建构了民族身份,并使各群落合法化。”通过承载着集体记忆的物件,博物馆拥有了促进身份发展和认同建构的核心基础。博物馆所及的实物资料包括实物展品、辅助材料、影像资料、现象复演等。其中,前三类相较而言在建构认同时更常被涉及。
1. 实物展品。凯文·摩尔(Kevin Moore)提出了博物馆“真实力量的三重概念”,包含“真实的事物、真实的地方和真实的人”。实物展品是这种真实性最基本的依托。尽管在博物馆中它们脱离了原始环境,但却是时间性具体化的深层历史证据。在发挥认同建构功能时,实物展品具有自我独特性、稳定性和连贯性等优势。首先它们作为文体论层面上的文化产品( a stylisticcultural production)被理解,关注其形式特征所代表的符号象征意义。其次是置于多元文化模式的变异范围之中被理解,需避免对其进行简单概括。例如,实物展品在博物馆环境中产生了主要功能变化和次要功能变化。前者指的是实物本身使用性的差异,后者指的是物质文化所及社会背景。实物展品可以发挥催化、关联、分离和桥接等物质能力,促成认同的多维表征,如个体或群体的社会角色结构、社会地位变化、代际价值取向等,并涉及权力、利益和意识形态的社会策略,帮助观众积极调解思想和实践。
2.辅助材料。辅助材料的制作一般会受到国民族理想愿景和政治需求,或制作者所处时代 家、审话语偏好和媒体材料等因素的影响,辅助材料本身美就承载了重要的集体记忆和国家民族元素。例如,特雷布林卡模型(the Treblinka model)由特雷布林卡灭绝营中70名幸存者之一的夏姆·斯塔杰( Chaim Sztajer)制作,后捐赠给了墨尔本犹太人大屠杀博物馆和研究中心( JewishHolocaust Museumand ResearchCentre)。斯塔杰完成了广泛的细节描绘,使模型充满了他作为幸存者的复杂情感。模型不再仅仅展现了一段历史痕迹,更是对一段时间内实际记忆和生活经历的集中物化,被赋予了生命力。辅助材料有时提供了一种超然的视角,将事件背景、个人元素与材料形式结合,使其拥有相对完整和充实的观点,尽管浓缩却达到了扩大意义的效果。

特雷布林卡模型的制作
3. 影像资料。影像资料被视为充满力量的记忆文本,是博物馆实物资料中情感浓度最强烈的类别之一。作为“历史对象”,它们将集体和个人记忆通过回忆、想象和再现变得感性和可见。在制造和使用的过程中,它们被安置、分散、损坏、重塑、修剪,涵盖了制造者、使用者和流传者等多方的意志和行为。例如,照片在直接呈现图像所指信息的同时,也可能激发了轻抚、亲吻、撕裂、哀悼、交换等行为,在照片的日常使用中重新确立这些行为所体现的分析意义,表明了人、信息索引和实物资料之间的不可分割性。2018年,首都博物馆举办了“国家相册 致敬历史”展,其中展示了一幅 1948 年冬,淮海战役期间,解放军战士围观双堆集前沿阵地举办战地影展的照片。除照片对战地影展的记录意义外,更重要的是记录了战士们观看影展时高兴、自豪的神态和行为,赋予了照片多层次的认同建构价值。影像资料从视觉和听觉开始,帮助博物馆观众理解信息对象,逐渐引发他们的多感官触动,并在信息分析中注意到了这些人工制品的行为维度,使抽象的国家民族共同体得以具像化、人格化。在强化认同意识时,博物馆语境中的影像资料经由选择和组合,连接和凸显了图像的社会功能,聚焦又延伸了文字化记录,它们交织着不同的动态故事,反复演绎,并利用其情感特质,将不同主体联系在一起。
(二) 信息阐释与话语建构
博物馆将看似分离甚至支离破碎的实物资料组织到展览脉络中,展开不同维度的信息阐释,使得在一定程度上能重构实物脱离的原始语境,塑造合法的国家记忆和集体记忆叙事。官方维度的宏大叙事能够为公共记忆提供总体性的阐述框架,有助于界定认同话语的边界和意义。 民间维度的个人或群体叙事能够提供公共记忆的多元面向,以更充分地代表不同群体的文化价值观。此外,在现代博物馆中认同话语不仅呈现了共识性的记忆表征,还需要妥善处理冲突记忆的表达,有效发挥“社会黏合剂”作用。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又难免受到不同权利主体的影响,最终认同话语往往突出的是记忆的首选版本。基于记忆的认同话语创设是持续在竞争和协商中进行的动态演绎,博物馆对认同的建构需要置于社会文化背景下在纪念与遗忘之间选择和平衡,在定义“自我” 和“他者”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英国布里斯托尔市博物馆(the Bristol City Museum)推出了一个名为“创意空间”(Creative Space)的社区阐释项目,他们认为实物资料体现了那些创造、使用或珍视它的人的感受及个人经历。对于馆内所藏的中国瓷器,他们打破了传统说明文字的撰写方法。策展人并没有把物件定位在其原本所处的历史语境中,而是鼓励观众利用自身体验赋予物件新的意义,产生文化理解和认同。鉴于此,在现代博物馆中以强化认同为目标的展览叙事可以从不同维度入手。
其一,时间维度。博物馆的认同叙事许多都以历史为基础,利用相关资料将其情节化。博物馆应当关切的是传统历史、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以及当下社会演进和未来趋势这三个历史时空如何相互渗透和支撑。传统历史时空是培育认同话语所需要的重要文化基础,产生了独特的、相对稳定的价值观、共同心理和精神信念。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时空为认同话语的建立提供了制度层面的建设实践,形成了“国家”、“地方”、“公民”等概念的现实版本。当下社会演进和未来趋势时空是认同话语涉及最复杂和最具挑战的社会背景,既需要站在国家立场阐释现有社会制度的历史与时代合理性,也需要站在世界范围阐释多元价值观并存及相互影响的社会格局,涵盖的问题如国家对重大事件的态度、对当下社会发展的历史定位、对未来趋向的把握等。
其二,空间维度。博物馆是文化记忆、知识生产和消费的场所,也是根据当代社会环境和观众关注的议题来讨论过去意义的场所。博物馆围绕实物资料提炼概念符号,包括国家符号、文化符号和历史符号等,创设文化情境。博物馆的空间叙事首先需要打造物理空间的记忆场域。如以色列亚德瓦西姆大屠杀纪念馆( Yad Vashem Memorial) 与赫茨尔山( MountHerzl)国家公墓相联、法国凡尔登战役纪念馆(VerdunMemorial Museum)的“在战争废墟中崛起新生” 等设计,表明了认同话语可以经由物理空间而创造和强化。物理空间被认为具有回溯性和前瞻性双重功能,前者促使观众回溯历史,唤醒记忆,后者能够将历史与发展勾连,促使观众获得历史认同,明确未来方向。其次,博物馆也需要营造仪式场域,这是带着必要的文化隐喻的,如“5. 12”汶川特大地震纪念馆的“裂痕”建筑设计、美国“9. 11”纪念馆(9 / 11 MemorialMuseum)前的纪念水池等。仪式场域会先暂时将观众与其既有的特定社会身份分离,然后将自身介于博物馆空间中结构化的社会代理角色和可接受的社会规范之间,最后对观众重新面向社会后的角色进行再次定义。此外,虚拟空间也是博物馆叙事传播的重要路径。虚拟空间有较强的导航性,能够为观众提供更具脉络性的角色转变依据。而当虚拟现实、元宇宙等技术运用于博物馆后,观众可获得的多感官体验也不断增强。
其三,价值维度。博物馆建构认同的一项基本任务是运用有效和合理的方式将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和认知逻辑合理地安排进博物馆叙事中具有特定历史与文化的社会之中,服务于核心价值体系,使其保持代代相传的延续性。南京博物院曾举办“和·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之道”等展览,就是在价值立意的层面上用当代人的判断去提炼中华传统文化。对叙事话语中社会文化价值的关注,博物馆要展现立场,包括情感立场,展示和定位自我和他人;认知立场,展示知识信息来源及其确定性程度。也要展现社会角色、社会关系和所属群体,包括展示相应主体的社会行为和社会参与形式。因此,博物馆建构认同话语的价值维度可包括:从历史脉络和社会背景中寻找现代国家产生与发展的基础和逻辑;从社会实践表征中寻找国家治理模式和国家制度的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从社会生活和社会伦理中寻找个体与国家互动中获得的公民权利;从物质和非物质遗产中寻找国家多元化与一体化共存发展的精神内核等。
(三) 情感依恋与审美体验
受实物资料、信息阐释和话语建构等要素支撑,博物馆强化认同的优势还在于能将上述要素化作情感和审美层面上的共鸣。情感依恋是个体除功能性依恋外,对外部集体产生认同的重要表现。尤其在外界环境的不确定性日益加剧的情况下,集体的整合力量取决于它能在多大程度上调动与亲缘关系及个人经验密切相关的情感。由于博物馆对认同要素形成了时空范畴内的高密度集聚,所以其“调动”能力是远高于其他公共载体的。就个人层面而言,博物馆帮助观众在一定空间内形成了精神、情感和心理环境的自我指涉。博物馆需要关注如何在认同要素和观众之间建立呼应关系,使观众能够在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中寻找到博物馆叙事中相对应的自我参照,了解身份的价值和意义。但博物馆内的情感实践不仅仅与纯粹的个人心理相关,也涉及了情感依恋的社会层面,主要体现在社区关系、生活质量等。博物馆是对公共记忆的表达,需要企及当代社会分析和进一步社会建设等主题。这种与集体归属相关的情感承诺充分发挥了情感的驱动、选择、矫正与掩护等功能,支撑了认同的产生、增进和维持。当然,情感依恋不仅仅是针对观众对其所属民族、国家和其他集体身份的,也涵盖了观众对“他人”经历的理解。美国宽容博物馆 (the Museum of Tolerance)将自身关注点定位在:(1)大屠杀事件;(2)宽容在当代世界中的重要性。通过提炼共性价值,博物馆策划了思想驱动型的互动性展览,引导观众重新评估社会环境,建立关心他人和尊重人类尊严的价值观。越来越多的展览嫁接起了超越国家、民族的情感联系。
博物馆认同建构的情感路径可以是:借助实物资料及象征性符号、空间排布、情境还原来完成情感触动;通过围绕集体叙事话语和价值观念的阐发,描绘出共同的历史文化轮廓,实现情感强化;与观众个人经历或共性价值观建立联系, 体现情感的实践意义等。
审美体验是博物馆在面对受现代身份价值观影响的观众时,除政治因素之外建构认同的重要方式,也是认同建构的社会反馈评价中不可或缺的维度。现代性认同倾向于通过生活休闲、文化消费、体验参与等方式建立和强化。博物馆对审美价值的塑造可以“超越单纯的符号所指和形象扮饰以体现更为基础的自然生存-生命根源和更为深潜的公共性精神本义,而后成为认同的理想媒介”。审美的意识形态功能是缓和困扰现代思想的多极矛盾,如主体和客体之间、普遍和特殊之间、理性和悲情之间等,成为现代价值形态中的一种变革力量。博物馆创设认同话语时所及的审美体验主要包含三个方面。首先,是对展览叙事空间和载体的艺术化处理,如图文版设计、展览空间照明、动线布局等。苏格兰现代美术馆(Scottish National Gallery of Modern Art)在序厅中强调了策展理念———“通过个人故事、电影、音乐、诗歌和物件,希望你能发现苏格兰生活中众所周知和被忽视的方方面面。”根据布展安排,实物展品实际上是观众进入展厅看到的最后一个部分,它们已被深深地嵌入在了展厅所营造的视觉、影像和音频框架中,反而成为了展览中有趣的例证,而非叙事的关键。其次,是针对展览叙事所需,创作及研发艺术作品和文化衍生品。这些艺术处理的产品本身就已经成为了博物馆展项中的一部分,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展现现代性文化的杂糅。它们在研发和实施阶段都与受众身份感有关,也多与受众和环境的交互有关,此处所谓的“环境”既是物理的,也是人际的和文化的。 再次,是对博物馆所属建筑整体或遗址遗迹空间的艺术化呈现。这些场所多是所在区域重要的文化景观,仅仅其外观就有强烈的认同建构能力,能够增强地区居民的自豪感、自尊感,产生场所依恋。 一般情况下,公众对公共空间更高的审美评价会带来更高的地方和国家认同感。但需要注意的是,个体是无法同时兼顾“内在”体验和“外在” 反思的。若沉浸在审美体验中,可能会因情绪影响而不知所措;反之,若完全以逻辑和超然的方式进行批判性评估,又可能会失去体验自发审美愉悦的能力。 适当平衡参与和分离的视角是“审美形式”和相关体验的基础。
(四) 认同理性的回归
情感依恋与审美体验激发了认同建构所需的内驱力和共情力,基于上述几个阶段,博物馆能够迈向认同建构的最终目标———培育具有理性自觉的观众,以维护和强化认同。博物馆所欲达到的认同理性包含了认知理性和实践理性。
认知理性层面,要求博物馆积极推进观众对个人、群体和国家民族间不可分离的伦理关系的认知并由此增强共同体意识。观众会认为自身不仅是不司的个体,更是所在群体类别中相似的原型代表,产生从独特的属性和个人差异到共享的社会集体成员身份的认知转变。公众在脱离博物馆语境后,也可以向集体目标中稳定和可靠的方向发展。除上文已提及的记忆形式外,还需要博物馆为认知理性的验证、推理,以及必要的理性怀疑等其他表现形式提供体验和思考的支撑。在我国,博物馆建构认同所需的认知理性旨在生动表明国家治理、公民权利和民族利益的理论体系和价值观念,及其在个体和社会其他主体实践中的综合呈现,分析前置价值承诺与实现效果之间的现实对标,帮助观众理解自身的义务、责任,同时也感受到自身个人身份和社会身份被予以了充分的尊重。博物馆对认同的建构要成为观众寻求文化心理归属的可鉴依据,也要为培育对国家和民族忠诚的对象做出贡献。
实践理性层面,要求博物馆深度融入现代生活, 与公众在日常生活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文化环境以及国家治理所建立的制度环境相联。 例如,哥伦比亚麦德林建立了数个博物馆,纪念为反对毒品暴力和恐怖主义而开展的法制斗争,参与社会教育,帮助儿童重返课堂,并为降低青少年犯罪率作出贡献。又如,美国康纳派瑞生活史博物馆(Conner Prairie) 推出针对失智症和阿兹海默症患者的项目,为患者及其看护者创造了一个没有批判的社会环境。在博物馆所传递的信息影响下,提高公众的“自我治理”能力,并进一步影响宏观的文化治理进程,促进整个社会关系向着良好的方向发展。博物馆观众受认知理性的影响,会在社会实践中进行认同的理性选择。 促成理性选择的因由既来自于主体内在信念的养成和支撑,从而构成实践的心理驱动,也来自于主体基于个人的社会生活体验,结合博物馆所传递的价值观,遵循效用最大化逻辑,从而投射到实践的现实行为之中。博物馆在建构认同的实践理性时,是允许在一定的框架内,观众的认同信念结构有所调整或被重新解释的,其目的在于帮助观众“协商”认同信念的含义和情感成分,不断平衡、缓和和解决内在认知和外部环境的矛盾。
综上,博物馆认同建构的基本路径可分为以下阶段。 第一阶段,以实物资料及其所处的语境信息为核心。将实物展品、辅助材料、影像资料等既作为博物馆中支撑认同意识形成的物理资料,也作为信息融合与传播表达中重要的概念性元素,对观众的感官产生直接刺激。第二阶段,围绕实物资料展开信息阐释和内容叙事,凝练认同话语。在此过程中,信息阐释是技术媒介,由此组合形成的叙事是基本视角和逻辑,认同话语是对最终应实现的传播价值进行判断。第三阶段,以提升认同所需的两个心理层面要素———情感和审美为核心。在个人和社会层面,产生认同情感依恋,推动观众由外观型身份认知和确认的“被动型”认同转向内化的“主动型”认同。此外,通过空间、展品的审美处理,博物馆提供了与社会生活深刻意义相关的象征性审美体验。当这种体验能够为个体未来成长创造希望和机会时,审美和认同就成为了“ 一体”。第四阶段,帮助观众回归认同理性。博物馆所能达到的理性自觉既拥有认同的稳定性和持续性等传统特征,同时受现代公共理性观念的影响,个体主体意识更为凸显,因此又显示出动态性和多元性特征,尊重和关照了不同个体或群体所期冀的认同表达。
(本文原刊于《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注释见原文)

【作者简介】
张昱,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博士,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博物馆学和城市文化。出版专著1部。在《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东南文化》等期刊上发表论文40余篇,先后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中央网信办全网推送。主持或参与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十余项。
主编:朱生坚
编辑:张晴柔
运维:任洁
制作:小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