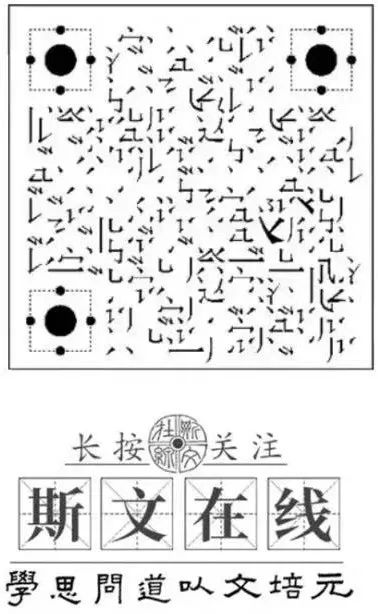2009年9月的数字游戏研究协会(DiGRA)会议(Digital Games Research Association Conference)上,伊恩·博格斯特(Ian Bogost)发表了题为《电子游戏是一团混乱》(Videogames are a Mess)的演讲。这篇演讲以讨论电子游戏的本质为线索,梳理了过去十年间就“电子游戏是一套关于各种规则的系统,还是某种叙事”这一问题,游戏研究者与叙事学研究者们的激烈争论。这场漫长的辩论并非毫无价值,例如Ludology(游戏学)这个名词的提出。但博格斯特认为,游戏学与叙事学在本质上并非对立——二者倚仗的都是形式主义分析方法。他借用哲学家拉图尔(Bruno Latour)的“非还原”(Irreductions)概念来描述电子游戏的非本质性:“(作为整体的电子游戏中)‘没有什么是可被还原的’,即使其中的一些方面被认为(相较于其他方面)令整体产生了质变。”
当时,游戏学家与叙事学家们的理论攻防正逐渐走向温和的尾声,博格斯特的观点也得到了认可。“电子游戏不可被单纯视作叙事载体”与“叙事研究是游戏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共识,研究者们开始更多从“游戏—叙事”关系的层面来思考问题。有些人更是设想了长远的前景,例如克里斯·克劳福德(Chris Crawford)便认为,真正的“交互性故事讲述”的载体——他称之为“交互故事世界”(Interactive Storyworld),不会在电子游戏的发展历程中诞生,而其一旦出现,将取代电子游戏产业。
但电子游戏的本体论,或者说使电子游戏得以成为电子游戏的所谓“游戏性”的幽灵,并未从学术研究实践和日常游玩体验中隐去,其与叙事(以及电子游戏所包含的其他艺术特质)的张力也难以被彻底消解。例如关于“文字冒险游戏是电子游戏还是多媒体小说”的争论背后,暗藏的仍然是游戏与叙事的主客之争。
电子游戏作品毫无疑问可以讲一个或多个好故事。约西亚·勒波维茨(Josiah Lebowitz)在《电子游戏的互动性故事讲述》一书中自述,史克威尔公司于1997年制作发行的《最终幻想Ⅶ》是“改变他一生的游戏”,因为他的两项爱好——游戏与讲故事——在其中相遇。2023年5月初,网名为“KyoStinV”的海外游戏主播在读完《明日方舟》的“孤星”主题故事后,在直播间潸然泪下:“如果满分是10分的话,我会给这个故事打11分,我认真的,这是最棒的故事。”与此同时,找到一款叙事简陋,或者完全不包含叙事要素的电子游戏却并不困难:前者如杰斯帕·朱尔(Jesper Juul)曾提到的《太空侵略者》和《吸血鬼幸存者》;后者如《俄罗斯方块》《合成大西瓜》等益智游戏。
在审美体验层面,一部电子游戏作品具有“格式塔”式的整体性,无法被简单还原为其所具备的各类艺术特质之和。这些艺术特质并非缺一不可,即使是最为基础的视听元素:现今许多商业游戏专门为听觉障碍玩家设置了全字幕选项,也存在专门面向视觉障碍玩家的游戏。当尝试讨论诸如“电子游戏如何进行叙事”或“叙事之于电子游戏的意义”之类问题时,游戏与叙事二者在本体论层面的严重不对等成为难以忽视的障碍,因而有必要为电子游戏这一概念找到思考上的“锚点”,也就是在“一团混乱”之中找到“质变”(Transformative)的因子。
克劳福德在将游戏与电影、图书等其他叙事载体相比较时,指出游戏与它们的差异点在于具有交互性(Interactive)。接受美学等理论认为读者/观众在阅读/观影中也具有主动性和参与性,但克劳福德认为那并不属于交互(Interaction),而是反应(Reaction),二者的区别在于读者/观众无法在审美过程中对具体作品主动施加动作(Act on)并产生影响。在他看来,“交互”是“发生在两个或多个活跃主体(Active Agent)之间的循环过程,各方在此过程中交替地倾听、思考和发言,形成某种形式的对话(conversation)”。具体到电子游戏软件与玩家的交互,考虑到前者是游戏开发者主体性的“幻象”,其在参与交互过程的行为也可以被描述为“输入—处理—输出(呈现)”。
延续克劳福德的思路,仅在针对“游戏—叙事”关系问题的研究中,将“(有规则的)交互”作为游戏概念的“锚点”,无疑可以使思考路径明朗许多。当然,“交互”并非游戏所独有,绝大多数计算机程序都拥有这一特征,而一旦任何程序与通常认知中的叙事行为发生交集,它便有可能进入电子游戏的概念范畴。于是,“电子游戏如何进行叙事”与“叙事之于电子游戏的意义”这两个较为抽象的问题,便能以“电子游戏如何在交互过程中进行叙事”与“叙事对电子游戏交互产生了何种影响”作为起点来展开讨论。对于游戏学而言,后者也许是更具价值的话题。
一
马尔克斯·弗里德里(Markus Friedl)于《在线游戏互动性理论》一书中认为,游玩网络游戏的行为存在三个维度的交互:玩家与计算机;玩家与玩家;玩家与游戏。在当今电子游戏领域,这一理论同样适用。基于对“游戏—叙事”关系这一具体问题的研究实践,本文将弗里德里的观点表述为:在游玩电子游戏的行为中存在三组交互关系——玩家与游戏程序的交互、玩家与玩家的交互以及玩家与游戏设备的交互。
在玩家眼中,单纯发生在自身与游戏程序的交互行为中的叙事是最为直观的,也最接近传统艺术类型的审美体验。在这组交互关系中的“叙事”,其语义与“故事讲述”高度重合。“这款游戏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在日常语境中是大部分人对电子游戏叙事的主要认知。以文字冒险游戏为例,这一类型通常指程序通过文字、影像以及配乐和音效展现游戏场景并进行超文本叙事,玩家在阅读文本的基础上对角色对话或情节分支进行有限选择,达成特定条件后推动故事发展的游戏,例如《Fate/staynight》《428:被封锁的涩谷》等。对这类游戏,故事是否精彩、叙事技巧是否巧妙是评价它们艺术价值的重要标准。前文所提到的争论也由此而生:有观点认为文字冒险游戏不属于电子游戏,因为它们缺少“可玩性”,其在本质上更接近配有插图与声音的超文本小说——换句话说,它们的所谓“游戏性”实际上是“文学性”。
但事实当真如此吗?在2004年版《Fate/staynight》中,触发游戏结束事件的交互节点共有45处,其中5处指向故事的完整结局,另外40处触发的则大多是以玩家所扮演的主人公死亡为标志的“死亡结局”或“坏结局”。如果将《Fate/staynight》视为以叙事为主导的超文本小说,那么45种结局都可被同等视为这部作品的完成。但无论游戏的创作者还是玩家,显然都不会这么认为。除了5个完整结局,其他结局会被视作“游戏中止/失败”(Game Over)。游戏中止时,名为“老虎道场”的场景将出现,创作者在其中会借游戏人物之口告知玩家失败的原因,并推荐重复游玩应选择的存档节点。这正是文字冒险游戏不同于超文本小说之处,玩家不是在选择想要阅读的故事情节,而是根据已知信息与游戏程序进行交互,选择故事情节的走向,避免“Game Over”从而完成游玩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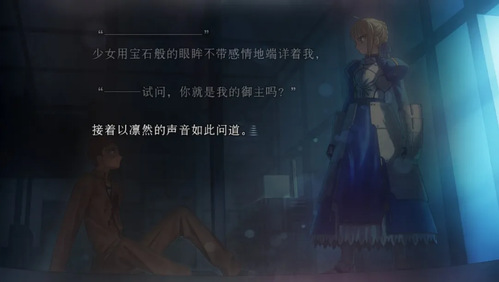
《Fate/staynight》
“可玩性”存在于交互性游玩过程之中。广义的“可玩性”可以是玩家在游玩电子游戏时获得的各方面乐趣,包括视听体验、氛围沉浸、自我挑战、情节阅读等,而本文所讨论的“可玩性”则特指游戏所设置的“接受挑战——选择并实施策略——完成挑战——获得反馈(奖励)”这一套多次循环的交互系统,以及玩家通过这套系统所获得的乐趣。游戏制作人樱井政博在《樱井政博谈游戏创意》(Masahiro Sakurai on Creating Games)系列视频节目中谈到,“可玩性”(他称之为Game Essence)的产生过程,就是游戏对玩家施加压力,玩家选择策略并化解压力的过程。
文字冒险游戏显然拥有完整的可玩性系统,只不过对玩家来说,可选择的策略数量较为有限,在实施策略的过程中,所能够主动参与的部分也仅仅是用操控设备选择文字选项而已。这确实容易令人产生叙事主导着游戏交互的错觉,但实际上,这类游戏与其他可玩性机制更丰富的游戏类型一样,其叙事是通过结构、内容与表达方法的呈现,作为可玩性机制的表征而存在的。“交互”始终是文字冒险游戏的底层逻辑。
若游戏作品将玩家与游戏程序的交互作为单纯的叙事方法,就会使玩家的心流(Flow)产生混乱,影响游玩体验。例如在《使命召唤:高级战争》中,玩家所扮演的角色在一段葬礼相关的剧情流程中,会将手放在战友的棺材上默哀,为了触发这一动作,游戏提示玩家“按F键以致敬(Press F to Pay Respect)”。这段提示文本迅速成为全球互联网上广为流传的模因(Meme)。游戏创作者对这位亡故的战友角色并无令人信服的刻画,只是为了营造深沉哀痛的氛围而强行用交互手段迫使玩家代入主角的心境,这一行为显然带有几分廉价的刻奇(Kitsch)意味。这种设计令玩家感到不快并引来大量嘲讽和批评的原因之一,在于创作者没有把“按F键”这一交互行为合理地置入可玩性系统,使其变成只为推进故事叙述而缺乏自身必要性与内在价值的工具。与之存在类似问题的,还有曾被玩家戏称为“QTE之子”的《崛起:罗马之子》:为了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呈现出符合叙事内容的精美画面,这款游戏充斥着重复的“QTE”,在可玩性层面近乎空壳化。
伊万·斯科尼克(Evan Skolnick)在《扣人心弦:游戏叙事技巧与实践》一书中谈到游戏故事与游戏玩法的一致性时说:
一个附有目标和障碍的挑战摆在玩家面前,玩家想要成功并取得胜利,但游戏附带了必须先克服的复杂度和挑战。没有挑战、目标或障碍的游戏很难被称为游戏,就像没有冲突的故事很难被称为故事一样。
在这个核心层面上,故事和游戏是高度一致的。这两种体验背后的驱动力都是形如“角色想要某物,但又需要克服挑战才能得到”这样的主要冲突。
斯科尼克的这个观点,是站在设计者角度提出的。一部讲故事的游戏作品在立意之初,既可能先有故事创意,从而设计出于与之匹配的可玩性系统;也有可能先确定可玩性系统,再就其选择适宜讲述的故事。以结果论,一部优秀的游戏作品的叙事与可玩性必然是同步的。例如初代《超级马力欧兄弟》的故事:为了拯救被酷霸王绑架的桃子公主,马力欧突破重重困境,距离真正的目的地越近,环境就更险恶,敌人也越密集。游戏难度逐步提升,玩家在“选择并实施策略”环节所需要考虑的信息与实施的难度增加,可玩性也愈发丰富。交互的演进外显了叙事的结构,叙事则为这种变化提供了相对直观的合理性依据。对于大量以英雄母题为核心叙事的游戏来说,“英雄不断战胜更强大的敌人”使“游戏持续对玩家提出挑战”显得与大多数人的直觉相符,“英雄在自我超越的进程中磨炼了智慧与力量”则使“玩家可选择的策略越来越多、操作难度越来越大”合理化。
总体来说,在玩家与游戏程序交互的层面,叙事有大致三种功能。
首先是赋予玩家游玩的动机。当今绝大多数游戏作品在发售前进行宣传时,在大方展示视听技术的同时,往往刻意保留故事的悬念,而因为故事与游戏的一致性,宣传品也同样不会完全揭示最终成品的全部可玩性系统。例如,《黑神话·悟空》在持续4年的公共宣传中,始终不对玩家明示,这部游戏中手持铁棒降妖伏魔的神猴与《西游记》读者们熟知的孙悟空是何关系,也从不详细解释与游戏角色成长相关的具体机制。对于玩家而言,了解一部尚未体验的电子游戏“怎样玩”“是否好玩”与“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是并置同生的游玩动机。
其次,与游玩动机相对应,叙事的情节单元(Plot)可以成为玩家完成游戏挑战后的反馈或奖励。比如在《星际战甲》中,玩家可以自由更换所操作的人形战甲,因而被“我究竟在扮演谁”这个问题所困扰。当完成名为“第二场梦”的系列任务后,玩家在游戏中真正的化身(Avatar)——“Tenno”的身份才得以揭晓,游戏的宏大世界观与背景设定也进一步展开。对玩家来说,谜题的答案就是完成挑战后的奖励之一。又如《最终幻想Ⅹ》中,玩家推进游戏故事发展时的期待之一,就是能观赏到在当时引发轰动的高质量电影化CG(Computer Graphics,计算机图形)动画。在此个案中,情节单元的表现形式与内容都可称是对玩家的奖励。
最后,叙事与视觉、听觉等其他感官要素一样,是整体的游戏交互得以“诗化”的原因之一。在《剑侠情缘外传:月影传说》中,玩家扮演的杨影枫可以获得一件名为“独孤剑”的武器,从可玩性系统层面看,这一道具能够为角色能力带来极大提升,足以使玩家轻松化解游戏提出的一切挑战。“独孤剑”之名,取自《剑侠情缘》系列正传主人公,一位率领武林同道抗金救国的江湖英雄。正是叙事,令“独孤剑”这件本质上是一组程序代码的道具拥有了特殊的含义,它象征的是民族精神之传承与英雄身份的确立。杨影枫拿起“独孤剑”这一简单的“主角获得强力武器”的游戏程序事件,成为玩家心中“史诗回响”般的叙事体验。
电子游戏是年轻的艺术类型,纯粹的可玩性系统当然有其独特的美学价值,但这种价值很难独立地与传统的审美理念通约。电子游戏在发展进程中,正是借助作为表征的叙事、美术、音乐等既存艺术特质使其“可玩性”诗化,才得以渐次进入审美艺术的讨论语境。
二
提到玩家与玩家之间的交互,很多人第一时间会想到网络游戏/多人在线游戏(Online Game),但最近十余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很多被玩家凭直觉划分为单机游戏/单人游戏(Single-PlayerGame)的作品,也会设计基于玩家间交互的叙事内容。例如,在《黑暗之魂3》的“环印城”DLC(Downloadable Content,可下载的后续内容)中,根据故事设定,某个组织会从平行时空召唤强大的援军与玩家角色进行战斗,而其他玩家只要在游戏中装备特定道具,就可以通过互联网“入侵”这名玩家的游戏世界,扮演这名援军,成为对方必须击败的首领敌人。在可玩性系统层面,两名玩家互为挑战者,各自需要进行游戏策略的选择与实施,达成挑战的胜者可以获得奖励。另一个例子是,在《龙之信条》中,玩家可以自行设计、培养NPC(None-Player Character,非玩家角色)“侍从”并通过网络上传至游戏服务器,“侍从”会被其他玩家雇佣,为他们的游玩提供协助并赚取报酬。被雇佣的“侍从”会根据其在培养者的游戏世界中的经历,为雇主玩家提供攻略建议,例如敌人的弱点、场所的方位等等。这同样是十分精妙的设计:在雇佣“侍从”这一交互行为中,雇主玩家的策略选择与培养者玩家的策略选择高度相关,这使得可玩性系统的深度与趣味性大大提高,也完善了游戏的世界观设定。

《黑暗之魂3》
讨论这一类游戏作品的“游戏—叙事”关系,可以参考玩家与游戏程序交互层面的思路与分析框架。我们可以理解为,它们是在玩家A与游戏程序的交互过程中,将原本应由程序所承担的功能和职责,通过互联网接入了玩家B与同款游戏程序的交互过程,使其成为游戏对玩家B所提出的挑战。也即是说,对玩家A而言,若切断网络,由游戏程序虚拟一位“玩家B”完成交互,游戏的可玩性系统与叙事功能仍然是完整的。《黑暗之魂3》与《龙之信条》确实也对离线玩家提供了这种完成游戏的方式,前者的做法是由一名预设的NPC担任援军与玩家战斗,后者则是令系统随机生成“侍从”供玩家雇佣,故事还是可以讲述下去。
在真正的多人在线游戏,也就是可玩性系统建立在玩家间交互的基础之上的游戏中,情况则有所不同。我们固然可以沿循前文的思路,想象性地建构一个“自闭”的玩家,他完全不与其他玩家进行交流互动,将多人在线游戏视为单人游戏进行游玩,如此一来,其他玩家在他眼中与NPC并无差别。但电子游戏作为交互艺术,单一地从接受角度提出假想是难以立足的。弗里德里认为:
玩家与玩家互动性定义了非常自然的多人在线游戏。正是它使设计师的宝贵的玩家感觉到这些游戏不同于他们玩过的其他游戏,并且可能是他们购买这些游戏的原因。如果互动性是计算机游戏的全部,那么对于在线游戏及玩家之间的人与人互动而言也是如此。
设想中的“自闭”玩家也许能够“进行”多人在线游戏,但那就像《超级马力欧兄弟》玩家放弃跳跃而笔直冲向危险一样,无法被称为“游玩”,因为他并不是可玩性系统的真正参与者。
多人在线游戏在玩家与程序交互层面的叙事,即游戏预先设计的故事情节,与单人游戏的叙事呈现出相似的特点。区别在于,玩家间的交互深深嵌入了可玩性系统之中。一名玩家要完成游戏给出的挑战,体验故事,就至少需要在策略的选择与实施环节与其他玩家发生交互,包括沟通、交易、合作与竞争等不同形式。除此之外,这类游戏中还存在着另外一种故事,即玩家在多人交互的社会性活动中自身经历的故事。多人在线游戏中的玩家间交互可能会令玩家体验诸如加入公会、遭遇挫折、交友和恋爱等各类事件,其中能带给玩家正面情绪的事件,如弗里德里所说,很可能就是他们游玩这类游戏的期待之一。游戏设计者可以部分预料到这些事件的发生,却不可能对它们一一进行叙事设计。关萍萍援引利奥塔对后现代时期“大叙事”向“小叙事”转变的观点,提出“每一个在游戏虚拟世界中的玩家都成为了一个‘中心’——都成为信息传播者和媒介叙事者。传统大众媒介的宏大叙事变成了玩家个体的小叙事”。玩家在多人在线游戏中的个体经历,显然是她所说的“小叙事”的代表之一。
玩家在多人交互中的个体叙事超越了游戏程序玩家交互的层面,无法在狭义的可玩性系统内进行分析。但构成这种叙事的母题(Motif)却可以被多人在线游戏的可玩性系统所整合为题材(Subject Matter),以情节单元的形式展现出来。在《剑侠情缘网络版叁》和《最终幻想14:重生之境》等网络游戏中,两名玩家的角色之间可以举行“婚礼”,而这场“婚礼”往往作为完成某些挑战后的奖励给与玩家。游戏的交互机制既是玩家个体叙事的语境,也是符号。
当然,在承担叙事语境与叙事符号的功能方面,交互机制并不总是如游戏设计者预想般有效,例如在多人射击游戏《反恐精英》中,玩家控制角色下蹲,与在物体表面喷绘图案,都是游戏内的常用操作,本身并无额外的含义。但玩家在游玩过程中击杀对手后,若在“尸体”处反复下蹲(这被称为“Teabag”,浸茶包)或喷图,则被普遍视为对对手的嘲弄与侮辱。又如在卡牌对战游戏《炉石传说:魔兽英雄传》中,对战的两位玩家可以通过角色发出的6种预设语音来进行简单沟通,表达“问候”“抱歉”“称赞”“威胁”等态度。不过,在玩家进行游戏时,如果在即将赢得胜利时选择“抱歉”,在对手看来,释放的信号却是鲜明的反讽和蔑视。
多名玩家参与在线游戏时,主体之间习惯性的交互行为会变成“在他人期待下的、相互间特定的行为”,从而形成朴素的“共同体行动”。游戏程序无法真正约束或支配这种共同体行动,而承担符号功能的可玩性机制,也会因“能指的漂移”而被不断地赋予新意义。玩家与玩家之间在交互中形成的个体叙事,不是依附于游戏可玩性系统的诗学的叙事,而是深入玩家日常生活的、历史的叙事。
历史学家戴维·卡尔(David Carr)认为人类日常活动与经验本身就带有叙事性:
我们想要表达的是,无论效果如何,我们一直努力试图在我们的行为上占据故事讲述者的位置。不要觉得这只是一个牵强的比喻,想想在反思和审议过程中,向他人和自己讲述我们正在做的事情,这一行为有多重要。当被问及“你在做什么?”时,我们可能会被要求讲出一个具有开头、过程和结尾的故事,这种叙述或复述既是描述,同时也是一种申辩。
一些网络游戏往往会用“玩家可以书写自己的故事”来进行宣传,但其实,玩家自己的故事是“自在”的,它们只是被游戏外化了叙事结构,从而变得可被清晰地感知:玩家可以通过游戏将另一位玩家加入通讯录或标记为“好友”,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二人就此“认识”或“产生友谊”,但抽象的人际关系确实被交互机制具象化了。可玩性系统在运行过程中不断生成符号性的象征物——比如前文所提到的“婚礼”——从而使隐藏于日常生活中的、蛰伏在人类精神深处的叙事题材被有机地组合了起来。
三
对玩家的个体叙事的思考,为“游戏—叙事”关系带来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假设人类活动本就具有叙事性,那么“玩家游玩电子游戏”作为包含人类主体性参与的行为事件,是否也可以被认为是某种叙事?如此一来,任何电子游戏,包括不存在叙事意图的《Pong》和《Breakout》等作品,好像都具有叙事性质,或成为某种叙事构成中不可缺少的要素。游戏学与叙事学的辩论似乎战火重燃。不过我们同样能以看待游戏的眼光,把人类生活描述为“选择并实施策略从而完成挑战以获得反馈”的过程,其不可预知性源于我们尚未发现“交互”的规则。“白马非马”式的逻辑游戏并不会对“游戏—叙事”研究带来多少实际帮助。
真正值得探究的,是当日常生活,或者说现实世界进入“游戏—叙事”关系的讨论范畴,身体意义上的“玩游戏”,即玩家与游戏设备的交互行为,是否有承载叙事的空间与潜力?
就用语习惯而论,“玩电脑”“玩电子游戏机”等描述人类操作游戏设备的词组,基本都指向“玩电子游戏”这一行为。但电子游戏却常被视为精神娱乐——最严厉的批评,是称之为“精神鸦片”或“精神海洛因”。描述身体行为的“能指”联系着的“所指”是精神活动,这符合索绪尔主义中语言形式与概念实质二分的观点,但在多数人看来似乎有些违反直觉。倘使承认这种“常规智慧”(Conventional Wisdom)存在某种内在逻辑,那么我们可以粗浅地推衍出如下假说:玩家与游戏设备的行为关系,是游玩电子游戏不可或缺且具有代表性的要素。
关于这一假说是否会在未来的电子游戏发展中被证伪,暂且存而不论。它的提出,至少意味着“玩家游玩电子游戏”这一组二元关系行为,可被拓展成为“玩家通过游戏设备游玩电子游戏”的三元关系行为。一方面,游戏设备本身并非克劳福德所说的活跃主体,无法与玩家进行真正意义上的交互;另一方面,在玩家与游戏程序的交互过程中,前者需要通过设备进行言说/输入,后者同样需要设备进行倾听/输出,游戏设备的缺席将使交互行为无法完成。玩家、游戏设备和游戏程序三者在“电子游戏的交互性游玩”语境中相依共存。只在此特定条件下,玩家与游戏设备存在交互的论断才得以成立。
杰斯帕·朱尔在2001年时提出过一个著名观点:“在‘互动故事’游戏中,使用者观看视频剪辑或做出决定时,故事时间、叙事时间和阅读/观看时间是分别进行的,但是一旦使用者开始施行活动,这些时间就开始内爆:已经发生的事件是无法改变的,这意味着‘你不能同时互动和叙事’。”考虑到此文发表前后“游戏学与叙事学之争”的学术语境,这个建立在“游戏—叙事”二元对立预设之上的观点,其意图很可能是学科与范式之争,带有“矫枉必须过正”的策略性考量。朱尔从时间角度思考交互与叙事是具有启发性的。他以《DoomⅡ》举例,认为叙事有双重时间序列——“过去发生的故事”和“正在发生的叙述”,与此相对,玩家与游戏的交互事件则永远处于“正在发生”的瞬间,这是“时间内爆”理论的前提。随着电子游戏技术的进步和人们对交互概念的更深入思索,这一前提的可信度摇摇欲坠。
玩家与游戏设备的交互确实是瞬间发生的,但玩家借之与游戏发生交互的过程,却明显具有时间跨度。在《赛博朋克2077》的一组名为“拿货”的任务中,玩家可以选择是否与一名NPC“斯托特”合作,游戏会由此走向不同分支。如果玩家选择合作并输入相应指令,那么在此任务组结束的数天(游戏故事时间)后,与“斯托特”合作的额外任务“穿皮草的维纳斯”会加入玩家的游玩目标,玩家可以通过完成它获得奖励。记“玩家与斯托特合作”为A,“玩家通过操作游戏设备达成A”为a,“‘拿货’任务组与‘穿皮草的维纳斯’任务”为A´,可以看出a∈A且A A´。通过分析能够得出如下结论:玩家与游戏的交互未必是单一或孤立的,而可能是由一系列跨越维度的、机制规模和时间规模大小不一的交互行为环环相套所形成的交互组。因此,“玩家—游戏设备”和“玩家—游戏程序”这两组交互关系的进程,在时间上并非总是同步的。
由此出发,对是否存在围绕玩家与游戏设备互动的叙事这个问题,答案是肯定的。这可以通过对“自指游戏”的互动性叙事的分析加以证明。“自指游戏”是将“玩家游玩本游戏”的行为视为游戏事件并纳入可玩性系统设计的电子游戏,通常被认为属于“元游戏”(Meta Game)的一种。在“自指游戏”中,游戏的可玩性系统的构成要素之一是其自身,也就是说,“玩家通过设备与游戏程序交互”是“玩家与游戏程序交互”的组成部分。
最知名的“自指游戏”是《史丹利的寓言》。看上去,玩家是以“史丹利”作为自己的化身进行游戏,“旁白”的声音会描述并引导“史丹利”的行为,试图完成对游戏故事的讲述。但玩家可以控制“史丹利”拒绝遵循“旁白”的引导,从而使游戏进程通向不同的分支和结局。这部作品放弃了对所谓沉浸感的追求,不断试图“打破第四面墙”,阻断玩家与其化身的心理投射,从而令他们意识到自己正在玩游戏。玩家可以通过游戏设备控制“史丹利”的行为,但玩家不是、也不扮演“史丹利”。如果在游玩过程中的某一时刻,玩家不进行任何操作,旁白会描述“史丹利”呆立不动的行为,并称赞这是“天才正在工作”。游戏对选择并实施“不选择或实施任何策略”这一策略的玩家给出了反馈,这正是“自指游戏”的可玩性系统设计的精妙之处。一个更极端的例子是,在这个游戏中玩家可以尝试完成一项名为“出去走走”(GoOutside)的挑战,条件是“5年不玩《史丹利的寓言》”。玩家通过不游玩游戏的方式游玩游戏,这看似是“罗素悖论”式的逻辑困境,实则不然:玩家是以“不操作游戏设备”为策略,参与了游戏的可玩性交互。“不玩《史丹利的寓言》”这一表述可以被转译为“不运行《史丹利的寓言》的游戏程序”。可以说,游戏构造了两种叙事,一种围绕游戏内角色“史丹利”与“旁白”进行,一种则是建立在“玩家与设备和游戏交互具有时间差”这一基础上的,以玩家与游戏设备间的交互为中心。

《史丹利的寓言》
另一款发布于个人电脑平台的“自指游戏”《一次机会》有着相似的创作逻辑。玩家扮演自身,引导(操作)主人公尼克(Niko)拯救自己和世界,他们的敌人则是时不时会自我关闭的游戏程序。游戏会在电脑系统里生成特殊文件,玩家需要找到这些文件并从中获取解决谜题所需的信息。可以说,玩家在游玩这款游戏时所获得的最精彩的叙事体验,发生在他们与游戏设备而非游戏程序的交互过程中。
游戏设备不仅将玩家与游戏相连接,也把游戏所书写的虚构故事——即诗学的叙事,与玩家在进行“游玩游戏”这一主体性行为所体验到的个体的、历史的叙事,巧妙地融合了起来。由此,“交互”与“反应”的差异得到了更鲜明的体现。
结语
如阿尔瑟斯(Espen Aarseth)所说,“游戏—叙事”的关系是复杂且形式多样的,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思路有着超越结构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丰富可能性。“叙事为游戏交互带来了什么”和“游戏的交互性机制如何讲述故事、生产叙事”应等量齐观。存在于三个维度的交互关系中的叙事要素并非割裂、各自独立的,而是紧密结合、互相影响的,就玩家的体验而言,游戏叙事是可被直观感知的整体。叙事的力量,在不同层面赋予了交互性游玩特殊的意义,使其超越了单纯愉悦感官的行为。
严锋曾谈到:“我是一个热爱文学并因此以文学为职业的中文系教师,但这辈子最难忘的艺术感受却是在游戏中得到的。”对人类来说,玩电子游戏与读书、看电影、听音乐一样,不只是追求快感的娱乐活动,同时也是体认世界、确立自我的心理仪式。我们借此对抗现实生存环境带来的异化,避免成为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人”。

【作者简介】
李汇川,文学博士,曾就读于南开大学和北京大学。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青少年社科研究工作室首席专家,数字游戏文化研究中心负责人。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跨文化形象研究和电子游戏文化研究。
【新刊目录】
《上海文化》(文化研究版)
2024年第10期
专 题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上海实践
蒲 妍 赵正桥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理论主张、基本议题与实践进路
邓又溪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上海城市文化实践
访 谈
严 锋 金方廷 技术时代的文学、艺术与教育
理 论
朱 虹 袁 佳 媒介批评视角下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的流变与审思
文 学
叶奕杉 “跨越”何以养成新风格——论“新南方写作”的物我伦理表达兼及文学文化的跨界融合
纪水苗 “新南方写作”:文学事件的发生与文学策略的选择
杨 莹 方言实验与地方想象的空间建构——以“新南方写作”为中心
文 化
刘 欣 重绘游戏思想史谱系:游戏思想史视野下电子游戏本体论的断裂与重构
李汇川 电子游戏的三重交互关系与叙事
严奕洁 黄锐杰 生命之“涌现”——《塞尔达传说:旷野之息》与游戏现实主义的第三条道路
文 艺
魏 玲 模拟、象征与差异——新世纪乡土电影中城市形象的空间构形
卢巍文 中国新黑色电影的现实主义审美表征研究
书 评
徐同欣 《拉斯科,或艺术的诞生》:巴塔耶的起源话语
编后记
英文目录
封二 周卫平《古镇边道》
封三 好书经眼录
《上海文化》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扩展版)来源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引文数据库来源刊
社长:徐锦江
常务副社长:孙甘露
主编:吴亮
执行主编:王光东
副主编:杨斌华、张定浩
编辑部主任:朱生坚
编辑:木叶、黄德海、 贾艳艳、王韧、金方廷、孙页
《上海文化》(文化研究版)
主办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地址:上海市中山西路1610号2号楼928室
邮编:200235
电话:021-64280382
电子邮箱:shwh@sass.org.cn
邮发代号:4-888
出版日期:双月20日
主编:朱生坚
编辑:张晴柔
运维:任洁
制作:小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