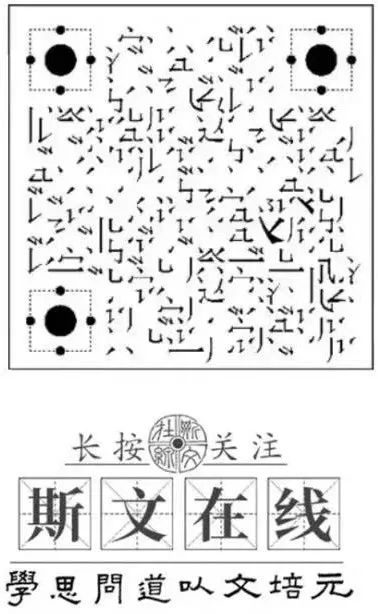20世纪70年代,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石上,创新性地阐述了“空间生产”理论,引领了学术界的“空间转向”,该理论核心在于,用广泛的空间及其生成机制来揭露空间形成的本质,体现出一种跨越社会关系、物质生产及非物质生产的全方位视角。而后,列斐伏尔的“三元空间辩证法”(空间实践、空间表象、表征性空间)为理解这一动态过程提供了框架,强调空间是社会动态交互的结果。电影作为一种文化与艺术表现形式,其空间构形同样蕴含了“三元辩证”逻辑。然而,电影并不等同于现实,它只是现实的摹本,是光学影像对物理世界的二度生产。基于此,电影空间生产的“三元辩证”与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的“三元辩证”既渐近又有所区别。在新世纪乡土电影中,城市的空间构形大致归纳为模拟空间、象征空间与差异空间。模拟空间是基于影像空间与现实空间关系的宏观划分;象征空间是从影像的意义层面来解剖电影与现实的微观联结;差异空间则是在包纳前两者的意义之上,所形成的一种更为开放的空间表达。
一、模拟空间:物质影像的二度生产
在文化学视域中,模拟与模仿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模仿更接近一种对被模仿者的忠实复制,“而‘模拟’的目的在于产生出某种与原体相似与不似之间的‘他者’”。 所谓“他者”,在电影模拟空间中,指影像通过光学机制对物理世界进行的二度创作。它主要包含三种形态:日常化、想象化与景观化。日常化空间遵循“实”的创作原则,着重于展现电影对客观现实的忠实模拟;想象化和景观化空间遵循“虚”的美学向度,即通过调度现实空间中的物体,将各种元素进行零散式的堆叠与组合,从而形成一种具有特定意义的符号景观。在新世纪乡土电影的模拟空间中,城市形象的二度生产既有秉承克拉考尔“物质现实复原”的镜式空间,也有醉心于景观堆叠与蒙太奇组接的后现代“超真实”空间。

(一) 镜式空间:物质现实的复原
镜式空间是物质空间的影像复原,也即列斐伏尔物质空间的镜像表达。列斐伏尔认为,“物质空间”的经验感知性可以通过不同的物质区域来区辨,这一观点与美国城市规划学者凯文·林奇在《城市意象》一书中提出的“可意象性”概念异曲同工。“可意象性”,即近似于列斐伏尔的“可感知性”,指那些在有形物体中能够激发大多数观者强烈意象的特征,如形状、颜色或布局等。这些特征不仅有助于塑造个性化的环境意象,还赋予空间“可读性”。在该书中,林奇通过缜密的实证分析,阐明了美国典型都市中心区在个体心理地图上的五大构成要素:道路、节点、区域、边界与地标。这些元素及其背后的城市意象,构成了他城市认知理论的核心基石。
1. 道路与节点的城市意象
“节点与道路的概念相互关联,因为典型的连接就是指道路的汇聚和行程中的事件。” 其中,道路是城市意象中的主导元素。如果将城市中的各个元素视为语法轨道中单个语词的话,那道路就是句法结构的守护者,它表征着城市的语言逻辑与空间秩序。同本雅明将“漫游”街道作为感知城市空间的方式一样,乡土羁旅人得以窥探城市奥秘的首选也是道路。“节点是观察者可以进入的战略性焦点,典型的如道路连接点或某些特征的集中点。” 道路和节点在空间影像的叙述中密不可分,二者协同营构了一种连续性的活动空间,构成银幕中城市意象的秩序表征。在新世纪乡土电影中,以道路、节点为主元素的乡土电影主要有以下两种主题:
一是展现城市繁华、拥挤、等级森严的特性。譬如,夏雨主演的《电影往事》讲述了热爱电影的乡下青年毛大兵在城市中与电影的不解之缘。影片中,城市各个阶层的句法排列就是通过毛大兵与道路的触摸而跃然入画的:富人的高楼、穷人的陋巷以及边缘群体的灰色地带……一景一幕,一砖一瓦都在道路的牵引下一览无余。此外,以道路来揭秘城市意象的乡土电影还有《应承》《平原上的夏洛克》《Hello!树先生》等。

《Hello!树先生》
二是借助主人公的位移,将城市道路的拥堵、喧嚣与乡土道路的静谧、空旷并置对比,以期展露城乡文化的差异性。在《美丽的大脚》中,自由广袤的荒原土路和车水马龙的北京水泥路、简陋温暖的乡间学校和现代冷漠的城市商场两相对比,就凸显出城市空间巍峨冷漠与乡土空间温情脉脉的差异基调。这种城乡空间的差异基调在王全安的电影《惊蛰》中尤为明显。乡土空间中,关二妹的活动范围被困在以家之名建造的监狱中:主屋—猪圈—庄稼地,这是乡土社会特有的“超稳定”空间。伴随着关二妹对乡土的“越狱”,街道的面孔解开了她对城市的神秘想象:暧昧、时尚且充盈着物欲。在二妹和毛女的小城视野中,小城空间中的“鱼馆”和“梦巴黎”就是节点,它们预示着女性在城市生存的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然而,影片并未在城乡两种空间胜利与否上给予非此即彼的评判,毛女的“城”与二妹的“乡”都不是女性逐梦自由的“理想国”。
与之相对,还有一种城乡路径的并置,虽未直接点明两种空间的优劣,但通过人物位移前后的状态变更隐喻出城市空间与乡土空间的权力对弈。电影《一个勺子》中,主人公从拉条子到勺子的转变就是在城乡空间的位移以及追与被追的行动中完成的。第一次“追”的对象序列是勺子——拉条子,追逐方式是主体传统位移速度的较量(跑)。第二次“追”的对象序列是拉条子—大头哥,追逐方式是传统与现代位移速度的较量(人/车)。首尾相合,两次追逐的路径皆由城至乡,小城中心的歌舞广场与荒原的空地分别成为两个空间追逐路径的节点(也是叙事节奏的节点)。通过城—乡追逐路径的一览无余,传统与现代两种话语争夺的成败在主人公失序的精神状态中有了具体的喻指。
2. 区域与边界的城市意象
“边界是除道路以外的线性要素,它们通常是两个地区的边界,相互起侧面的参照作用。” 在城市中,有些边界的划分不仅在视觉上表征着绝对的话语权,也在形式上连续且不容僭越。当然,这仅指称那些强大的边界,诸如上海的黄浦江和波士顿的查尔斯河。在新世纪乡土电影中,城市内部的边界则弱得多,因为它不涉及国家领土意识层面,仅指涉文化、地理、身份、地位的区隔。区域则是在边界的划分下形成的板块状空间成分,其范围要广于节点及标志物,个体对它的识别是由内而外的,需要一定的经验累积。
在新世纪乡土电影中,城市边界和区域的划分是在城乡对立的视域下展开的,有着特殊的影像意味,如城市游民聚居地、工厂、富人区等。以电影《矮婆》为例,矮婆在进城后,其对城市的所见所闻都框定在工厂这个坐标轴中,连沿途的风景也都是一栋栋标准化的工业塔楼。在电影《矮婆》中,那一栋栋的塔楼就是城市空间用以隔离务工乡民身份自由的区域。工厂区域的意象呼应了刻板而僵硬的福特主义,揭露了城市工业的冷漠。
3. 标志物的城市意象
地标是一种点状参照物,通常被定义为一个有形的物体,被用作确定身份或结构的线索,如建筑物、标志、店铺或山峦。 地标是一座城市精神气质的可视化符号,可以作为城市特殊意义上的恒定标识。在新世纪乡土电影的语境下,城市地标类的意象呈现出更为错综复杂的特质,可以从多元化的视角对其进行深入剖析。以凯文·林奇的城市意象理论为框架,电影中所展现的城市意象可细分为两个层面:“在场”与“缺席的在场”。
“在场”这一概念相对直观,指的是通过影像和声音直接呈现给观众的城市地标。以电影《额吉》为例,上海外滩就是一个典型的城市地标。这一地标与主人公的命运紧密相连,既反映了主人公作为上海孤儿被亲生父母遗弃的“历史”,也体现了现阶段他被城乡至亲(血缘父母与养母额吉)双重需要的“当下”。
“缺席的在场”比较特殊,指的是具有城市标志性的建筑物在影像中出现了,但又不是以实景的形式出现。在宁浩导演的影片《绿草地》的启幕阶段,首先进入观众视线的是一个极具北京地标的建筑场景——天安门广场。然而,随着镜头推拉,观众发现“此物非彼物”,镜头所展现的并非真实的天安门广场,而是一幅“画中画”。与此类似,万玛才旦的电影《塔洛》中,不仅展现了“北京天安门广场”,还呈现了“美国纽约时代广场”。这些看似真实的城市地标,实际上只是机械复制下的“画中画”。从影像实景的角度细究,它们并非真实的城市地标。然而,若就克拉考尔物质现实复原的角度来审视,便不能对其“真实性”进行武断。
“电影不仅帮助我们理解我们特定的物质环境,并且向各个方面扩展它。电影实际上把整个世界变成了我们的家园。” 克拉考尔的话表明,电影的照相本性能够拓展我们理解世界的空间。即便是实景拍摄的空间画面,其本质上也只是对现实空间的二度生产。如此,上述电影中被照相术索引的城市地标,便可被视为一种“缺席的在场”式地标。综上,模拟影像中被二度生产的复制品艺术(城市意象的景观复制)也是表达城乡语境中乡民对城市认同与否的一种幽微切口,属于“缺席的在场”。
(二)超真实空间:虚空中的奇观魅影
20世纪40年代,巴赞提出“完整电影”的神话,表明对电影模拟空间无限趋近现实空间的一种期许。21世纪以降,伴随着数字影像的普及,巴赞所构想的“完整电影”神话在技术叠置的浪潮中加速“失重”,从而落入“超真实拟像”的虚空幻影中。“超真实”(hyperreality)的概念由让·鲍德里亚提出,用以描述一种比真实还要真实的状态。
在新世纪乡土电影的模拟空间中,城市“超真实”空间的建构主要体现为城市话语的抽象植入及城市实景的具象缺席,两者协同营构出乡土影像中的“超真实”神话。值得注意的是,“超真实”空间在乡土影像中的呈现会依据导演城乡情感及影片类型(商业/艺术)的差异而展露出两种模态。
一是以城市话语的隐形嵌入为核心路径,其叙事场域虽在乡土,但内核却迎合城市受众的认知习惯与审美预期。在这类乡土电影中,地域性的乡土概念只是一个空洞的能指符号,其真正所指的空间则关涉某种“伪饰”“化装”后的城市衍生体。由此,银幕内的乡土空间便呈现出一种似城似乡、非城非乡的奇观状态。以电影《自娱自乐》和《决战刹马镇》为分析文本,可以观察到,城市与乡土的空间界限交错戏谑,反映出电影的商业导向与城市定位。在此类影像叙事中,“超真实”空间的建构同时指涉城市与乡土,即外表乡土,实质揭示城市内核。“社会空间相互渗透和相互叠加的原则有一个很有效的结果,因为这意味着服从于分析的空间的碎片掩盖的不只是一种社会关系,而是一群社会关系,即分析能够揭示出来的那些关系。” 其结果是,城乡之间的壁垒似乎在“影像童话”的干预下摇摇欲坠,实则却是在“影像造梦”的机制运作下,美饰了城市空间植入乡土空间的权力风景。二是城市实体虽依旧保持“不在场”的姿态,话语表述上也偏向城市,但叙事内核却聚焦于乡土主体。这类影片中,城市“超真实”空间的建构更多源于乡土主人公对城市空间的向往与想象。以管虎执导的电影《西施眼》为例,“上海”作为串联三个故事的主要意象,从未以实体影像的形式出现在影片中,但“想象上海”始终作为主人公走向最高行动的驱动力弥散于影片的各个角落。在这部电影中,上海之于三个女主人公,不啻好莱坞电影之于其受众,都在以奇观咒语的方式使“信徒们”产生一种近似迷狂般的向往,并使其沉浸于被约翰·麦克道威尔称作“在虚空中进行的没有摩擦的旋转”的状态。 如果城市影像是机械(物)对现实空间的二度生产,那么想象就是主体(人)对现实空间的二度生产。毕竟,人脑知觉系统对信息的筛选组织与蒙太奇的剪辑原理在某种程度上如出一辙。

《西施眼》
“摄影机构造并规定这个世界中的客体。因此,观者与其说是与再现之物(即景观本身)认同,不如说是与安排景观使其可见的那个东西认同,正是那个东西迫使观者看到它所看到的东西。”让-路易·博里达的话表明,不是乡民的想象替代了摄影机建构了上海意象,而是电影、电视的盛行使得上海意象得以越过人眼直接被赋予了期待视野。“上海”的“超真实”建构,之所以能够在阿兮的心中种下理想乌托邦的种子,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照相术”对被摄物体“超真实”性的片面呈现。
城市通过乡土电影猎奇乡土空间,乡民也通过影像建构城市空间,而格式塔心理学又为观影者的知觉系统予以了相应的心理补偿。于是,上海的空间意象就在少女阿兮的知觉系统中被真实地建构了,这是一种剔除了一切“不真实”的“超真实”空间。在这场“超真实”的空间漫游中,“开麦拉”的确是一支笔,导演是建构城市“超真实”空间的主建造师,而乡民对于城市而言,却是生活在别处的“孩童”。
二、象征空间:晶体影像的物性出位
象征空间即指借助具体的物或物之间的陈列来隐喻某种抽象意义,将无形的意蕴赋意到有形的事物当中,从而营造出“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想象空间。在新世纪乡土电影的象征空间中,观众与角色往往会处于一种“做梦中梦,见身外身”的恍惚境地。至于象征,其概念本身也具有多重意义指向。在中国文论中,象征由意象和意义两部分构成,前者指称“物”的表和显,近似于西方文论中的概念符号化;后者指称物表象之下的里和隐,即西方文论中隐喻与潜在的意义运作。“寓意把现象转换成概念,把概念转换成意象,并使概念仍然包含在意象之中,而我们可以在意象中完全掌握、拥有和表达它。象征体系则把现象变成理念,再把理念变成意象,以致理念在意象中总是十分活跃并难以企及,尽管用所有的语言来表达,它仍是无法言传的。”基于中国文论对象征概念的阐发,本文将乡土电影中城市形象的象征空间分为符号隐喻与潜在象征两个维度。前者侧重于单个“物”对于空间的意义生产;后者则强调物与物间潜在的关系运作对空间的象征意义。
(一)生吞活剥:城乡空间的意义生产与符号隐喻
时间与空间,作为特殊空间生产的两大要素,是彼此依存、不可分割的。电影的空间生产亦是如此。况且,“第七艺术”能指的由来,首先就是基于对莱辛式“空间艺术”和“时间艺术”二分的破维。因此,对影像中空间性的研究必然离不开对时间性的追问。欧文·潘洛夫斯基(Erwin Panofsky)将电影的特性界定为“空间的动态化及随之而来的时间的空间化”,这与德勒兹的运动—影像、时间—影像存在部分切面的耦合。而“时间的空间化”在以城乡关系为落脚点的电影中似乎找到了最恰如其分的切口,毕竟时间范畴中的传统/现代二元进步观念在影像中往往都被纳入乡村/城市二元对立的空间化范畴。因此,在新世纪乡土电影中,城乡异质空间、同质符号的并置对比,便衍生出多种象征意蕴。
在电影《暴裂无声》中,城市空间的画面出现了一组隐喻符号,即资本家—昌万年、劳动对象—羊肉、劳动者—服务员、劳动资料—切割机、资本累积—贵价红酒。在这组以陈列物为背景的空间中,资本主义生产的全过程被赤裸地呈现,“人”与“羊”之间仅仅是猎食者与猎物、资本家与劳动对象的关系。紧接着画面一转,切换到了乡土空间中的人与羊,此时昌万年的“盘中餐”(羊)也以生命的形式得到了张保民夫妇的关怀。这种画面对比的核心要点不在于羊与羊肉,而是幼羊与劳动对象、饱腹与奢靡、尊重与践踏、城市与乡土。在电影《暴裂无声》中,城乡两组空间中“物”的并置对比,所衬托出的不仅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实隐喻,更指涉了资本空间对乡土空间的盘剥与统治。

(二)故土难觅:回忆空间的互文性生产与晶体想象
回忆—影像在德勒兹的影像学中,既位于晶体影像坐标轴的前位,又与纯粹的晶体影像密不可分,其影像的理论模型源于伯格森的倒锥平面图——倒锥垂直于平面,锥体表征记忆时态,平面显示现在时态,时态交汇处便是晶体。晶体,即意味着过去—现在—未来时态的不可区辨。“倘若我们把时间解释为一种媒介并在其中区别东西和计算东西,则时间不是旁的而只是空间而已。” 尽管柏格森说这段话的本意是想将时间脱离出运动规范,以剥离和空间的合体。然而,仅就电影而言,两者是很难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
本文这里所探讨的回忆空间既包括主体回忆—影像呈现的情感体验空间(原乡),也包括触发回忆影像的物质实在空间(城市),两种回忆空间在纯粹时间流的包裹中促成实际影像(城市)与潜在影像(原乡)的双面嵌合。基于回忆空间与晶体影像的时间性特质,单个文本的罗列式分析很难将乡民当下的现实空间体验(城市)与过去的回忆空间想象(乡土)放在纵向的历史维度上去考察。因此,本部分的研究将采用文本互文的方式,将表征过去—现在—未来的乡土电影放在时间延展的维度上综合分析,并进而总结出叠合空间(现实空间+回忆空间)的晶体属性。
以电影《老兽》为引,片中主人公真实的空间位置在城市,回忆空间的闪回出现在其与情人巫山云雨后。现实空间中,主人公刚经历过贩卖骆驼、身无分文、与情人云雨时“力比多”功能的退化,这既隐喻着主人公生理层面“廉颇老矣”的现状,也暗示着他与草原精神的渐行渐远。随后,在玻璃碎片的虚晃与光晕的簇拥下,主人公在半睡半醒的眩晕状态中借由光斑开启的“隧道”,穿越到了回忆空间中。至此,玻璃碎片作为晶体的界面,通过闪回这一“吸引力”手段,将草原意象从主人公的知觉系统中抽象提纯为现实空间中那一缕额前的五色光,这缕光就是主人公对原乡意识的结晶。在闪回镜头建构的回忆空间中,高洁凛冽的白马、虚化模糊的骆驼、生了病的童年自己以及影影绰绰的草原意象等都被覆上了一层如梦似幻的气质。

《老兽》
玻璃碎片与五色光都是城市空间中用以象征、过渡回忆空间的真实景观,当主人公回忆中的虚拟幻象与其叠合时,便构成了德勒兹借柏格森理论所论及的圆锥体顶点S点。S点的能指就是现实—虚拟的晶体影像,它既包蕴了回忆空间中的过去—梦幻影像,也涵括了勾连回忆空间的现实影像(城市)。在此,艺术性的回忆空间成为建立主人公“老兽”自我和集体身份认同的重要组成元素,在冲突与认同之间产生张力并提供表现场所。“回忆的进行从根本上来说是重构性的;它总是从当下出发,这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被回忆起的东西在它被召唤的那一刻会发生位移、变形、扭曲、重新评价和更新。” 在“老兽”的记忆空间里,“草原意象”一直都在位移:清晰—模糊—遗忘—唤起。直到S点的到达,晶体的催化才使得他回忆空间中储存的“内在力量”得以觉醒。这种内在力量是想象力、理性与记忆力的三位合一,其唤醒机制源于牧民血液中对家园意识的询唤。
李睿珺的电影《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在某种程度上与《老兽》形成时间—空间维度上的互文。影片中,骑着骆驼寻找家园的阿迪克尔和巴特尔兄弟实际上是“老兽”回忆空间中二度美饰后的“自己”,是S点锥体于平面另一点上凝结的晶体。前者表征城市、老年及信仰遗失的阴面;后者象征故土、少年及永怀希望的阳面。电影《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虽然看似空间的主体是草原,但草原空间在影片中却无处可觅。
影片收束之际,当阿迪克尔久久地凝视着荒漠中烟雾缭绕的工厂时,潜在影像(回忆中的草原空间)与现实影像(工业空间)的交织使他的眼睛凝成了晶体的界面。“晶体显示或呈现的,是时间的隐秘根据,即时间在两种投向上的分化,一是正在逝去的现在,一是自身保存的过去。时间既使过去流逝,又把过去保存于自身之中。因此已经存在两种可能的时间—影像,一种基于过去,一种基于现在。” 透过阿迪克尔的眼睛,观众可以看到德勒兹时间—影像中的晶体寓言出现在了当下工业空间与过去草原空间交叠的回忆空间中。于是,在阿迪克尔晶体状的视网膜中,那一闪而过的“绿色回忆”就是晶体界面上的圆锥体顶点S点。
综上,两部电影在不同晶体界面上表达了相似的象征意象:草原人身处城市空间却无以为家,穿越回忆空间又故土难觅。在工业文明狂飙突进式的围剿下,实在的草原空间被逐步地吞噬,直至消隐。最终,不得不在回忆空间中以虚体的方式出现在潜在的城市象征空间中。其结果是,《季风中的马》《图雅的婚事》中草原空间的现实影像在《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中逐步沦为了主体回忆空间中的晶体影像;《绿草地》中毕力格一家想象的城市空间也成了《老兽》中的日常空间;那曾经驰骋草原的乌日根也只能在未来“老兽”的消磨时光中慢慢遗忘成吉思汗的历史壮举;阿迪克尔兄弟长大后也会在“何以路过未来”的迷茫中家园失守、进退失据。在上述乡土电影的回忆空间中,草原既是空间性的,也是时间性的。当回忆空间(乡土)与现实空间(城市)在某一点交汇时,回忆中再现的“历史时刻”、当下的城市空间便一同跳出了真实与虚幻、时间与空间的掣肘而凝固为一种永恒的晶体影像。

《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
三、差异空间:双城影像与第四堵墙
在三元空间概念的基础上,列斐伏尔还进一步将社会空间的生产拓展为绝对空间、神圣空间、历史空间、抽象空间、矛盾空间及差异空间等6种类型。其中,尼采式差异空间与黑格尔式抽象空间的对弈是阅读列斐伏尔资本主义空间批判理论的核心。在列斐伏尔看来,抽象空间倾向于均质化,而社会空间却并非均质的抽象逻辑结构,而是一个充斥矛盾、开放的差异性实践过程。对此,米歇尔·福柯也提出了“差异空间”(也译为“异托邦”)的概念,认为其既表征世界的真实,又指称世界中的世界。为详尽阐释,福柯列举了“差异空间”的六大原则,即多元文化性、历史相对性、单一场域内多重矛盾的并存、异托时、封闭与开放的双重特性,以及空间的真实与虚幻两极等。本文将以此两者为理论基础,结合银幕内城市空间的构形方式和银幕外“黑箱空间”的异托邦特质,对21世纪乡土电影中城市差异空间的运作机制和深层内涵进行多维度的探讨。
(一)幕内之城:差异空间的含混与复义
在新世纪乡土电影中,城市空间内呈现的各种场所,如娱乐场所、封闭式工厂、城漂聚居地、火车车厢、照相馆、理发店等,均在不同层面上展现了差异空间的特质,从而为观众提供了一个探秘城市复杂性的独特视角。
譬如,在电影《季风中的马》中,娱乐场所这一差异空间成为多重文化身份的交汇点。其中,“乌日根”是草原精神的守卫者,陶高代表着向城市生活无限趋近的草原背离者,毕力格则象征着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挣扎的迷失者。此外,还有众多沉浸于低俗狂欢之中的人群。这些角色不仅各自代表了传统、现代以及后现代等不同形态的文化,更在这一虚幻的空间内汇聚,酣畅淋漓地释放着各自的狂欢欲望。娱乐场所,其本质上可视为一个虚幻的世界,舞女和客人都戴着无形的面具,在与现实区隔的舞厅中酣畅淋漓。酒客们在这个空间中既感受不到传统时间的流逝,也意识不到对“马”(象征着草原精神)的羞辱实际上是对“自我历史身份”的羞辱,这暴露出福柯谓之比真实空间更为虚幻的本质。
(二)幕外之城:第四堵墙的建构与解构
前文所述的差异空间是电影文本内部的一种探讨,本部分则是将论题外延到了文本外部的差异空间:从影院到银幕。20世纪20年代,爱森斯坦受到了黑格尔辩证观的影响,提出了杂耍蒙太奇理论,认为电影的美学意义取决于异质镜头间的冲突与对峙。20世纪40年代,安德烈·巴赞对此持有截然不同的论点,并提出长镜头理论以阐述电影的真实美学观。现代电影理论阶段,麦茨又在中和两者论点的基础上,指涉了电影理论的两个新研究方向,即从电影符号学到精神分析学的引入。综上,无论是爱森斯坦、巴赞还是麦茨,都在表达电影空间的一种意向性:即电影空间是在主客互涉的过程中被层层建构的。只是爱森斯坦赋权导演,立志于铸牢第四堵墙;巴赞则将能动性交予观众,试图解构第四堵墙。无论哪种立场,电影院所表征的空间属性都指向差异空间。在新世纪乡土电影中,影院的差异性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影院在城乡现实地理空间与文化语境中的差异,二是银幕在观众幻象心理空间中的差异。
首先,是影院在城乡现实地理空间与文化语境中的差异性,这主要体现为影院空间公共属性与排他属性的共存。城市文化中的大众审美趣味与消费惯习都透露出城市文化资本对乡土文化的排异,而影院空间的区域限定更是在某种程度彰显着城乡阶级与文化身份的区隔。自电影诞生以来,全球电影史上见证了各式各样的场所作为电影放映的地点。在西方,咖啡馆、音乐厅和沙龙等地不仅是社交和娱乐的聚集地,也时常成为电影放映的场所。在中国,茶馆、戏院和露天广场等地也扮演着同样的角色。这表明,电影作为大众艺术的旗帜,曾为各阶层的人敞开大门。然而,21世纪的今天,既开放又封闭的城市影院则成为电影放映的主要场所。曾在乡土中国盛行一时的露天电影也成了特定年代的文化景观(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于21世纪后逐步萎缩、隐匿),被封存于电影博物馆的史料集册中。影院,作为现代城市的一种文化景观,成为市民阶层践行城市文化与审美趣味的仪式性场所。
与此同时,电影票的售卖机制也标明了进出影院的必要条件:坐标—城市、经济支出—买票、审美认同—兴趣、生活结构—闲暇时光。这是一个看似向公共随意开放的场所,只要符合地理条件与消费条件就可以随意进出影院。然而,仅就地理位置与消费惯习两点就已经区隔了绝大多数的乡土主体,这是影院空间对乡土主体的一种隐形排异。这与福柯的差异空间进出管理机制类同,即异托邦具有开放与封闭的双重性。21世纪以降,当廉价的露天影院销声匿迹后,乡土主体,尤其是年长的乡民实际上是很难看到自己在银幕上被表述的过程的。换言之,乡土电影作为全世界观摩乡土中国的文化标签,其创作与生产都是为“他者”群体服务的。

山东德州庆云县常家镇的露天公益电影(图片来源:《德州日报》)
其次,是银幕在幻象心理空间中的差异性,这主要体现在观看群体的心理需求与乡土电影的心理补赎上。“放映机、黑暗的大厅、银幕等元素以一种惊人的方式再生产着‘柏拉图洞穴’——对唯心主义的所有先验性和地志学模型而言的典型场地——的场面调度。对这些不同元素的安排重构着对拉康发现的‘镜子阶段’的释放所必需的情境。” 易言之,封闭的黑箱式影院以及摄影机暗箱等共同建构起“柏拉图洞穴”式的情景, 如此,银幕作为差异空间的支点,便在观众虚幻的心理空间中创造出一个补偿性的真实空间,用以补赎真实空间中的缺憾与不完美。
在城市观影者的心理空间中,乡土既是一个满足窥视、猎奇欲望的地域符号,又是一个表征诗意栖居的情感符号。窥视、猎奇的把玩心理使得城市观影者在观看乡土电影时不自觉地开启上帝视角俯视乡土,而诗意栖居的渴望又迫使他们以仰视的方式注目乡土,就如同回看幼时的童真。两种欲望的摩挲既是城市观影者走进影院欣赏乡土电影的心理驱动力,也是补赎城市居民高压生活下心理裂隙的疗愈良方。一般而言,在新世纪乡土电影中,补赎城市观影者现实裂隙的方式有以下两种:
一是与悬疑类型杂糅,通过紧张、刺激的视觉盛宴及悬念铺陈,放大城市“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暗黑特质,以期在造梦式的观影空间中完成观众对资本剥削的心理抒泄。相关电影有忻钰坤的《暴裂无声》、曹保平的《追凶者也》等。在这类电影中,城市以“恶托邦”的形象呈现,观众对乡土主体的同情不仅源于叙事的召唤,也根植于自身对于弱势群体的体认。幕内之城中,被压迫的是阶级身份的强弱(城市主体—乡土主体);幕外之城中,这种阶级身份的强弱则被直接置换成了等级身份的强弱(富人—穷人)。于是,在这种深层次的体认与同构中,银幕之镜起到了异托邦的作用,它消弭了现实影院空间的在场性:银幕对主体占据的位置实施了一种反作用力。在差异性的心理补偿空间中,幕内之城与幕外之城以同构的方式实现着双城影像的“里应外合”。
二是风景叙事的大面积铺陈,通过对乡土画面篱落青烟式的唯美呈现,放大乡土空间的柔美诗意,给“久在樊笼中”的城市观众们带来一丝“复得返自然”的沁人之感。这类乡土电影中,城市空间所占篇幅非常有限,有时仅以一种抽象的形式存在,来表现乡土主体对城市“等待戈多”式的荒诞期许,如电影《暖》《1980年代的爱情》《西施眼》《婼玛的十七岁》等。如果说前文造梦式的乡土悬疑片在观众的心理空间中创造的是一个补偿性的差异空间,那诗意乡土与“戈多”式城市传说的叠合,则为城市观众营构出一个纯虚幻的想象空间,这也是福柯差异空间概念很重要的一条原则:异托邦创造出一个虚幻的空间,并进而暴露出比真实空间更为虚幻的本质。在电影《西施眼》《婼玛的十七岁》中,“上海”与“电梯”的意象,对于阿兮、婼玛来说,从头到尾都只是一场虚幻的想象。然而,对于司空见惯的城市观众来说,影像对“上海”与“电梯”的重构会让他们产生一种“陌生化”的审美感,即“柏拉图洞穴之喻”中“影子”摹本,其带来的真实感与眩晕感在黑箱影院的操控下暂时性地代替了现实电梯。实际上,这种审美的真实感与眩晕感是虚幻的,因为当他们走出观影厅,切身乘坐电梯时,“电梯”意象带给他们的美感会瞬间戛然而止。他们就像“柏拉图洞穴之喻”中获释的囚徒,在看到真实世界后,才明白此城(光影之城)非彼城(观影之城)。
“银幕空间作为一种镜式空间具有某种拓扑学功能,就是让观看主体在想象的空间和真实的空间之间往返地位移,通过此处和彼处的循环变换而达至此与彼的界限的消融,达至想象和现实的相互替代,以至于最后银幕的空间和放映厅的空间混融在一起,形成一个多重空间交叉叠置的乌托邦空间。” 这个多重的乌托邦空间也是影院中可见的差异空间。
四、结语
研究新世纪乡土电影中城市形象的空间构型,就是以“空间生产”理论为基点,通过考察新世纪乡土电影中城市模拟空间、象征空间、差异空间的文化逻辑与隐喻,为新世纪乡土电影中的城乡关系作出合理的文化阐释。具体而言,在新世纪乡土电影中,城市模拟空间的建构,可以为现实城乡关系的变迁提供镜鉴参照;城市象征空间的考索,可以反映乡土导演在文化身份认同上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城市差异空间的探究,可以厘清城市空间“生产”与“被生产”的双重特性,并对拓宽乡土电影市场的进路大有裨益。综上,研究新世纪乡土电影中的城市形象的空间构型,既呈现了现代化进程中乡土影人的记忆纹理,也为过去——现在——未来维度中的“乡关何处”“乡村振兴”等问题提供着历史参照与蓝图设想。
原刊《上海文化》2024年第10期,注释从略

【作者简介】
魏玲,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艺术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戏剧与影视学,近期发表论文包括《构建当代中国话剧作品评价体系:现状、框架及意义》(《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乌托邦·恶托邦·伊托邦——新世纪乡土电影中城市形象的气质构形》(《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新世纪乡土电影中城市形象的叙事考索》(《新疆艺术》)等。
【新刊目录】
《上海文化》(文化研究版)
2024年第10期
专 题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上海实践
蒲 妍 赵正桥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理论主张、基本议题与实践进路
邓又溪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上海城市文化实践
访 谈
严 锋 金方廷 技术时代的文学、艺术与教育
理 论
朱 虹 袁 佳 媒介批评视角下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的流变与审思
文 学
叶奕杉 “跨越”何以养成新风格——论“新南方写作”的物我伦理表达兼及文学文化的跨界融合
纪水苗 “新南方写作”:文学事件的发生与文学策略的选择
杨 莹 方言实验与地方想象的空间建构——以“新南方写作”为中心
文 化
刘 欣 重绘游戏思想史谱系:游戏思想史视野下电子游戏本体论的断裂与重构
李汇川 电子游戏的三重交互关系与叙事
严奕洁 黄锐杰 生命之“涌现”——《塞尔达传说:旷野之息》与游戏现实主义的第三条道路
文 艺
魏 玲 模拟、象征与差异——新世纪乡土电影中城市形象的空间构形
卢巍文 中国新黑色电影的现实主义审美表征研究
书 评
徐同欣 《拉斯科,或艺术的诞生》:巴塔耶的起源话语
编后记
英文目录
封二 周卫平《古镇边道》
封三 好书经眼录
《上海文化》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扩展版)来源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引文数据库来源刊
社长:徐锦江
常务副社长:孙甘露
主编:吴亮
执行主编:王光东
副主编:杨斌华、张定浩
编辑部主任:朱生坚
编辑:木叶、黄德海、 贾艳艳、王韧、金方廷、孙页
《上海文化》(文化研究版)
主办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地址:上海市中山西路1610号2号楼928室
邮编:200235
电话:021-64280382
电子邮箱:shwh@sass.org.cn
邮发代号:4-888
出版日期:双月20日
主编:朱生坚
编辑:曹晓华
运维:任洁
制作:小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