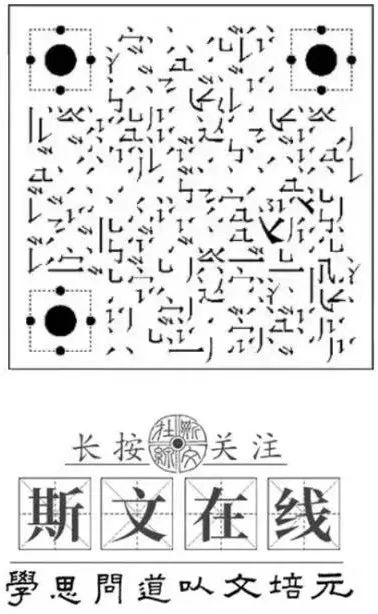地方性是人类普遍经验的基本存在维度,人的具体生命是在地方社会关系中生成,地方性生活场景不仅仅是“恋地情结”(段义孚语)的来源,同时也是个体意志与行动展开的基本出发点。袁红涛所著《地方的浮沉:现代乡绅叙事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3年;以下简称《浮沉》)一书,引入地方性视野,以百年来乡绅叙事为研究对象,揭示个体在历史情境中的命运展开,在对乡土生活世界的观照与呈现中揭示这一阶层的历史变迁,梳理小说人物及叙事主体之欲望情感、思想意志,彰显个人在历史洪流中的能动性作用。同时,又将这一阶层置于总体性社会结构变动中进行辨析、梳理,考察其分化组合的不同路径,探索乡绅个体与地方权力网络、地方公共空间之间的互动关系,提供了关于地方性问题的独特思考与研究进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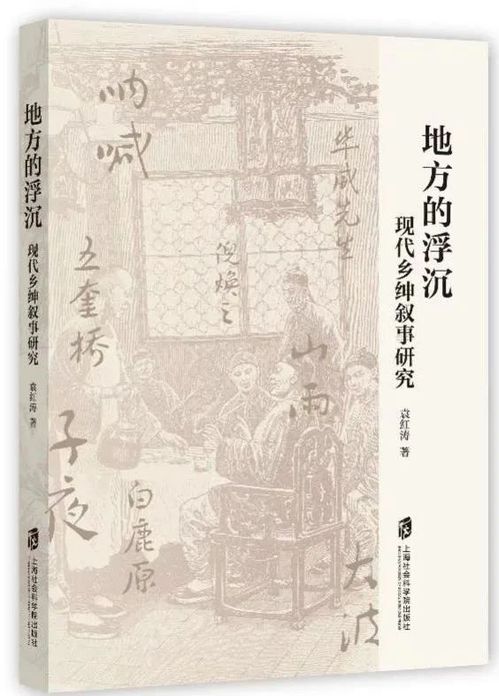
《地方的浮沉:现代乡绅叙事研究》
袁红涛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3年版
“乡绅”是中国二十世纪文学中的特殊人物形象。丰富驳杂的文化意识、多元复杂的经济身份以及逐渐向边缘位移的政治地位,使得这一阶层在风起云涌、改天换地的历史变动中呈现出整体性的晦暗暧昧态势。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着近现代以来社会转型之际的阵痛,同时也蕴含着叙事者在旧秩序崩溃而新秩序尚未形成之际的迷惘与犹疑、反思与探索。“发现”乡绅,是《浮沉》一书的重要主题。袁著通过对经典文本的重读,打捞起若干在以往研究中被忽略的人物形象,如鲁迅《离婚》中的慰老爷与七大人、叶圣陶《倪焕之》中的蒋冰如、王统照《山雨》中的陈庄长、茅盾《子夜》中的冯云卿等,揭示其各自不同的“乡绅”身份及个性,从而在时代转型、阶层结构变动视野中分析人物心理与行为动机,在乡绅与乡民的互动中揭示绅权运作的过程,为理解、研究作品打开新的空间。这一研究方法也延伸至对当代文学作品的解读中,如分析贾平凹《腊月·正月》中韩玄子的人物身份及其行动逻辑,探测并描摹陈忠实《白鹿原》中朱先生与传统士绅阶层的精神联系,在以往基于民间文化、道德秩序角度的研究之外,揭示人物活动与乡土社会政治、经济形态的有机联系。
在充分梳理并呈现乡绅人物图谱的同时,袁著进一步勾勒时代转型之际乡绅阶层存续、分化的不同路径:一部分乡绅迅速攀附新兴政治力量,逐渐与传统乡土社会分离,在经营地方关系网络中谋求私利、鱼肉乡里,成为“劣绅”,如茅盾《动摇》中的胡国光,洪深《五奎桥》《香稻米》中的周乡绅与姜老爷等;也有一些乡绅,积极吸纳西学,意欲振拔而图国之富强,如《霜叶红似二月花》中的钱俊人、朱行健等;更有一部分人在时代动荡之际彷徨失措,虽抱持着朴素的乡绅情怀,却无力调和传统意识与现代文化的矛盾,最终失去乡民信任,走向衰败,如王统照《山雨》中的陈庄长、洪深《青龙潭》中的林先生等,其形迹是乡绅叙事中格外浓重悲凉的一笔。《浮沉》借由对鲜活人物形象身份的还原而揭示乡绅复杂的存在形态,力求表现个体在应对世事变化时的不同策略与处事方式,从而在传统的“地主”身份、阶级话语之外发掘并彰显出个体的情感欲望、思想意志,充分体现“历史中的人”这一命题的丰富内涵。与此同时,袁著对乡绅身份及其阶层分化的揭示也延续至“子一代”。如《霜叶红似二月花》中的钱良材,以往研究多以“青年知识分子”称之,但袁著则将他对父辈、自身道路的反省与士绅阶层嬗变相关联,认为只有理解他作为乡绅“子一代”的身份意识、文化心理,才能更清晰地把握其内心深处的困惑与迷茫。同样,王统照《山雨》中的陈葵园继父亲之后成为一代新乡绅,其崛起与新学教育有密切关系,也因为与地方社会分离而不断劣化。此外,《浮沉》重提鲁迅笔下的“假洋鬼子”,借此指出彼时中国的乡绅构成来源已呈现多元化趋势,其间蕴含着新学与旧路、维新与革命、“地主”与现代知识人等多重矛盾关系及历史走向的初始形态。
《浮沉》在梳理乡绅阶层历史走向、描绘人物精神图谱时,格外注重近现代以来国家与地方关系的消长变化所产生的影响。在明清时代,乡绅与国家权力共生,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构成对中央权力的制衡,在地方自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绅权运作过程中,传统伦理道德起到了重要的维系作用,乡民的信任也基于此产生,此所谓绅权在下而不在上。然而,清末民初以后,传统乡土社会逐渐崩溃,乡绅阶层开始分化。同时,乡绅对乡村的道德责任感逐渐淡化,有的成为控制地方利益资源、唯以谋求私利为重的“劣绅”。对于这一历史进程,袁著借助于分析王统照、茅盾、洪深等作家的叙事,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考察,探索乡绅阶层与地方权力空间的密切互动,也充分呈现了乡土社会共同体的裂痕不断扩大、趋向分离的态势。《浮沉》通过文学叙事分析国家与地方关系变化对乡绅阶层分化的影响的同时,引入社会学的“地方性”视野,探讨乡绅在地方权力结构中的角色与作用,从而进一步打开文本解读空间。譬如,考察李劼人“大河三部曲”关于四川绅界分化与变迁的叙事,进而探讨近代以来四川基层社会权势结构在西方力量刺激下的剧烈变动,勾勒绅界、官员、学界、洋教势力、袍哥等各方势力的角逐图景,并从中发掘“绅士公共空间”的萌发与新质,从而揭示出李劼人自觉的“社会”意识与书写“社会”的追求。又如,分析贾平凹小说《腊月·正月》中地方社会空间的绵延与复苏、变化与重组,从而指出,“地方社会的发现”乃是贾平凹一九八三年重返商州之旅的重要收获以及写作转向的肇始,显示了社会学视野及方法在解读文学作品、作家感觉结构时的有效性。

《乡绅》(瑞士记者博萨特1930年冬摄于中国河北农村)
袁著揭示不同背景、处境下的乡绅个体在差异性地方社会空间中的生活方式与道路选择,进而表现个体情志突进历史的过程。历史浩浩荡荡,由无数个体的情感欲望、思想意志汇聚而成,经典作品往往能以全息的方式保存最为生动鲜活的人性“数据”,《浮沉》力求呈现“地方性”月映千湖般的存在形态,照见多姿多彩的生活世界,在理解彼时彼地的人物个性角色、身份认同的同时,反观自身在现代知识、价值体系中的位置,进而启发思考现代社会中关于地方公共空间建构、知识分子角色等一系列议题。“乡绅”本是与古代士人阶层有着内在精神联系的群体,绅权的运作与个人的道德意识、文化修养有密切关系,其进与退不仅关联着地方权力空间的消长、社会秩序的存续,同时也关联着文化传统的当代转化。乡绅及其“子一代”,无论是告别乡土而走进城市,还是固守乡土分化重组,抑或出海后回归而成为“假洋鬼子”,都体现了个体不断寻求意义的过程,其差异性的道路选择在历史中留下的印记——不管共振还是背离——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可能尚未被充分揭示,历史代际延续之间的断裂也有可能会以另一种“出走——回归”形式弥合,显示出钟摆效应的特征。就此而言,总体性研究亟待加强,譬如不同学科研究方法的交叉互渗,在整体性视野下观照士绅阶层及其文化传统的古今流变,以及知识分子的公共性意识构建、当代社会治理视野中对地方性经验的探索,等等。袁著已经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尝试,并在方法论方面起到相当重要的示范作用,如社会学及历史学视野的引入、文史互证方法的运用等,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百年乡绅叙事研究的范围及深度。
近年来,关于“总体性”的意识逐步强化,不仅与学术脉络自身的内部生长与创新有关,也与外部社会的变化生息相通——对“总体性”的兴趣已经溢出了学术研究领域,而在社会热点话题讨论、大众流行文化中受到追捧,这反映了个体在快速变化的时代中渴望了解自身位置以积极应变的深层心理。但与此同时,也有论者基于对“总体性”的追求而对“细微”“琐碎”的文学提出疑问,这在文学批评中多见。在文学创作中,也有因过度追求总体性、无意于建构鲜活饱满的生活世界而损伤艺术性的个例。因此,应注意避免将“总体性”固化为一种理念,而强调其实践性、动态性特征,使文学始终有能力保存生活的复杂性,在对亿万个体欲望升腾与湮灭的描摹中贴近宏大精微的全息图景。人类重要的精神文明成果往往致力于探求总体与局部、大与小、一与多、上与下的融通化合,从而在动态平衡中探索和谐之道。在这一点上,《浮沉》的探索值得重视。一方面,《浮沉》体现出对“总体”的自觉关注及辩证性思考,如打通经典文本与社会总体结构之间的有机联系;另一方面,又深入辨析“总体性”文学话语与基于生活实践的“总体性”之间的差异,将“总体”置于具体的生活实践中进行检验,揭示文学批评与研究自身可能存在的洞见与不见。由此,通过对研究话语与时代话语之间内在关系的分析,袁著进一步敞开“总体”的本真性存在,不仅以“地方性”凸显“总体”的丰富性、复杂性,同时也在文本细读、文学研究现象分析中,探索叙事者自身思维、视野的局限,从而使文学话语的“总体性”摆脱机械性,不断靠近生活实相。

乡绅出行(英国摄影师格雷戈里摄于1920年代)
在国家与地方、总体与局部的动态关系中观照乡绅叙事,《浮沉》所讨论的问题具有强烈的现实指涉意义,充分体现出文学研究的当下性特质。历史上的乡绅阶层虽然已不复存在,但乡村基层治理与经济文化建设却同样需要共享地方性知识、构建地方公共空间网络,近年来关于“新乡贤”的呼吁正体现了这一需求。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就传统乡绅而言,伦理道德所构成的礼教体系是其存在的重要基础,因守护道德秩序方能保证熟人社会中的个体持续获得长久利益。但随着现代经济发展、人员流动,乡村公共事务的内涵、范围发生巨大变化,道德已无法成为新乡贤存续的核心根基。《浮沉》梳理相关的文学叙事从而描绘乡村权威人物的更迭路径,如指出《腊月·正月》中韩玄子与王才的矛盾,实质上是新一代的经济能人替代了老一代的文化权威从而引发“地方影响力”之争,并进而发现地方社会秩序在变更中所显现的韧性与活力,这就为理解乡村生活世界的具体权力关系场景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研究方法示范。作者特别提示,“在现代化、革命整体进程与地方社会的具体实践之间存在空间,由此才能理解和认识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从乡绅覆灭到召唤新乡贤之间,并非一片空白”。同时,《浮沉》也重申文学关于“政治”多重内涵的理解,如在分析陈忠实《白鹿原》时指出,白嘉轩并非如一些学者所言“疏远政治”,他本就置身于地方“政治”之中,只是其政治理念与动员方式偏于传统而非现代,乡土社会的政治形态与现代知识框架中的政治概念并不对等。就乡绅这一阶层而言,实则可看作是传统社会中的“代理人”制度,在道统、政统合一的社会,能够起到润滑关系、减少社会运行成本的作用,缓冲国家权力与地方利益的摩擦,但在现代性全面扩张、资本与信息流动加速的时代,其存在成本相对于以往大幅提升,因而也注定了其衰败的命运。
古代“乡绅”的核心意义在于以“士”的道德理性维系绅权运作,在个体修养与外部社会机制之间寻求平衡,体现出儒者与封建王权的复杂关系。无论是“绅士鬼”与“流氓鬼”的辩证,还是“作为方法的乡绅”,都体现出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知识分子对自身角色、身份定位的认知,也体现了在现代视野中如何转化传统的思考,而在这一过程中,“地方”则是重要的支点。“地方”并不意味着封闭,甚至正因心系地方,才能成就“天下士”,正如从小世界、小日子出发,反而更容易看清宏观权力机制内部的不同利益诉求,从而寻求并实现自洽,促使总体与局部、上层设计与地方经验相统一。基于此,梳理乡绅叙事经验,探索乡绅阶层的分化变迁,在地方性视野中探索人的归属与认同,考量个体与地方生活空间、权力空间的互动,不仅是重构“记忆之场”(皮埃尔·诺拉语)的必要路径,同时也能够更为有力地立足当下、想象未来。
(原刊于《书城杂志》2024年9月号)

【作者简介】
王小平,复旦大学文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副教授,上海市“晨光学者”、“浦江学者”,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主编:朱生坚
编辑:张晴柔
运维:任洁
制作:小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