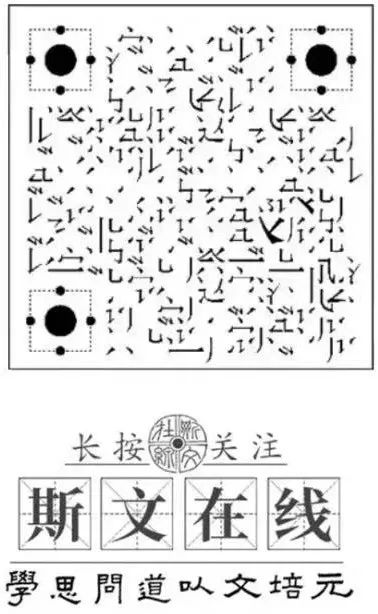一、“大时代的文学”风云激荡
王西强:谢谢张老师接受我的访谈。您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一直追踪新时期文学的发展进程,是中国当代文学流变的见证人和鼓吹者。同时,您也对百年中国新文学予以积极的关注,参加过“百年文学书系”的撰写。您领着我们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选题,就叫作“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的变革研究”。您觉得在我们这个消费为王的快餐文化的小时代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大时代并置的时代背景之下,我们怎样对百年新文学作出一些新的思考呢?
张志忠:回答这个问题,可能要写成一本书或者一套书。结合中国式现代化与百年新文学之关系的思考,我认为它比较完整的说法应该是“中国式现代转型之大时代的百年新文学”,缩略一下,在我们的对话中,我称之为“大时代的文学”。今天我们选取其中的一个点,从百年新文学的起源及其某些特征谈起。
王西强:您一开始就让我感到振奋,“中国式现代转型之大时代的百年新文学”这个论题非常有震撼力,请您从源头上讲起。
张志忠:文学发自性情,成立于语言,所谓“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从人类早期开始发生,古今中外皆然,有常有变,有盛有衰。人类在生存与发展中,产生了语言和思维,形成了面对自然、面对社会和面对个人生存诸多命题的丰富感受,对生活非常敏感而富有语言表达技巧的人们,将其富有艺术性地表达出来,从“断竹削竹飞土逐肉”开始,创造出文学的各种形态。鲁迅先生说,诗歌起源于劳动,人们为了协调共同劳动扛木头的节奏,产生劳动号子,这就是诗歌中的“杭育杭育”派。小说则起源于休息,人们劳动累了,休息的时候就想要听些什么逸闻趣事,放松心态,化解疲劳,于是就有人讲故事。这就是文学的常态,自然而然地生长起来。我们的百年新文学,则是一种非常态。它的特征何在?什么是中国特色?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文学当中的体现?我觉得,首先它就是一个“大时代的文学”。
韩少功有一篇创作谈,说到他出国到欧美国家去访问的感受。欧洲也好,美国也好,第二次大战结束以后,整个社会进入一种常态性的发展,风平浪静,没有大的动荡,没有大的战争。和韩少功年龄相近、在二战后出生的这一代欧美作家,他们感慨说中国的作家很幸运,有这么多的故事可讲,有这么多的非凡经历,有这么多的命运传奇时代的变迁造成人和社会的跌宕起伏柳暗花明,给作家提供了广阔的写作题材。他们说我们在欧美的生活风平浪静,读书、就业、成家、写作,经验相近,感受类同,没有大的波澜起伏,没有大的时代风暴所造成的戏剧性、社会性、普遍性的矛盾和冲突。就业与升职,恋情与婚姻,内心的焦虑,生活的烦恼,似乎就是生命的全部。与之相应,德国汉学家抱怨中国作家为什么要讲故事,他推崇的是欧洲小说刻镂人物的内心世界,和一个苹果写100页的描写能力。

一正一反两个例证,都是在辨析当代中国文学的独特性。对此我可以作一点补充。韩少功和我,都是“50后”,这一代人经历了共和国的全部进程,尤其是从“红卫兵运动”“上山下乡”到“恢复高考”,从“改革开放”“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全民下海”“工人下岗”“乡下人进城”等等,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每一个重大举措都改变千百万乃至亿万人的命运。这也成就了大量的作家。近些年很亮眼的“铁西区三剑客”,双雪涛、班宇和郑执,他们都是“80后”,但他们都在讲述父辈的故事:曾被称为“东方鲁尔”的工业重镇沈阳市铁西区,经历了从辉煌时代到国企改革阵痛的转变,父辈下岗之后的艰辛辗转的谋生自救,成为他们创作的聚焦。因为历史的亮点和痛点切换得过于频繁,乃至在电视剧作中专门出现了一种独特的类型:“年代剧”,从《大宅门》到《人世间》,从《繁花》到《大江大河》,成为电视剧中的带头大哥。这就是清代文学家赵翼所云,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风云激荡的时代,容易产生大作家大作品。当然,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冲突永远都会有,不管是普通劳动者的劳作图景,还是资本家集团或者社会上各个政党之间的经济竞争与政治博弈,家庭纠纷,两性战争,都是社会常态,但是我们经历过的那种牵一发而动全身式的大的动荡、大的冲突,在西方人远远地看来不明就里,在中国人呢,则身处其中感同身受,惊心动魄,悲欣交集。这也成为有心思有见识的作家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来源。
二、“文学与时代到底是什么关系”
王西强:您对中国式现代转型的大时代的描述引起我的很多思考。这也让我联想到唐德刚提出的“历史的三峡”的命题。唐德刚指出,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就是您说的现代转型的历史,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大约需要两百年,他的参照是秦汉之际历史转型的两百年。穿行三峡,波涛汹涌,险象环生,却也有无限风光,让作家神醉心迷。那么,中国作家怎样体认这风云激荡的大时代呢?
张志忠:唐德刚说的很有道理。秦汉交替之际的两百年,郡县制和集权制,以及儒表法里的统治思想,开时代新风,造成中国农业文明时代持续两千年的政治体制。中国式现代转型的大时代,无论是从1840年算起,还是我们这里讨论的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讲起,确实和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朝代更迭有着本质的区别,一开始就引起有识之士的高度重视,也引发现当代作家的自觉认识。
就像李鸿章,洋务运动的开创者,走出国门的最高位的重臣,非常有眼光,他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来描述鸦片战争以来古老中华所面临的前所未有之存亡危机。“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之所未载,亘古之所末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李鸿章:《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这就是我们常常引用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说法的出处之一。
百余年间,从文学的角度提出“大时代”命题的作家不在少数,我这里仅以鲁迅和韩少功为例。
1927年12月,鲁迅在《〈尘影〉题辞》中,称赞《尘影》反映了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大革命时期,湖南作家黎锦明在广东海陆丰亲历彭湃领导的农民革命运动的兴起与失败,目睹革命者的奋斗与殉身,以此写成中篇小说《尘影》,鲁迅在《〈尘影〉题辞》中说:“在我自己,觉得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但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许多为爱的献身者,已经由此得死。在其先,玩着意中而且意外的血的游戏,以愉快和满意,以及单是好看和热闹,赠给身在局内而旁观的人们;但同时也给若干人以重压。这重压除去的时候,不是死,就是生。这才是大时代。”作为最清醒的现实主义者,鲁迅断然指出,这个革命与震荡、流血与牺牲的大时代,以其生生死死、轰轰烈烈而超越于日常生活之上,但它的未来走向并没有绝然向好的保障,尚需人们的全力拼搏。

并非偶然,时隔近百年,韩少功也提出“大时代”,并且对“小时代”与“大时代”的文学差异予以深度辨析。韩少功由郭敬明执导的系列电影《小时代》讲起,指认其表现出当下这个吃喝玩乐、花天酒地、纸醉金迷、娱乐至死的时代。韩少功提出:什么是“大时代”呢?其范例之一就是史家们说的“启蒙时代”,即从欧洲的16世纪开始、俄国的18世纪开始、中国的19世纪末开始,直到今天的所谓“现代化”过程。大时代的作家不乏世界文坛的巨擘。英国的狄更斯、法国的维克多·雨果、俄国的托尔斯泰,用他们的笔展现了战争、革命、人间苦难,一幅幅风云变幻的历史画卷。以前很多中国作家也把文学看作“旗帜”“号角”“投枪”“匕首”,紧紧地盯住时代,有力地介入时代——这些作家同时代的关系看起来好像比较明显(韩少功:《文学与时代到底是什么关系》,《财新周刊》2017年第3期)。
韩少功对时代的嬗变非常敏感,他懂英语,国际视野开阔,非常关心科技发展新成果,对中国当代历史慧眼独具,他的思想家气质在同代人作家中,只有张承志可以媲美。在2010年之后,我也曾经以为,中国崛起而雄踞世界,中国的现代化追求大局已定,大时代行将结束,小时代即将当道,普普通通地过日子,波澜不惊地向前行,那些杯水风波即将会成为文学的日常。所以,对《小时代》,我没有韩少功那样强烈的不屑。对于社会与民众而言,长治久安,能过好日子,就是最大的幸运。然而,从特朗普引发的中美贸易战,到当下俄乌、哈以的战争状态,反全球化运动与民族主义-民粹主义高涨,以及国内经济状况遭遇新的挑战,都告诉我们“大时代”仍然在路上,“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仍然是任重道远。文学如何体认和表现这“大时代”,也仍然是中国文坛的超级课题。
三、百年新文学与现代民族共同体的艰难建构
王西强:您用“大时代”与“小时代”,常态与非常态的辨析,界定百年新文学的基本特征,为中国式现代转型与同时代文学的关系作出独到的阐述,让我很受启发。那么,“大时代的文学”,在具体展开的过程中,有哪些基本特性呢?
张志忠:“大时代的文学”的基本特征,包括诸多方面,我还在逐渐地将其梳理出来,将其学理化。首先要注意到,现代化是全球性的,在世界各国次第发生,互相影响,对于近现代以来的中国,它的独特性就是它所面对的多重难题:抗御帝国主义列强的吞并危机,实现民族独立;扫荡数千年君主专制的陈旧体制,实现政治、经济、文化和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从英日君主立宪制、美法民主共和制、俄苏红色专政、北欧社会主义等多种模板中苦苦寻觅,进行现代民族共同体的艰难建构。基于现代印刷术而出现的现代报刊,从文言文蜕变为现代汉语,以及现代教育体制促进了人们的价值观转换,促进了现代意义上的阅读与写作,应运而生的中国现代文学为现代民族共同体的建构发挥了积极的社会情感动员作用。
这样的描述受到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的启示。安德森提出,即便再小的民族,它的民众也不可能彼此相识、直接认同,而是“想象的共同体”。在不同的民族和民族主义形成过程中,资本主义印刷术,现代报刊,特别是小说,作为一种具有极强的传播力的文化产品,对于民族认同感的塑造,发挥了重要作用。小说通过其叙事方式,打破时间、地域和社会阶层的阻隔,将建立现代民族共同体的理念与情感传导给民众,帮助人们构建对民族共同体的认知,从而强化民族认同感。
安德森对“想象的共同体”的阐述的适用性,遭到学界的质疑。有学人以为,安德森作出的论断是基于他对南洋的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亚等前殖民地国家的考察,而中国早在夏商时期已经形成了稳定的民族共同体。所以,安德森的理论并不适用于中国语境。但是,这样的否定性说法并不具有充分的理由。中华民族的自觉意识,从自称是华夏族裔,从三皇五帝的传说开始,到孔子的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产生强大的凝聚力,延续数千年,锲入中华民族的灵魂。但是,从农业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之际,中国和欧美现代国家的境遇不同,它是在列强环伺、丧权辱国、瓜分危机日甚一日的屈辱状态下,开始了民族现代转型的艰难历程,它需要经历古老文明的自我清算,求得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实现民族的现代认同。它形成了内外两种张力:既要张开眼睛看世界,向世界各国文化与文学汲取新的精神资源,又要以弱小民族的悲凉悲壮去抗争帝国主义、西方霸权的欺凌践踏,维护民族尊严,争取应有的世界平等地位;既把民族复兴的希望寄托在亿万普通民众尤其是广大农民群众身上,又时时焦虑地面对国民性批判的沉重课题,进而产生知识分子的自我怀疑、自我忏悔与自我批判。这比起欧美诸国及南洋国家所面对的形势都更为严峻和沉重。百年新文学自觉地承担起这一使命,也创造了自身的辉煌。安德森所言的现代报刊、语言变革和文学新创,在近代以来的中国缺一不可,三者的良性互动,催生出百年新文学。而且,与那些南洋岛国相异,中国的作家和文化人,他们对此有着更为充分的自觉,他们为此所作出的全方位努力,也远非后者可比。
建构现代民族共同体的宏大历史命题,给20世纪的作家以一种新的职责,他们大都同时具有多种身份。一种习见的说法是,自从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读书人通过科考获取功名进而跻身仕途的传统发展道路被阻断,现代知识分子的职业化、专业化得以取而代之,现代意义上的教师、律师、医生、工程师等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在我们所讨论的文学论域,如前所述,依照安德森所讲在现代民族共同体建立过程中的现代印刷术、报刊和出版物、现代语言的建立等诸多要素,“大时代的文学”发端期的作家们,他们不曾躲进书斋和研究室,而是直接诉诸社会、诉诸民众,除了从事教师和作家的职业,还积极地投身出版业,办报纸和刊物,用现代汉语写作,开创百年新文学,进而评说社会现状,直接投身现代政治,探求改革乃至革命的路径,在多个方面取得开创性的成果。

恩格斯称赞文艺复兴时代的达·芬奇、路德、马基雅维利等为文化巨人,称赞他们同时在多个领域进行开创性的工作,具有多种才能。百年新文学起源阶段的一批领袖人物,也大都有着多种才能、多重身份,有极强的实践能力。首先,他们都是宣传鼓动家,为了表达自己救国救民的思想,办报纸办刊物,办出版社,在报刊上发表自己的文学作品和文学评论,通过出版社出版自己的著作。他们还都是文学活动家,通过组织各种文学团体和文化团体,如“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新月社”等,凝聚同道,抱团取暖,产生集团效应。其次,他们都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以各自鲜明的立场投身于政治活动,无论是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的陈独秀、李大钊,还是在大革命失败后于白色恐怖中加入中共的郭沫若、冯雪峰,或者是曾经宣称“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胡适等自由派文人,概莫能外。胡适在文学革命大潮中是最为稳健的,他一心要从事新文化的建设工作,为更新中国政治做好思想文化的准备,但现实让他无法置身事外,从“好政府主义”的倡导,到国难当头时出任驻美大使,再到参与创办《自由中国》鼓吹美国式民主自由,将文化主张和政治实践融为一体。
四、有预设目的的文学建构
王西强:您借用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的理论,阐述百年新文学起源的诸种关系,让我很受启发。晚清的四大谴责小说,都是借助了新创办的各种报刊得以发表和流通的,正因为如此,这些作品的时政性、批判性加上花边新闻、官场黑幕,赢得了大量的读者,获得报纸销量和作品转播的双赢。梁启超创办《新小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茅盾主持《小说月报》,就是为了拥有一片新思想新文学的成长园地。我的理解是,这是百年来中国社会对于文学的社会性需求,是百年来中国作家的现实考量。我想继续请教,“大时代的文学”还有那些特征呢?
张志忠:“大时代的文学”的又一特征是它的体制建构性。
《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的作者柄谷行人说,日本现代文学并不是随缘性的,而是一种隐秘的建构,是民族现代转型中的伴生物,是一种人为的装置,文学与民族国家建制有着共谋关系。它是日本民权运动(明治初期发生的以反对专制政治、争取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权利为主旨的政治运动)失败后的文化颓唐的产物,“风景”“内面”“疾病”“儿童”等概念或意象的重新发现,或者说是一种颠倒的装置。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的译者赵京华在译者后记中明确表示,自己译介《起源》的目的正是在于由柄谷行人对日本现代文学起源的考察而获得的反思中国现代文学的刺激和启发,因为尽管日本与中国在现代性上有诸多差异,但面对作为现代性发源地的西方,中日的现代性问题则具有诸多相通之处。这样的思想方法也可以移用过来考察中国的百年新文学的起源与建构。
说到“大时代的文学”,它不是纯文学的生产,而是有一种预设目标指导下的文学体制建构。上一节我们所讲述的就是它与现代民族共同体的建立的共生关系,无论是梁启超、鲁迅,还是陈独秀、胡适的文学主张,它在效力于启蒙-救亡-解放和改革大业,建立独立富强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同时,也成功地建立了与中国古代文学有很大分野的中国现当代文学。
但是,中国现代文学与日本现代文学同样有着鲜明的差异。从其起源来说,较之以日本民权运动失败造成的民众的心灵挫败,现代文学从改良社会退身而转向“内面”,转向“个人”“心理”“忏悔”等人物的精神世界的发现,中国现代文学则是轰轰烈烈的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是在后者的狂飙突进中崛起的。它要面对的时代难题,我们常规地说是反帝反封建,抵制帝国列强的侵略瓜分危机(五四运动从文化启蒙转向爱国群众运动的关节点就是一战胜利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侵吞青岛的狼子野心),以及清除帝制和北洋军阀专制。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点,日本在明治维新实现之后,就进入现代转型的快车道,到1970年代柄谷行人写作《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之际,其现代转型已经完成。柄谷行人是站在后现代主义立场,对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进行症候式分析、溯源式清算,而中国的现实却更为千回百折,探索民族复兴路径的过程路漫漫其修远,至今仍然在路上。
就以柄谷行人提出的疾病隐喻母题而言,日本文学中的肺结核病描写,分别具有写实的和象征的两个层面,因作家气质而异,在现代中国的语境下,它却两者兼而有之,更多地是一种民族寓言式的书写。疾病和疗救,是鲁迅小说的一个中心命题,总是寓民族危机以个人存灭,华小栓、魏连殳等都是罹患肺结核,却分别隐喻着蒙昧的民众和觉醒之后无路可走的新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郁达夫《茫茫夜》《南迁》《银灰色的死》等作品的主人公都是肺结核病人,让那些“零余者”身心憔悴饱经摧残,也与鲁迅笔下的魏连殳等心有灵犀。丁玲笔下的莎菲女士,巴金《寒夜》中的汪文宣,同样是身患肺结核,他们的心病却各有千秋,显示出时代与个人的生死纠缠。
再比如,日本现代小说之所以转向“内面”和“自白”,柄谷行人认为,这是因为自由民权运动失败,政治理想受挫后,参与社会变革的路径被阻断,作家们转向内面,醉心于内心世界,加诸现代心理学理论和基督教会的告解制度,让日本文学转向“私小说”,并且以此作为日本文学的典范类型。柄谷行人说:“重要的并非芥川龙之介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文学动向的敏感,也不在其有意识地创作那般‘私小说’,重要的是芥川把西欧的动向与日本‘私小说式的作品’结合在一起,使此类‘私小说式的作品’作为走向世界最前端的形式具有了意义。”(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这也让我们联想到德国汉学家顾彬极力推崇的“一个苹果可以写100页”的欧洲小说。中国现代文学的海外发源地之一就是日本,郁达夫、张资平等都曾经追随“私小说”创作,但是,他们都无法完全躲进个人的心事之中,郁达夫的弱国子民的悲叹,张资平革命与恋爱的拼贴,使他们得以跳出“私小说”的窠臼,而染上时代的风霜雨雪,朝晖夕阴。
在加拿大现代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看来,每个不同民族不同国别都有其文学的总主题。代表美国文学中心象征的是它的拓荒精神;代表英国文学的是它的岛屿精神;而代表加拿大的则是生存精神。以加拿大文学为例,寒荒境地为人的生存提出严酷挑战,而现代化时期的过度开发和环境污染则困扰着现时代(阿特伍德:《生存:加拿大文学主题指南》)。中国现代文学的主题,是国民性的批判与再造,文学的开新与语言的再造。从源头上讲,梁启超提出的通过“新小说”的创作与传播,新人心,新政治,新道德;陈独秀首倡“文学革命”和三大主义,涤旧开新;胡适倡言“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将语言的变革作为文化变革的焦点;鲁迅将文艺视作引导国民精神前行的灯火,要“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凡此种种,都成为中国现代文学起源的预设路标。

日本文学专家谭晶华指出,以西方近代自我观念为轴心发展起来的日本现代文学思潮,造成不健全的一面,以及造成由其衍生的日本现代文学的软弱性格。这也是柄谷行人批判日本现代文学的症候的出发点之一。它是在不触动现实的社会格局和专制残余的前提下,展现个人的心灵躁动、情感欲望与精神探索。中国现代文学则是在现代理性烛照下省思,怎样塑造与现代民族共同体建构同步的国民性格。日本20世纪30年代的革命文学溃败之后,公开宣告政治“转向”得以被释放出狱的岛木健作、中野重治等一批作家转向了“私小说”创作。而在大海的另一边,唯美主义的苦吟诗人闻一多,优雅惆怅的雨巷骚客戴望舒,却是在20世纪40年代走出象牙塔,参与到民族解放的伟大斗争中来。
从建构的角度阐释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源与基本母题,也是个很有意思的研究课题。比如说,日本文学发现了“个人”,中国现代文学发现了作为中国国民主体的农民和生不逢时的新知识分子——“多余的人”。比如说,“XX+恋爱”的叙事模式,从鲁迅的《伤逝》发端,“启蒙+恋爱”“革命+恋爱”“改革+恋爱”“商战+恋爱”,都是大时代在某一时段的特定命题,与青年男女的爱情叠加在一起。还有“救亡+恋爱”,情场+战场。1936年,大上海的几位演艺界明星,赵丹、叶露茜、唐纳、蓝苹、顾而已、杜小鹃在杭州六和塔举办集体婚礼,然后回到上海招待众宾客,文艺界人士多才多艺,浪漫不羁,晚会上演唱了“定制”歌曲《六和婚礼贺曲》。贺曲由孙师毅作词、吕骥谱曲,“六和塔下影成双,决胜在情场,莫忘胡虏到长江”,“喝喜酒,闹洞房,五月潮高势正扬,共起赴沙场,同拯中华复沈阳”一时传为佳话。你看这样的场景,令后人不可思议。
五、别求新声于异邦,转益多师是汝师
王西强:您讲的太有趣了,对“XX+恋爱”的叙事模式作出了新的阐释新的理解,也更加深化了“大时代的文学”之时代的印记。您把鲁迅的《伤逝》作为“XX+恋爱”之肇始,那么,“XX+恋爱”就获得了正面的积极的评价。就像刘纳老师所言,问题不在于写什么,而在于写得怎么样。古华的《芙蓉镇》,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都写到落难右派的爱情,都写得很出彩,非常富有时代气息,爱情描写也非常成功。请您接着往下讲。
张志忠: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作为现代转型的后发民族,中国现代文学的建构,是有着参照的蓝图的。我将其概括为“别求新声于异邦,转益多师是汝师”。“别求新声于异邦”,是鲁迅所言,这正好合乎中国现代文学发端时期作家大多留学于海外的文化背景。“转益多师是汝师”则是说,中国现代文学的建构,具有广阔的文化视野,是面向世界文学的全方位开放,尤其是对于反抗强权、争取自由——个性自由和民族独立的文学的独具慧眼高度赞赏。
中国新文学的起源,基于积贫积弱、列强欺凌的窘迫,在文学的视野中,取法的对象却更为开阔,不仅有欧美发达国家,更有俄罗斯文学和东欧弱小民族国家的文学,弱小民族的受压迫与奋起抗争,都颇受青睐。林纾翻译《黑奴吁天录》,自谓是其译作中最悲哀者,其目的则是以黑奴之命运参照在美华工遭受奴役的悲惨遭遇,进而警醒国人的亡国灭种的危机意识。林纾在《〈黑奴吁天录〉跋》中强调说:“余与魏君同译是书,非巧于叙悲以博阅者无端之眼泪,特为奴之势逼及吾种,不能不为大众一号……今当变政之始,而吾书适成。人人既蠲弃故纸,勤求新学,则吾书虽俚浅,亦足为振作志气,爱国保种之一助。”波兰的显克微支,波思尼亚的穆拉淑微支,以及芬兰和丹麦作家的作品,都被周氏兄弟翻译为中文,收入《域外小说集》。如鲁迅所言,当时他们“注重的倒是在绍介,在翻译,而尤其注重于短篇,特别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为那时正盛行着排满论,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为同调的”(《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陈独秀发动文学革命,以补正近代以来政治革命之劳而无功,就是对标其时之欧洲的。20世纪初年,他就和苏曼殊合作翻译了雨果《悲惨世界》节译本,译作初名《惨社会》,自1903年10月8日起,隔日连载于《国民日日报》,后来又出版单行本。在《文学革命论》中,陈独秀指出,自文艺复兴以来,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有革命,伦理道德亦有革命,文学艺术,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进化。近代欧洲文明史,宜可谓之革命史。“欧洲文化,受赐于政治科学者固多,受赐于文学者亦不少。予爱卢梭、巴士特之法兰西,予尤爱虞哥、左喇之法兰西;予爱康德、赫克尔之德意志,予尤爱桂特郝、卜特曼之德意志;予爱倍根、达尔文之英吉利,予尤爱狄铿士、王尔德之英吉利。吾国文学豪杰之士,有自负为中国之虞哥、左喇、桂特郝、卜特曼、狄铿士、王尔德者乎?”(陈独秀:《文学革命论》)这和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对中国之摩罗诗人安在的呼唤如出一辙。郭沫若也讲过,他五四时期的诗歌创作有摹本不同的“惠特曼时期”“歌德时期”“泰戈尔时期”,因此形成其诗歌的不同风格。郭沫若也是歌德《浮士德》等诗作的最早翻译者之一。那个时候的人很可爱,会说我不同的时期创作,我的参照模仿学习的对象不同,这是一种调节,通过学习世界文学当中成功的作品,增强自己作品的文学性,提高自己作品的艺术水准。
文学之途,道阻且长。及时而广众的借鉴,是必然的选择。就像毛泽东所言,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文坛常青树王蒙曾说:“我们这一代中国作家中的许多人,特别是我自己,从不讳言苏联文学的影响。是爱伦堡的《谈谈作家的工作》在50年代初期诱引我走上写作之途。是安东诺夫的《第一个职务》与纳吉宾的《冬天的橡树》照耀着我的短篇小说创作。是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帮助我去挖掘新生活带来的新的精神世界之美。”(转引自李雪:《人性美的礼赞:王蒙与艾特玛托夫》,《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年1月22日)新时期的改革文学,有20世纪70年代苏联的改革文学的痕迹在里边,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就让人联想到前苏联作家维·李巴托夫《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李国文荣获第一届茅盾文学奖的作品《冬天里的春天》,当时被称为反思文学,它也有苏联文学的影响,伊凡·沙米亚金《多雪的冬天》,我专门写过一篇比较这两部小说的文章《冬·春·雪·雾——〈多雪的冬天〉与〈冬天里的春天〉之比较研究》(《当代文艺思潮》1984年第5期)。还有艾特玛托夫对中国作家的影响:路遥《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和田晓霞的爱情故事,就和他们读当时作为“供批判用”的黄皮书《白轮船》——艾特玛托夫最早介绍到中国的作品之一——爱不释手沉醉其中的过程密不可分。王安忆被认为是“海派传人”,但她近20年作品的逻辑建构受到阿加莎·克里斯蒂推理小说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另一位女作家残雪,除了源源不断的小说创作,还潜心解读卡夫卡,解读博尔赫斯,创作与阅读的密切互动,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随意漫谈,跳出高头讲章的窠臼,是一件快事。但还是要能够铺得开,收得拢,立得住。小结一下吧。我提出了“大时代的文学”的概念,用来描述古老中华进入现代转型期间的文学特性,强调其对现实的参与性、实践性功能,用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和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作为理论参照,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源。这只是一个初步的设想,有待于进一步学理化和在诸多命题上丰富扩展。
本文由王西强教授访谈、整理,经张志忠教授审定。
原刊《上海文化》2024年第12期

【作者简介】
张志忠,男,1953年生,中国当代文学史家,文学评论家,山东大学人文社科青岛研究院荣聘教授,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作者简介】
王西强,男,1978年生,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学者,文学翻译研究学者,塔里木大学人文学院讲座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主编:朱生坚
编辑:曹晓华
运维:任洁
制作:小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