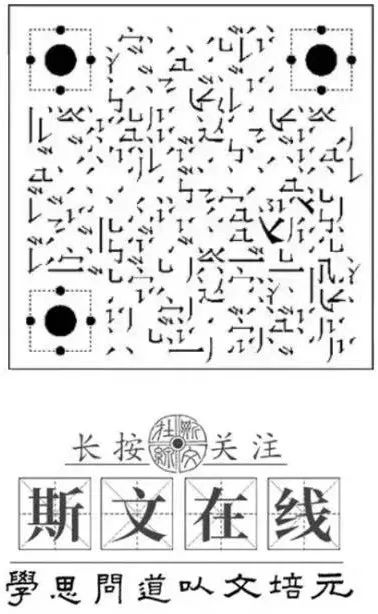在《刺客信条:起源》中,玩家在托勒密埃及的亚历山大、底比斯、孟菲斯等城市中随处可见古埃及的经典建筑“方尖碑”。方尖碑同时具备奉献给太阳神的宗教性、纪念法老文治武功的政治性以及视觉上的装饰性,是典型的黑格尔所谓的“象征性艺术”。而如巴塔耶所说,方尖碑的构筑是一种权威的展示,也显示出神性存在的永恒性——人类赋予方尖碑的象征意义会随着时代消解,而方尖碑却会始终留存下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大多数古埃及建筑都已经化为尘烟时,《刺客信条:起源》构建的虚拟空间中的“方尖碑”,也具备了永恒的神性:它们成为超脱实在的,满足想象和象征需要的“景观”。
随着图像技术的发展,电子游戏的“空间”越发与现实世界同步,游戏世界的构建同样需要处理空间和建筑的能力,相较于实在空间,电子游戏世界的空间是相对没有限制和没有界限的,没有“实体”的虚拟建筑理应更加指向创作意义上的“虚构”。埃森曼指出,建筑的“虚构性”分为表意上的再现、理性下的真实和历史性的永恒三种虚构特征,也如鲍德里亚所说,哪怕是实体的建筑,也是一种“超级写实主义”,是社会整体性虚构的一部分,而游戏空间中的建筑更是如此。由此,对游戏建筑的设计反而更加贴合我们的精神需要,更可以被当作一种艺术创作,需要“更加可观察,更加特别,更加可控”,也更加“戏剧化”。
在齐泽克看来,建筑空间具备符合“三界”理论的三重维度:实在界承担起实用需求与功利性,象征界负责建筑的意识形态意义,而想象界则指向与建筑进行交互的人的经验与感觉。而我们在电子游戏中遇到的建筑以及与这些虚拟建筑的互动关系,和在日常生活中的建筑空间体验是迥异的,这直观地指向齐泽克的“视差”概念:我们以不同身份、不同角度、不同状态去观察同一个“客体”所得到的对客体的印象之间必然存在差异,而当我们试图去弥合这些差异的时候,我们就在对比之下得到一个不存在的实在界;面对游走在历史题材、现实题材和未来科幻题材之间的电子游戏建筑和城市空间,由玩家、设计者、评论人和大众等多重视角构建的“视差”和其背后的意识形态阐释意义,在如今的赛博时代的重要性不亚于任何一座现实建筑:电子游戏中的城市空间,正是这个时代的永恒不朽的“方尖碑”景观。

方尖碑
一、电子游戏中的虚拟建筑和城市空间的特征和发展
游戏中的空间既是一种对“现实空间的再现”,同时却也是一种“再现的空间”,可以为了赛博个体的独特需求而构造自由的、全新的空间形态。虚拟建筑的构成元素是代码而非实体的砖瓦,因此设计者的美学企图会直接影响游戏建筑的面貌。然而,对游戏世界的构建毫无疑问要受到技术能力的限制:1992年发行的《重返德军总部3D》划时代地让电子游戏空间突破了平面的限制,建筑设计的理念从此进入电子游戏研发之中。虽然不需要参考现实世界的物理法则,但虚拟建筑的规模、精细程度和空间利用方式,在设计者的想象力和美学企图之外,也根本是由技术能力和成本所决定的,甚至技术越发展,“拟真”越发可能,反而加快了虚拟建筑与现实建筑的合流共通,进而导致对赛博空间使用限制的加强。如赛尔所言,建筑和城市作为公共的客体,起到的是隔断、分配本该无限的空间,并阻止已经流溢在空间里的对象自由移动的作用。《波斯王子:时之砂》等以构建城市空间为主要特色的游戏,被认为是真正依靠建筑设计来限制玩家行动、安排游戏节奏的典范。

《重返德军总部3D》
首先,在研发成本和技术限制之下,大多数电子游戏的空间设计和建筑设计,首要是为游戏的玩法和叙事服务的,设计者不会设计玩家无需进入的空间。而为了保证玩家不会自由移动到未曾开发的空间,游戏空间实际上存在一条“看不见的铁轨”,暗中引导玩家根据固定的线路来探索空间,实际上构建出一种德勒兹所谓的“光滑空间”。为了满足游戏玩法、任务设计和剧情需要而设计的虚拟建筑,具备游戏世界中的“实用性”,玩家所体验到的每一个空间、每一栋建筑都具有明确的功用,但这种赛博空间中的实用性,却偏离了住宿、储存等现实建筑的功用,游戏设计者怀着节约成本、遵循技术能力的功利性实用主义态度,却构造出大量纯粹以想象和象征为目的的虚拟建筑,只具备相应的美学、象征和意识形态意义,这正是某种设计者与玩家之间的“视差”所造成的结果。
其次,电子游戏空间可以塑造与现实空间迥然不同的陌生化空间,可以在一套全新的独属于赛博空间的“物理法则”中自由运行。电子游戏空间尤其适合对幻想类文学进行改编,来创造作家笔下的架空世界。不仅建筑可以突破物理法则限制并进行量与质的大幅夸张,满足在现实世界中难以实现的富有想象力的独特设计,更可以将游戏空间向能够赋予玩家挑战和探索可能性的功能性空间转变,彻底忽略文本和叙事中赋予相关空间的现实实用性。其中,“迷宫”是电子游戏空间设计的经典范例。设计需要玩家进行解谜的迷宫和“地牢”,是电子游戏的重要玩法,也是调节游戏节奏、难度、玩家游戏时间的“关卡设计”领域不可或缺的一环;然而在现实空间中,就算是警备森严的建筑都很少有“迷宫”或需要玩家进行“解谜”才能够前进的设计。
再次,在电子游戏中的建筑逐渐转向现实模拟风格后,玩家在游戏空间中与建筑的交互关系要比现实中的体验自由得多,这激发了玩家对虚拟建筑的想象界构建。查普曼总结过游戏中的现实模拟建筑的基本要求。这些要求结合起来从而实现游戏建筑模拟现实的理想:客观真实、没有意识形态偏见,并且能为玩家提供罗兰·巴特所谓的“真实效果”。而满足这些要求的游戏建筑,尤其是对历史上的经典建筑的复刻或复原,不仅满足了博物馆式的展览需求,更塑造了“活着的历史”,构建了生动鲜活的典型历史环境,从而让玩家能够沉浸式地参与其中,与建筑形成更多的交互关系,赋予玩家更多的互动可能,比如《刺客信条》系列中玩家可以探索金字塔内部,攀爬巴黎圣母院、埃菲尔铁塔等。这些的玩法,都是难以在现实旅游体验中实现的。迈克尔·尼采还提出概念“Machinima”,这个由“Machine”(机器,系统)与“Cinema”(电影)合成的单词,指的是玩家在游戏中自由的视角和互动方式,客观上类似于拍摄电影时随意和无限的摄影机位,任何一个玩家都可以在游戏中感受乃至录制出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影像体验记录,构建独一无二的与游戏空间的关系。
总之,面对被认为失去了海德格尔重视的艺术的“物性”的游戏虚拟建筑,在设计师看来,只要有技术能力支持,就同样具备甚至更加强调建筑学中对实用性、认识性、社交功用的重视。与现实建筑相同,虚拟建筑想表达的“意义和建筑结构是结合的”,都是在创造更加清晰的主体与空间的关系,填充没有限制和边界的赛博空间,并且讲述主体对空间的感受和理解。不过,玩家在游戏世界中体验到的建筑种类和空间类型,以及对游戏空间的体验交互方式的多元和丰富,造成了不可避免的“视差”以及随之而来的意识形态批判。一如《女神异闻录5》中的台词:“你如果想改变世界,你只需要改变看待世界的方法。”他们只需要在空间中发声,设计师就能立刻为其改变。
二、“还原”——在象征界渴望实在界:历史题材游戏
电子游戏中的虚拟建筑受到大众关注,普遍是因为游戏中对历史经典建筑以及著名旅游景点的还原与复刻。2019年巴黎圣母院发生火灾后,《刺客信条:大革命》中还原的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黎圣母院受到追捧,证明了游戏在还原实体和给玩家提供旅游体验上的成功。
然而《刺客信条:大革命》中的巴黎圣母院并没有做到精准还原,如今的历史题材游戏对历史建筑和历史现场的“拟真”也绝非完美。诚然,以育碧为代表的当代游戏公司在开发历史题材游戏时聘请历史专家顾问、借鉴先进考古成果已是惯例,如《刺客信条:起源》中对吉萨大金字塔的内部构造采用了考古学家、建筑师Jean-Pierre Houdin的前沿理论;然而,无论是设计师还是玩家都心知肚明,历史题材游戏中建筑的“还原”处于象征界而非实在界,字面意义上的纯粹的“还原”是不可能的。

《刺客信条:起源》中的金字塔内部场景
首先,再精细详尽的考古资料,也不可能还原建筑的所有细枝末节,更难以还原历史事件发生时的那种流动的、不断变幻的“现场性”。因此,设计师的设计必然存在大量“合理杜撰”的成分,而这些杜撰的“合理与否”,其实取决于被还原对象在文化上的象征意义,即是否符合玩家大众的符号化的刻板印象。如《刺客信条:奥德赛》中尽管有很多符合考古记录的彩色雕塑,但因为古希腊大理石白色雕塑的强烈象征性意味(温克尔曼所谓“高贵的单纯与肃穆的伟大”),玩家仍然可以在游戏空间中找到大量的以出土后面貌出现的白色雕塑。
其次,游戏本身的玩法和游戏性,依然是设计师的底层逻辑。历史题材游戏多以“开放世界”形式出现,对历史现场进行“拟真”所带来的虚拟旅游价值也成为一种玩法,因此玩家得到了很多对玩法和剧情并没有帮助的“非实用性”空间。然而当游戏性与“非实用性”发生冲突时,设计师依然会选择游戏性,而不是把“拟真”放在第一位。
再次,设计师主观的美学创作意愿不容忽视。尽管在拟真性和可玩性的双重限制下,赛博空间的自由度大打折扣,但设计者依旧可以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以自身的美学企图来影响对虚拟建筑的构建。后现代主义建筑师罗伯特·文丘里提出“Lessis Bore”,齐泽克也指出,正是大量的非功能性元素构成了建筑“宜居”这一本质功能,而很多游戏建筑的设计也已经成为象征符号的、对历史的浪漫想象,构建了大众对历史现场的普遍印象,回应了对游戏“还原”的诉求,也成为创作者发挥艺术才能的天然舞台。由此我们才在《刺客信条:奥德赛》中看到高达百米的宙斯神像、金羊毛迷宫乃至亚特兰蒂斯岛等非历史性的神话场景。
最后,也是从根本上展现出游戏无法达到实在界的一点,是游戏建筑尽管能提供现实旅行中无法得到的交互体验,但却无法提供一些个体对现实建筑的基础性心理体验。列斐伏尔指出,古罗马浴场是一个经典的“享乐式空间”,而这种对“具体乌托邦”的实用追求,最终促使建筑界开始迷恋于象征界中抽象的乌托邦;而《刺客信条:起源》中的浴场,在建筑面积和空间设计等方面都尽力还原了古罗马公共洗浴的盛况,但是相较于玩家在地图中快速穿梭的动态体验,游戏无法给玩家提供浴场内部参与者的静态体验。其一,游戏中的浴场相较于游戏中的广大宫殿和田野而言仍然是规模较小的建筑,玩家走上一圈不过数十秒,以游戏的第三人称视角也完全无法体验浴场内部空间曲径通幽、以小见大的视觉感受;其二,如今电子游戏的“具身化”还仅限于五官与部分肢体,“浴场”建筑首要的身体享乐功能是无法在游戏中实现的,然而要感受和理解古罗马浴场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底蕴,就需要身心一致的实践经验。《刺客信条:起源》特意安排了一场玩家身穿浴袍刺杀反派的关卡,然而这种体验与个体在浴场类建筑内所能获得的真实身体经验还是相去甚远。

《刺客信条:起源》中的昔兰尼浴场
古罗马浴场的例子意味着,历史题材游戏中对虚拟建筑的“还原”仍然是一种博物馆展览式的历史教育,仍然是旅游业衍生下的虚拟经验,其所能提供的新式交互功能也终究是为了观光体验服务的。完美还原历史现场、构建共时性的人与建筑的关系、探索当时历史环境下主体的感受和经验,对以还原历史建筑的象征性意义而非想象界意义的历史题材游戏来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历史题材游戏中的虚拟建筑,之所以要做出“还原”的面貌,是为了满足存在于象征界的“历史”这一对象持续的对实在界的渴望:对设计者来说,历史建筑的复原是使历史叙事更具说服力和沉浸感的重要推动力,由此传达出游戏作为一种新兴娱乐方式对历史和学术传统的尊重;而从玩家的角度,历史遗迹的复原给予玩家足不出户进行虚拟旅游的体验,满足玩家的享乐和社交需求,更促进了游玩时对叙事的代入感。无论从哪个角度,历史题材游戏的建筑都是一个试图从象征界走向实在界的隐喻,所有参与主体都沉浸在一个历史理性主义的意识形态幻想里,渴望以一种明确的“观念”达到实在的切实境地,渴望一个不可能完成的“还原”实体,渴望一个永远不会出现的他者。
三、“拟真”——从实在界逃离到想象界:现实题材游戏
现实题材游戏为游戏图像技术提供了基础的模仿对象:我们所生活的现实。图像引擎中的建筑材质、植被贴图、空间规划,都直接取材于我们生活的城市,在虚拟世界中找寻熟悉的感受,以自我对实在界的感知来构建一个“伪实在界”。而电子游戏从线性闯关、“箱庭式”设计逐渐转向大规模自由探索开放世界模式的趋势,把完全“拟真”一座现代城市的任务,交到了设计师面前。在开放世界“拟真”的需求下,现实题材电子游戏的城市地图设计规划,与建筑师设计现实城市别无二致。
知名建筑师库哈斯指出,大都市的构建是可识别的精神建构的结果,参与者都怀着对都市精神的意识形态共识。但这种基础共识并不能影响城市的具体规划,城市各个区域的功能和规划充满了自由发展的不确定性,功能不断变化与重组,宛若一块块可以联络但互不交接的“飞地”和“岛屿”,最终形成类似“大苹果”(纽约昵称)这样动态发展的大都市。所以构建大都市的设计不可能是教条的,最初的区域规划都会在参与者和市民的选择与行动中得到修正和发展。然而,库哈斯的大都市设计理论对现实题材游戏的城市构建来说,却是不得不反其道而行之的:“拟真”的需求本质是一种从实在界逃离到想象界的逃逸尝试,而这种逃逸尝试的本质是“游牧性”的,它并不支持、也不提供一种城市机器的“生成”性。
从成本和技术限制考虑,类似《侠盗猎车手》等都市题材游戏,也倾向于像历史题材游戏一样,直接复制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大都市。而且相较于不可避免地要进行象征性虚构的历史题材游戏,现实题材游戏中的城市空间则有高度还原的可行性。《侠盗猎车手》历代作品的城市地图以迈阿密、洛杉矶、旧金山、拉斯维加斯、纽约等大都市为设计原型,《看门狗》系列则以芝加哥、旧金山、伦敦为舞台,都赋予了游戏强烈的真实感和代入感。依靠现实中经过历史考验和严谨的“生成”过程的城市规划体系,游戏中的城市对空间的分配和规划都是高度合理的,这也给以“闲逛”为主的、不与NPC(非玩家角色)产生深度交流的、宛若本雅明笔下的“游荡者”的玩家们提供了真实而疏离的现代性都市体验。
然而,在短暂的惊喜之后,玩家依旧渴望关卡设计和引人入胜的游戏性;但显然,和历史题材游戏的“还原”问题一样,现实题材游戏的拟真需求与游戏性同样存在矛盾。游戏性和关卡设计理论会将虚拟城市空间进行更加明确、直观的区域划分和功能分配,这一在现实世界中明确指向阶级与种族、已然在城市机器的生成和建筑师主动的意识形态选择下开始模糊的区域界限,在电子游戏的虚拟城市空间中依旧非常鲜明。玩家需要知道各个区域的明确功能来规划自己的行动路线,甚至,部分玩家会以此为标准来评判游戏设计的用心与合理程度,他们对不同阶级、不同种族的NPC的生活环境和生活习惯加以关注,并要求其符合玩家对阶级和城市区域划分的刻板印象,实现他们的“想象”。由此,如今的现实题材游戏里大多数的现代城市空间,其与现实都市最根本的差异并不在于未曾拟真的部分,而在于这座城市整体的“生命力”。如今的虚拟城市还无法像现实世界的大都市一样,是一个自在的、自为的、始终在生产和生成的“活”的城市机器,而更像是在“开放世界”面纱之下铺满了无数“隐形轨道”的“功能性箱庭”的集合。
也就是说,大多数现实题材游戏中看似与现实世界别无二致的虚拟城市空间,实际上更多是虚拟的“游乐场”,是基于玩家对实在界的厌弃和对实在界的欲望想象而构建的可供逃离的想象界。对玩家来说,拟真绝非游玩的第一目的,是可以被游戏性所取代的。当初始的“震颤”消退之后,复杂的城市地形和空间分配甚至成为玩家游玩的障碍,建筑再次成为阻碍个体自由移动的、对个体进行规训的工具。当游戏中出现因为地形高低、建筑层级设计原因而需要认真研究地图乃至解谜才可以到达目的地的时候,这种根植于当代城市空间的“真实性”,却成为玩家厌恶和批判的重点——“可见而不可得”的体验尽管符合城市空间的特质,却违背了玩家对自由移动和自主游玩的渴求。在使用“游戏修改器”时,“穿墙”或“自由行动”模式深受玩家青睐,这不得不说是游戏城市空间设计的内在自反性。
本雅明在讨论20世纪的现代城市空间时指出,19世纪的住宅理念是把住宅当成居住者的保护壳,是居住者身体的延伸,而20世纪的理念则是将建筑与人的身体进行剥离,人们“居住的屋子”应该取代“住宅”,建筑的物质性和所有权的特质开始被用途和象征意义所取代,市民开始成为与城市空间产生疏离感的局外人和“游荡者”。这看似是现代性的可悲之处,但本雅明却对其寄托了超现实主义的期待,期待这种城市空间的革命性转变所带来的迷醉的美学感受可以激发一种实在的革命力量。本雅明对现代城市空间的理念是符合游戏玩家对待现实题材游戏中的城市空间的态度的。玩家渴望自由的本性促使他们成为虚拟城市空间中的闲逛者,而是否需要构建一个更加富有生机的、能够自我生成的、让参与者有更深层次的生活体验的虚拟城市空间,还存在疑虑,这种革命性对大多数人来说都过于激进,他们认为虚拟城市空间目前还是一种玩家从实在界逃离到想象界的手段,因此这种想象界必须保持足够的想象空间,而不是成为一种实在界本身之“不可得”的再次复制。
四、“证成”——以想象界构建象征界:未来科幻题材游戏
在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游戏中,设计师对游戏城市空间的态度时刻受到实在界的重力拖累,而看似能够破除这种实在界的不可能性的城市空间,则是未来科幻题材游戏所构筑的未来世界。
创造一座“未来都市”对建筑师来说充满吸引力。著名建筑师柯布西耶认为,建筑是更高规格的生活意义的革命,当建筑先行一步的时候,与建筑产生关系的个体必然会导向全新的生活方式。然而从现实世界的实践看来,现代建筑所构建的“乌托邦”大多数还是在运行的过程中难以摆脱时代的限制,现代建筑功能性与形式的分离引向齐泽克所说的现代建筑的精英主义本质——它们作为精英艺术受到资本主义庇护的现实,阻碍了其在创作动机上对既有结构的反抗性。在埃森曼看来,现代建筑是“人工的过去和没有未来的当下”,是结构主义意义上的可阐释的文本,而这样的建筑在鲍德里亚看来是无法构建真正意义上的“后现代”的,建筑的“达达主义”是近乎不可能实现的。
但是,在未来科幻题材的游戏虚拟空间中,对现代建筑的所有失望似乎都有被拯救的机会:在一个“未来世界”里,未来建筑只需要满足叙事和想象力。由此,很多在现实题材游戏中的城市规划问题迎刃而解,因为我们不生活在未来,对未来城市和未来主义建筑的设计不需要在意个体感受——都不以个体生活的享乐性为主导;对“高科技,低生活”的态度各异,但现状相同。未来科幻题材游戏中的建筑和城市空间,是从想象界出发指向象征界的,其高度的意识形态特征仿佛中世纪的神学建筑艺术,一切的设计和阐释都从意识形态的象征意义出发。任何不符合当代城市空间规划准则的设计在美学和意识形态的允许下都是合理的,而在虚拟的非物质性的庇护下,未来题材游戏中的城市建筑,均以叙事中的未来政治实体的观念传达为设计核心,游戏中的未来都市从本质上不啻于一个个古老的神殿、神庙、教堂——它们是在本质上最贴近纯粹想象和象征的“方尖碑”景观,是德里达笔下的“事件建筑”。
德里达指出,现实世界的建筑首先要满足四个公设:首要目的是让人栖居;有中心和层级,构建等级体系;本质为人服务;最终依赖于艺术。而“事件建筑”虽然不曾破坏这四个公设,却提供了使这四个本来按照既定结构组合起来的预设无限地“折叠”起来的“疯狂物”,这正是玩家在进入未来科幻题材游戏中所谓的未来都市时所最期待看到的——一种独属于未来的,通过建筑和城市规划而达成的“疯狂”。这种疯狂并没有剥夺空间中个体自由移动和生活的权利,而只是放大了空间的象征意义,使其作为“神迹”和概念的实体化,明确地宣示一种意识形态的强盛。虚拟建筑尤其满足了“事件性”,对于所有被未来风格的都市所“震颤”的玩家来说,这样的心理感受是一种刹那的相遇,是一瞬间的既有价值观的碎裂,但绝非一种延续性的常态。
由此,对未来都市空间的设计,是一种既有价值观的“证成”运动:对未来都市的明确设计自我证明了未来都市的可行性,在游戏虚拟环境之中,未来都市的构建纯粹是一种理想国式的“沙盘推演”。未来主义建筑需要展示人类对未来的想象,这种探索是从实在界出发的;而电子游戏中的未来建筑则更加直接,毫无拘束,与实在界几乎无关,而与象征界联系密切,本质上突出了科幻作品古典主义和英雄史诗的一面。因此,玩家身处其中可以明确感受到环境的叙事功能,因为空间始终在向个体经验展示权力。个体可以存在但不可能归属于此,因为未来都市是为“神”而非为“人”修建的。无论是在眼花缭乱的霓虹灯管中的赛博朋克都市(《赛博朋克2077》),被差分机器、钟表部件填充的蒸汽朋克都市(《空之轨迹》系列),还是雪白纯粹、以高度鲜明的几何形式存在的未来主义都市(《镜之边缘》《星空》等),设计师对虚拟的未来生活所进行的虚拟建筑空间规划,始终是一场通往象征界的符号操演游戏,沦为“拟像”,是空间与非空间的二元对立,为玩家提供一种得以触及世界真实性和本源的错觉。

《镜之边缘》城市图景
电子游戏中对未来都市的构建可以说是一种德勒兹与伽塔利笔下的“辖域化”:在建筑物没建起来时,每个人都在不同的“平面”上建造了它;当建筑建成的一刻,就意味着对空间划定了领土,建立了场域——建筑“插入”了我们的生活,并从此对生活进行建构与塑造。吊诡的是,最为自由而无限制的、最符合赛博空间初衷的虚拟未来城市构建,却浸透了灌输和压迫性质的意识形态的血泪,当设计者得以将艺术创作和自我表达放在首位时,他们以“证成”自我而非“还原”“拟真”作为主要动机,得以沉溺在想象界,并在象征界大胆地玩弄起符号游戏。脱离了实在界的重力和凝视之后,我们得到的却是“方尖碑”式“非人”的永恒实在,是一种高强度的、神学的、意识形态上的确定性,而非关切个体经验和独特感知的多元化状态。我们的“未来”想象始终通往一种在我们理性上其实不希望达到的未来,永远象征着“反未来”——这也就意味着,实在界在看似远离我们的同时,也在向我们投来嘲笑的目光:我们将始终被包裹在这种实在界投下的不可能性的阴影之中。
五、结语:游戏建筑作为“方尖碑”景观的意识形态超越性
回到《刺客信条:起源》的黑色大理石方尖碑面前,我们攀爬而上,立在不可能的支点上,俯瞰这电子游戏世界创造的古埃及历史现场:此时无论是游戏的关卡进度,还是眼前的古埃及是否拟真都并不重要,对个体来说,这是堪比参观现实中的古罗马浴场的“享乐”瞬间。我们对游戏虚拟建筑和城市空间的意识形态批判可以走向完全不同的路径。如齐泽克所言,建筑是一种“未知的已知”——我们对具体的批判内容无从得知,但我们对最终的结果心知肚明:那就是,建筑可以用来表达平等,也可以用来表达不平等,可以用来表达希望,也可以用来表达绝望,对同一座建筑的体验,哪怕是同样的个体经验,在空间内部和外部的“视差”始终都是不可通约的,对建筑的意识形态批判永远会产生一种内部性的矛盾,从而导致从建筑的整体性上来看,对其进行单一的意识形态批判会失去意义。
那么,在本应没有限制的赛博虚拟空间里的游戏城市空间,也许理应走在现实建筑之前,以其“事件建筑”的特性和在想象界、象征界的“方尖碑”式永恒性景观,寻找一种“享乐主义”的、短暂但又始终存在的意识形态超越性:属于个体经验的所谓“表皮和建筑之间的间性空间”,实际上在虚拟空间中随处可见,可随意占有,也可随意“放置”。对玩家来说,在感受大型3D角色扮演游戏为我们构建的“戴着镣铐跳舞”的城市空间的同时,玩家还有很多自行处理虚拟空间的选择:如《星际争霸》《魔兽争霸》之类的即时战略游戏配备的“地图编辑器”,以及《我的世界》《模拟城市》等“沙盒”类模拟游戏等。包括在《文明》《群星》等从广义角度探索虚拟空间的经营游戏里,我们可以应和露丝·伊瑞格瑞的期待,将我们的虚拟空间构建得更加富有诗意:在她的建筑理论中,承担不同区域之间联通功能的“桥梁”和“外壳”,是对抗建筑中的盲点和深渊的“天使性”存在。
本文证实了一种对电子游戏中的建筑和城市空间进行意识形态批判的可能性,但是,对于这种可能性,从赛博虚拟空间的积极意义上,在实在界永不可能达到的前提下,正如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所说,“最好的遵循之道与其说是照办,不如去打破”。
(本文原刊于《上海文化》2025年2月号,注释从略)

【作者简介】
孔德罡,1992年6月生于南京,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讲师,南京大学文艺学博士,南国剧社艺术总监。编剧、导演、剧评人,澎湃新闻·思想市场「现代神话学」专栏作家、江苏省网络作家协会理事。著有评论文集《现代神话修辞术》。
主要研究方向为20世纪下半叶后的西方美学文艺理论,戏剧、影视、游戏和新媒介艺术批评,在中文核心期刊和各大报刊发表论文多篇、评论和理论文章近百篇。
编剧、导演创作舞台作品近20部,累计社会各地公演二百九十余场,代表作《红楼薄命司》《超越星辰》《Yoko Yoko花神咖啡馆》,《中文系:一部赛博悲悼剧》曾获江苏省紫金文化艺术节小剧场单元最佳编剧奖。作品曾入围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杭州国际戏剧节、天津青年艺术节、斯芬克斯元宇宙戏剧节、紫金文化艺术节、南京戏剧节等。
【新刊目录】
《上海文化》(文化研究版)
2025年第2期
专 题 中国式现代化与上海文化
孙 超 中西现代性的协商—竞争:近代小说转变的重要驱动
专 题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田兆元 张 哲 从舶来品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上海绒绣的艺术涵化转向
访 谈
安靖如 吕剑兰 中国哲学在美国的译介与传播
理 论
路 程 论埃里希·奥尔巴赫与历史主义传统
文 学
孙立武 从《高兴》到《河山传》:城乡书写的内在伦理与美学新变
汪一辰 城乡叙事视野下的“城市时空体”——《人生》影视改编中的“上海”及其诗学阐释
徐雪涛 新世纪城乡叙事中的“离去与再归来”——以孙频创作为中心的考察
文 化
杨诗影 刘 舸 生活在别处:“风景的发现”与旅游景观的文化重塑
韩江枫 景观化演讲的文化逻辑与美学反思
孔德罡 想象和象征的景观:电子游戏城市空间的视差性批判
文 艺
黄一迁 从安于接受到相生相长——观众文化自觉、自信和海派艺术展览生态
张桂丹 风景的“未思”——朱利安风景画与山水画对比研究
笔 记
程 鹏 从都市民俗学到现代民俗学:上海都市民俗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编后记
英文目录
封二 周碧初《古镇水乡》
封三 新书推荐
《上海文化》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扩展版)来源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引文数据库来源刊
社长:徐锦江
常务副社长:孙甘露
主编:吴亮
执行主编:郑崇选
副主编:张定浩
编辑部主任:朱生坚
编辑:木叶、黄德海、 贾艳艳、王韧、金方廷、孙页
《上海文化》(文化研究版)
主办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地址:上海市中山西路1610号2号楼928室
邮编:200235
电话:021-64280382
电子邮箱:shwh@sass.org.cn
邮发代号:4-888
出版日期:双月20日
主编:朱生坚
编辑:张晴柔
运维:任洁
制作:小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