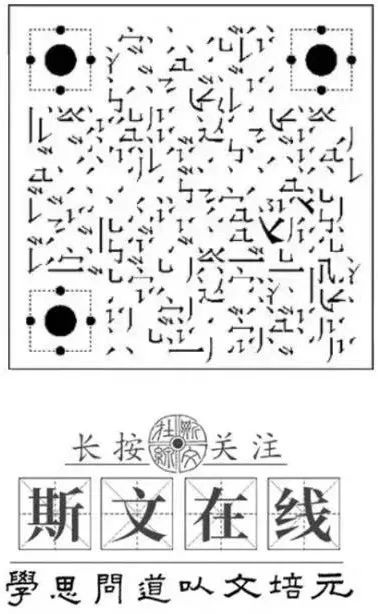一
虽然大小传统之说来源于西方,但自此概念引入中国以来,前贤时哲就中国本土的大小传统之说贡献了不少精彩观点。 如李泽厚先生认为,由于“巫术礼仪”在周初的彻底分化,逐步形成了中国的大小传统,“一方面,发展为巫、祝、卜、史的专业职官,其后逐步流入民间,形成小传统。后世则与道教合流,成为各种民间大小宗教和迷信。另一方面,应该说是主要方面,则是由周公‘制礼作乐’即理性化的体制建树,将天人合一、政教合一的‘巫’的根本特质,制度化地保存延续下来,成为中国文化大传统的核心,而不同于西方由巫术礼仪走向宗教和科学的分途”。李零先生则指出,自秦汉以降,中国本土文化分为两大系统,即儒家文化和道教文化,“儒家文化不仅以保存和阐扬诗书礼乐为职任,还杂糅进刑名法术,常扮演着官方意识形态的角色,与上层政治紧密结合;而道教文化是以数术方技之学为知识体系,阴阳家和道家为哲学表达,民间信仰为社会基础,结合三者而形成,在民间有莫大势力”。许倬云先生也提出过类似的观点,认为虽然儒家长期以来占据着中国文化的权威,但在中国民间尤其是底层,儒家的权威性比较淡薄,“在中国的民间,或者更恰当地说,有些处于文化精英层次的人物,一只脚踩在儒家,一只脚踩在民间,他们就会尝试如何整合这些不同的信仰为一个系统”。
需要注意的是,学界以往常常只关注从百家争鸣到儒家为尊的历史文化中的大传统,而忽略了以数术方技为代表的各种实用性为主的文化小传统,故而常常把中国文化理解为一种纯人文主义的文化,“但近年来随着考古发现的增多,我们日益感觉其片面。在我们看来,中国文化还有着另外一条线索,即以数术方技为代表,上承原始思维,下启阴阳家和道家,以及道教文化的线索”——换言之,就是对小传统中不同于“纯人文主义的文化”的这一特点和悠久的历史,我们不能视而不见。

诚然,如有学者所言,“不同文化中的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的关系,很难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且大小传统总是处于一种相互对应的关系之中,这种关系又常常伴随着时空的变化而变化。总体而言,我国的大小传统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并非截然隔绝,而是浑融互动的,并慢慢形成了我国复杂、包容、独特的神人一体、天人一体、生死一体的文化景观;它与西方基督教为主体的文化景观不同,它不会将生、死截为两段,也不会将神、人分置两端,更不会将圣、俗认作二心,它将这一切统统融作一体,当作一事,认为这个世界既是世俗的,也可以神圣的,“神圣在世俗之中,世俗有神圣的庇护”,人们在这日常中便能够化世俗为神圣、融神圣于生活,从而成就自己——这便是中国本土大小文化传统中最具特色、最有价值、最值得称道的地方。
概言之,笔者赞成李泽厚、李零先生之说,在中国文化的历史中始终有着两条线索流传,一者显耀而占据主流(可谓之文化大传统),一者隐蔽而遍布四方(可谓之文化小传统)。文化大传统主要以儒家为代表,而文化小传统则主要以各种民间信仰、数术方技为代表——如有学者就认为:“儒学是精英文化的大传统,术数则属于大众文化的小传统。”尤其要注意到,就中国本土文化长期的实践与发展而言,小传统与术数文化密不可分。数术文化在秦汉之后有着极深厚的民间基础,对普通民众影响深远,它体现出一种极为典范的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离开了术数文化,小传统也将蹈于空无。故而本文此后谈论文化小传统时,将聚焦于术数文化一隅。
有关术数文化的研究,不少学者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对于术数文化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关系问题,虽有部分学者给予了关注,但总体而言,此类研究并不多。故而本文拟进一步探讨在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术数文化作为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元素多元、影响深远的文化小传统,如何在全球文化交流和当代文化建设的实际中发挥应有作用,为我国的主流价值认同、科技与人文协同发展、构建中华文化共同体等方面提供有益的借鉴。
二
关于术数文化的相关问题,笔者已有相关论述, 此处仅就一些重点再略作分析。术数的定义至今聚讼纷纭,未有一个权威的答案。《四库全书总目》认为:“术数之兴,多在秦汉以后,要其旨,不出乎阴阳五行、生克制化,实皆《易》之支派,傅以杂说耳……今参验古书,旁稽近法,析而别之者三,曰相宅相墓,曰占卜,曰命书相书,并而合之者一,曰阴阳五行。”可见,所谓“术数”是以传统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通过一定的技术方法来预测未来的祸福凶吉,大致可分为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等三类,并合而为一统称为“阴阳五行”。不过,由《汉书·艺文志》“术数略”可知,当时的“术数”与后世以《易》为主的术数的关系并不紧密,反倒是与巫术、杂家的关系更加紧密些。此外,它所说的术数与道教兴起之前的术数也未必完全相同;道教兴起之后将“术”和“技”融为一炉,再结合了道家、阴阳家、杂家等诸家思想,才形成了后世“术数”体系。
关于术数的起源,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起源观认为,术数来源于巫术,其历史可以追溯到上古巫术盛行之时,其与巫术的关系随时代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在原始社会,“术数知识体系从属于巫知识体系,术数是从巫术中起源的,作为术数本质的占卜功能,本来就是巫术体系中的一部分, ‘巫咸作筮’反映的就是巫术和术数之间的渊源关系”。但此种关系随着时代的发展有了不同的变化,术数慢慢从巫术中分化出来,至唐宋时,巫为了继续发展开始“大批的转向数术,成为术数的附庸。有一部分则转向道教系统”。有学者认为,巫术与术数的相同之处在于以“事神”为基本特征,最大的区别在于巫更多地表现为一种“非理性的愚昧行为”,而“术数的法与术,虽然有不少的神秘行为,但也有不少的理性认识和行为荟萃其中,如阴阳、五行理论和天数、历术。这种差异,是术数摆脱巫术的重要原因,也是秦汉以后巫附属于术数的原因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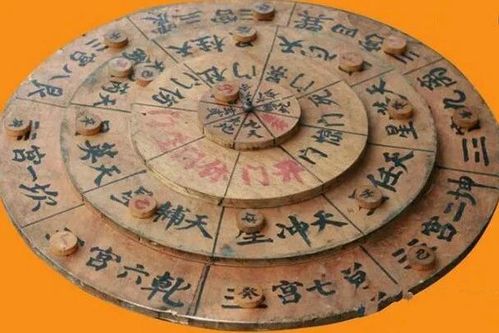
另有学者认为,我国术数应起源于周朝。西周之时出现了一种新的天道观,“在这种天道观下,原先自由任性或具有道德审判力的神,转变为受到数约束的神,神的人格特点,让位于自然特点。数成为决定一切的力量,天命观由此出现,数术从此兴起”。
第二种起源观认为,要以术数理论根基“阴阳五行”之说来判断其起源。持这一种观点的人认为,尽管巫术与术数之间有着某些关系,但是否是“术数”,要以它是否建立在阴阳五行的理论基础之上来判断。“术数应专指以预测吉凶为主的方术,且其理论内核为阴阳五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巫与术数的区别是,巫往往寻求神秘力量改变命运与自然,但术数一般只测算不改”,“那些产生于《周易》之前,不以阴阳五行的思辨为基础,而是建立在神秘力量及语言上的巫祝、汉代的谶纬等,便不能算是术数了”。如果以此为标准,则我国术数的起源确为“秦汉以降”了。
三
至于传统术数的理论体系,可从两方面来看待:其一,如果说术数与巫术有着紧密关系,那么其应当就与巫术的理论近似;其二,如果说术数是产生于“秦汉以降”,虽然其思想与巫性思维仍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更直接的则与阴阳五行学说紧密相关。
从其传统来看,西方的巫术概念来自两大传统,“一个是犹太-基督教的传统,另一个是希腊的传统”。在第一个传统中,“《圣经》把各种偶像描述为具有神秘术力量者,异教崇拜是为了安抚它们和从它们那里得到好处,它把这些态度与崇拜仪式贬斥为巫术和妖术。这是西方巫术概念的一股源流”。在第二个传统中,“希腊哲学家和‘科学’的先驱者并不把‘巫术’作为与他们的知识对立或不相容的东西加以排除。对于希腊人来说,‘自然的神性’是不言而喻的,神性原则遍及万物”。无论是从第一种传统还是第二种传统,可以发现它们都承认巫术的神秘性(“具有神秘术力量者”)和万物有灵(“神性原则遍及万物”)等特点。
从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来看,到秦汉之后,“原始巫体系分化为巫、史、卜、祝等门类,专职的巫术范围缩小,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巫术和数术分道扬镳”; “巫术时代以鬼神信仰为特征,数术时代以对数的信仰为特征,这是数术与巫术的根本差别所在。”这种对“数的信仰”,便落实在以阴阳五行理论为基础的一整套思维逻辑和运算方式之上。
阴阳五行理论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它对中国人的思想影响至深。顾颉刚先生曾讲:“五行,是中国人的思想律,是中国人对于宇宙系统的信仰;二千余年来,它有极强固的势力。”侯外庐先生则讲:“如果不理解阴阳五行学派的世界观、知识论和逻辑学,则对于自汉以下的儒家哲学也不能有充分的理解。”庞朴先生说:“一般都承认,‘五四’以前的中国固有文化,是以阴阳五行作为骨架的。阴阳消长、五行生克,迷漫于意识的各个领域,深嵌到生活的一切方面。如果不明白阴阳五行图式,几乎就无法理解中国的文化体系。”这都是肯定和强调阴阳五行理论在中国思想体系中的重要性。
阴阳五行理论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一般认为,其源头至少可追溯到商末周初,不过它的定型和成熟及发生广泛的影响,则要到战国后期至西汉中期。刘安的《淮南子》和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完成,标志着阴阳五行思想基本定型和成熟。在早期的阴阳家那里,由于“天时地利”多为外在于人的独立呈现,因此大多不会被“人”所改变或因“人”而自行改变,它具有较强的先期性、既定性。到了董仲舒这里,则突破了阴阳家认为“天时地利”不可改变的既定观念,给阴阳五行注入了积极能动的因素。李泽厚先生认为董仲舒这种对阴阳家的突破和改造,“用儒家仁义学说和积极作为的观念改变了阴阳家使人处于过分拘谨服从的被动状况”,“董仲舒的‘天’既有自然性,又有道德性,又有神学性,还有情感性”。这种改造可以从后世术数家重视“人”的力量、相信可以通过主动的努力改变不利的境遇等方面体现出来。如术数家常常提及的“福由己造”等观点,正是这种改变“人处于过分拘谨服从的被动状况”的体现。
笔者认为,基于阴阳五行学说之上的传统术数文化的关键点有三:一是以天人感应作为主要的理论根据,二是以阴阳五行、生克制化作为主要的推演逻辑和运算原则,三是以趋吉避凶、择福驱祸为主要目的。它有一整套完善的、内在自洽的逻辑:它认为天人同类,人乃天之所生,是万物之灵,甚或是天在世间的代表,故而能够与天感应,所谓“天之与人,有以相通”。天人相感需要通过一定的中介物体现出来,这种中介物所显示的吉凶情况,关系到人的吉凶祸福。人要获得吉福、避免凶祸,就需要通过特定的方法对这种中介物进行分析、判断。这种分析和判断,就需要借助术数的方法。另外,如果要化凶为吉或继续保持吉福,就需要人自身的努力精进,尤其是德行上的修持,这就是“人之精诚,感化于天”。如此一来,这就把外在的自然现象与社会道德的要求联系了起来,同时也把作为自然的人和作为社会的人在“吉凶祸福既是‘天设’又是‘人定’”这一层面上统一起来。

要言之,中国传统术数与中国的阴阳五行学说紧密相关。它自有一套完善的叙事逻辑和方法,是古代中国人追问人生意义、世界意义的一种路径;它呈现为一种杂糅、包容、边界不清的文化图示,最终又集聚在一种“情感性的群体人际的和谐关系”的特征上。它隐藏着中国人的某些思维方式、生活习俗和审美趣味,“体用不二、天人合一、情理交融、主客同构,这就是中国的传统精神,它即是所谓中国的智慧”。 它的生命力极为顽强,常常与各种具有地方特色的类宗教的民俗文化样式交融互补,至今草蛇灰线,绵绵不绝。若看不到这一点,仅是简单粗暴地贴以“不科学”“非理性”等标签对它加以全盘否定,则是片面的、不客观的。
四
在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文化大传统的重要作用已得到全社会的认同和重视,但对作为小传统的术数文化的重视程度则远远不够。从全球文化交流和当代文化建设的实际来看,它至少可以为我国的主流社会价值认同、科技与人文协同发展、构建中华文化共同体、对伦理道德的规范和引导等方面,都能提供许多有益的借鉴:
其一,术数文化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与辩证唯物主义有着近似的思想渊源。例如阴阳五行的思想,充分体现了中国特有的辨证思想:在其看来,某一单独的元素并不能独自显现出它的特征和作用,它必须与其他元素一起,才能显现出特征和作用;同时,某一事物也必须在与其他事物的互动中才能达到一种动态和谐。这种基于阴阳五行的辨证思想,也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类似理念,“中国的‘金木水火土’五行不同于希腊、印度的‘地水火风’四元素”,“中国古代的辩证法,更重视的是矛盾对立之间的渗透、互补(阴阳)和自行调节以保持整个机体、结构的动态的平衡稳定,它强调的孤阴不生、独阳不长;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中医理论便突出表现了这一特征,而不是如波斯哲学强调的光暗排斥、希腊哲学强调的斗争成毁”。
此外,术数文化的理论体系虽然并不排斥鬼神之说,但其根本仍旧在于重视对世界的观察、总结、推演,认为世界的规律、人的命运是可以通过探索而认知的;人不仅仅受制于“天命”,也反作用于“天命”;人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变不利的处境,建立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它虽然大谈“天命”,但重要的“不是对‘天命’或‘必然’的屈从或退让。而事在人为,可和‘命运’搏斗,虽败犹荣”,“既强调人的主观努力,同时也尊重偶然性的存在”。如传统地理术强调“阴地好不如心地好”,便是把单纯的客观环境决定论,转化为具有主观意义的社会道德决定论。这种转化背后,实为对主观能动性的强调。
其二,术数文化体现了我国古代科技与人文相融互通、浑然一体的思维模式,对当今科技与人文协同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思路。有学者指出,中国传统实用知识的思想架构是数理术三重互动关系,“数、理、术架构是中国古代文化建构与发展的一条脉络,例如,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与数、理、术架构起来的文化知识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我国古人的意识中并没有科技与人文学科的分野,在其庞大而混沌的学科体系中,算术、音乐、历法、天文、地理、物候、医学、军事、文学、化学等学科浑然一体。就当今称之为科技的这一面来看,它在中国古代知识体系中,正好对应了术数文化。这个术数文化“不仅囊括了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的所有‘基础学科’,而且还影响到农艺学、工艺学和军事技术的发展”。
现代学术体系的建立和学科的分野,是建立在西方启蒙运动与现代科技发展背景下的。这种建立和划分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但并不意味着它的绝对性和永恒性。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划分也越来越呈现出它的局限,如学科内部的封闭、学科之间的壁垒以及面对时代变化的滞后性,等等。就知识体系来讲,术数文化虽然对应科技领域的知识比较多,但它的思维方式、内容体系等饱含着充沛的人文思想、情感关怀。在这一传统中,人文与科技、情感与理性、知识与信仰、清晰与混沌,皆不可截然二分,“如果我们硬是要把数术方技之学的这两方面鲜血淋漓地割裂开来,一半归于科学技术,一半归于迷信,那不仅在材料取舍上将有许多不便,而且还会破坏对学术传统的整体理解。”术数文化的内在思想,正吻合了近年来兴起的交叉学科、融合学科的发展逻辑。
再从科技的实践来看,量子物理、生物科技、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突破性发现,都必然对人类的未来产生巨大影响。如果人类的知识领域仅是科技一枝独大,缺乏人文关怀的浸润,那么人类的未来必值得担忧。科技一枝独大最大的问题,便是容易产生“人无所不能”的幻觉,陷入以人为中心、以效益为主导的生产创造逻辑,从而破坏自然生态;遭到破坏的大自然又必然会反噬人类。西方近代工业化以来的历史发展早已证实了这点。因此,借鉴中国术数文化中科技与人文相融互通、浑然一体的思想,弥合科技与人文截然二分的弊端,提倡新型的、整体的科技人文协同发展的道路实属必要。
其三,作为复合多样的文化小传统的术数文化,有利于促进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推动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建构。费孝通先生指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对中国人认同的历史文化基础的解释,“‘多元’是指中国有着众多的民族、地方和民间文化小传统,‘一体’是说中国又有一个为大家认同的历史文化大传统。复数的小传统反映中国文化多元的现实……单数的大传统反映统一的要求……中国文化指的就是这样一个由单数大传统和复数小传统构成的相互依存的体系”。费先生此说,指出了小传统极其重要的一面:如果缺乏小传统“多元”的支持,大传统“一体”的根基也将大大动摇;小传统并不是将大传统分裂为各个不同的文化元素,相反,它是将各个不同的文化元素组合为一体,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文化小传统既是中华文化各元素的黏合剂,同时也是中华文化构成的重要材质。
另外,还要看到在中华文化的内部,大传统是凝聚主流社会的重要力量,它尤其可以促成中上层精英阶层形成相对共识;小传统则是凝聚民间大众的重要力量,它可以在底层民众中形成相对共识。它们都对国人伦理道德起着规范和引导作用。尤其是术数文化,它在民间社会有着类似于李泽厚先生所讲的“宗教性道德”的意义,它不是以法律等方式来强迫人们服从、遵循于社会的制度和秩序,而是让人们在精神层面自觉地服从、遵循某些制度和秩序。“现代社会性道德以理性的、有条件的、相互报偿的个人权利为基础,传统的宗教性道德则经常以情感的、无条件的、非互相报偿的责任义务为特征。”在这种现实情况之下,大小传统相互合作,对整个社会的价值观、每个个体的精神信仰,都有着不可忽视的正向建设作用。
因此,今天我们在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视野下来重新审视术数文化,要看到它至今在社会上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对每一个人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都有着或多或少的影响,对我们当下的整个文化体系都有着或多或少的建构、拓展和制约作用。在全球文化互动、世界文明互鉴的格局中,如何将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的思想观念融合贯通、如何引导和建构基层社会的价值观念以及广大民众的精神世界,我们都可以在其中寻找到许多有益的借鉴。
原刊《上海文化》2025年第4期,注释从略
【作者简介】
刘轶,上海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教授,上海周易研究会理事。主要论著有《以德“福”人:<发微论>的文本与理论》(即将出版)、《四库全书本〈青囊奥语〉初解》、《蒋平阶研究》、《闲坐小窗读〈周易〉》、《阳宅风水六讲》、《宜变之爻与之八皆八解赘论》等。
【作者简介】
欧阳端萍,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硕士研究生,发表论文及评论文章《试论丘处机诗歌中“山”意象的形态与意蕴——以<磻溪集>为例》、《跨时空体验,让老弄堂焕新颜》及《城市再造“烟火气”需从小处起笔 心怀长远》等。
【新刊目录】
《上海文化》(文化研究版)
2025年第4期
专 题 中国式现代化与上海文化
王启元 华洋杂处与文明汇通:上海近代城市的生长线索
专 题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刘 轶 欧阳端萍小道亦可观:再议文化小传统对我国当代文化建设的启示
访 谈
曾 军 金方廷人工智能时代的文艺学:媒介、技术与文化生产的重构
理 论
袁 青 由“趣味”到“现象中的自由”——论席勒对“美的艺术”根基的构筑与转换
文 学
莫雨曦 “新人”的塑造及其困境——王蒙《青春万岁》的个人想象与集体叙事
李 浩 谢有顺 生命实感、抒情声音,以及重建总体性的一种可能——论魏微长篇小说《烟霞里》
苏 勇 重新回到人本身——评毕飞宇《欢迎来到人间》
文 化
郝玉满重思“工作”的未来:基于数字社交的工作与工作文化
张登峰 触屏、“数字手势”及其空间逻辑:对手机界面的批判性考察
程 林 “复活亲属”:后死亡时代逝者机器人疗法的正向潜质与伦理风险
文 艺
高 洋 “魔力圈”的“内”与“外”:具身性视域下沉浸戏剧与遍浸游戏的假定性的比较研究
周志博 王玉玮 身临其境的具身想象:身体与影像交互的触感连接
韦拴喜 罗香杰 身韵、气氛与中和:国风舞剧身体审美的三重向度
笔 记
张 治 钱锺书中西文读书笔记系年相关证据考略
编后记
英文目录
封二 吴大羽《公园的早晨》
封三 新书推荐
《上海文化》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扩展版)来源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引文数据库来源刊
社长:徐锦江
常务副社长:高渊
主编:吴亮
执行主编:郑崇选
副主编:张定浩
编辑部主任:朱生坚
编辑:木叶、黄德海、 贾艳艳、王韧、金方廷、孙页
《上海文化》(文化研究版)
主办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地址:上海市中山西路1610号2号楼928室
邮编:200235
电话:021-64280382
电子邮箱:shwh@sass.org.cn
邮发代号:4-888
出版日期:双月20日
主编:朱生坚
编辑:曹晓华
运维:任洁
制作:小邵